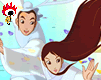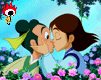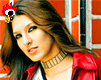| “孔雀公主”杨丽萍:因舞而生,再给舞以新生(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06日15:15 金羊网-羊城晚报 | ||
|
纯粹而非“过酸”,舞台看作田野,把生活的原生态“映射”进《云南映象》 文/本报记者 邓琼 图/本报记者 魏辉 交谈人物:“孔雀公主”杨丽萍 云南大理白族人。从小酷爱舞蹈,没有进过任何舞蹈学校,1971年从村寨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开始职业舞蹈生涯。1986年她创作并表演的独舞《雀之灵》,荣获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第一名,一举成名,并于1994年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创作表演的双人舞《两棵树》,获得观众投票第一名。1998年导演并主演的电影《太阳鸟》荣获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交谈动机 2004年,“《云南映象》与杨丽萍”是国内演出市场提及率最高的词组。这位昔日的“孔雀公主”,领着她的族人,在都市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以舞台为山野,再现了云南少数民族最本真的原生态歌舞,连获第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蹈诗金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编导奖、最佳服装设计奖和优秀表演奖。 从今晚开始一连五天,这台歌舞就要在广州友谊剧院上演。演出前,记者有幸采访了杨丽萍。已经从肺炎中完全康复的她告诉记者:“在广州我们一定会有好的表现。”在如清风般的语调中,她向记者讲述了《云南映象》台前幕后的故事;伴随着那双著名的“孔雀之手”极富表现力的动作,曾经的“冷美人”杨丽萍给人的感觉却是如此热情、年轻而富有活力,“太阳”、“土地”和“耕作”的比喻,在交谈中频频出现。
创作初衷:自然映射头脑中 “就像太阳,它只是一个炽热的大火球,从来不会说‘我要给你们照亮’、‘我要给你们温暖’之类的话,但它就是带来了这一切。”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部原生态歌舞集取名为《云南映象》,“映象”具体的由来或含义是什么呢? 杨丽萍(以下简称“杨”):云南太大,民族歌舞太丰富,要想在一个多小时中全部搬上舞台、呈现给观众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给大家一些图像。但这个“图像”不是强加给你的,印上去的,而是以非常和蔼的方式、自然而然映射到观众的头脑中。 记:不少人从这个歌舞集会联想到张艺谋的《印象刘三姐》,因为这两部作品都与当地的民间歌舞密不可分,而且都蕴涵着一种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的努力,您有没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想过呢? 杨:在《云南映象》创作之初我们是不知道有《印象刘三姐》的,后来我也只是从电视上看过一些片断。但张艺谋到剧场看过《云南映象》,他很欣赏。而我觉得张艺谋的电影很中国,像《黄土地》中的一段“安塞腰鼓”就是我见过的这种艺术形式最地道的表达。所以我们也在一起探讨过,到底怎样才能达到这种艺术的纯粹?一方面要对自己属性的东西特别尊重、有感情,另一方面还有艺术品位,这是不可能单从学校、人生经验中学习探索得来,二者缺一不可。像云南的民间歌舞如今其实遍地都是,甚至在深圳民俗文化村、什么大酒店里都能看到,但与《云南映像》根本的品质不同。那些对民间歌舞的表现太粉饰、矫情、做作,过酸或过甜,这对于艺术而言味道就不正了,我要做就一定要做正的、纯粹的。 但从另一方面讲,张导他们是要立意要做一个旅游、文化产品,动用上亿资金重拳出击;而我们不是,我们没有这种初衷,只是呈现一些美,但它本身就具备了所有成为文化品牌的特性。就像太阳一样,它只是一个炽热的大火球,从来不会说“我要给你们照亮”、“我要给你们温暖”之类的话,但它就是带来了这一切。 演员训练:祭司“发话”才敢跳 “有两个哈尼族的小伙子,要在舞台上表演祭龙的仪式,他们觉得这不对啊,在村里都是一年只有一次怎么现在天天跳!” 记:《云南映象》的演员70%以上都来自云南乡间的田间地头,有的是赶着牛一声吆喝就被选上了舞台,您能说说挑选和训练他们的经过、趣事吗? 杨:这些人都是我边采风边寻找到的,前后大概用了一年多时间。像其中有个叫叶秀丽的彝族姑娘,她本来就是村里的民间艺人,唱歌的本事连作曲家三宝都很吃惊。三宝在钢琴上弹出一个音高,叶秀丽立刻在这个音高上唱开去,一唱十几分钟,很好听,以为她离调了,但她的结束音一定会回到刚开始的那个音上。那个放牛娃,他的牛跑了,他就竭尽全力、用生命喊了一声“堵到起(拦住它)!”这一声让我听出来他不仅声音很好,而且有一种生命力,后来我们在节目中也用到了这个细节。 至于训练他们就更有趣,因为他们都来自民间,歌舞对他们来说只是自然的宣泄而非表演,所以有人跳不动了就蹲下歇着看别人、有人演完了就大摇大摆从台中间穿行到另一侧去,我得教这些起码的规矩。后来,表演中又会遇到和他们的风俗习惯相冲突的地方,例如有两个哈尼族的小伙子,要在舞台上表演祭龙的仪式,他们觉得这不对啊,在村里都是一年只有一次怎么现在天天跳!于是我只好请人把他们的祭司带到镇上,再拨电话去请示,结果祭司说没问题,杨老师这是在传播我们的文化,要信任她。还有哈尼族是不穿耳朵眼的,但我们开场担任打锣的那个哈尼族小伙子要跳一段佤族舞,需要穿耳朵眼,他开始也死活不肯,说回去以后不好交待,后来硬是请示了长老才开了戒。 文化保护:禁变会产生停滞 “原来你跳跃是为了追逐猎物,但现代人不需要追猎物了,这种跳跃也肯定没有了。舞蹈是要跟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 记:目前社会似乎正兴起一股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热潮,人们把您和《云南映象》看作其中一环,甚至把您的举动称为民族文化保护的“杨丽萍模式”,把《云南映象》的出现视为一个文化现象,对此您怎么看? 杨:我认为尽力去做什么,总归会有所收获。对于民族文化,忧虑肯定是有的,像那个绿春神鼓,只有一两个老太太会打,再不抢救就真的消失了。但消失了日子也照过,就像没有了恐龙,世界也还向前进化,所以我觉得许多古老艺术形式的消亡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但你做些工作,总归会多点东西、多些时间;没人去做,肯定就少点什么。 《云南映象》的内容来自民间,但我做的工作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创作或者编舞。我是一个民间艺人、传承者,但同时还有能力发展。我觉得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原来你跳跃是为了追逐猎物,但现代人不需要追猎物了,这种跳跃也肯定没有了。舞蹈是要跟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好的东西要保持,但是禁变就会产生停滞。比如说花腰彝,四大腔五大腔,旋律也很美,脚上的动作很多。但是一直是一个圈,这样就会很单调。包括在舞台上缺乏表现力。我就跟演员讲,手上的动作可以变化比如和别人拍,或是拍地,或是加快。这样会更好看。结果演员又把这种跳法告诉还在村里的同伴,民间也开始这样跳了,你能说不是提高了民间艺术的品位吗?这些演员70%都是田间地头的农民,今后不跳了,回到村子里,会教给村子里的人,这种传统艺术可能就更漂亮了更好了。而且,有了这个剧目,那些传统还能有用,就会有人学,这就是我所能为民间艺术做的事情。 艺术传承:舞台就该是学校 “表演就是学习,纺线、插秧、生命之爱,都从生活中来,不是可以教的。我的演员们不是把舞台当舞台,而是当作田野、土地、草场。” 记:像这样的演出,您一晚上要跳四段舞,一演就是五天,您就不累吗? 杨:很多人觉得我年纪这么大还在台上跳会不会很辛苦,或者做这么一大摊事儿很了不起,其实我说这都是别人觉得,我自己只是在尽本分而已。我在云南采风的时候,一天夕阳西下的时候路过一座山,见到一位农妇在山坡上向上挖地,因为是逆光状态下的剪影,看得非常清楚:她背上还背着孩子,跟大山比起来,就像一只小蚂蚁在搬山!当时我就感动了,觉得这高原女人真是伟大啊!她在挖一座山、对抗一座山!但后来却明白了,其实这女人浑然不知,她可能仅仅就是希望通过挖地、种粮食、让背上的孩子吃饱。我和她是一样的,耕耘这块土地,其实就是让自己吃饱,让我的灵魂和精神吃饱。所以我并不是像外界说的那样,天天皱着眉头要抢救啊、保护啊,我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而且收获了所希望得到的精神富足。 记:这一轮《云南映象》演出完了以后,您会退出舞台吗?会不会开办自己的舞蹈学校? 杨:我不止一次想到过退出舞台,毕竟舞者50岁以后就不再适合表演了。舞蹈家退出舞台后开办学校似乎已成为一种规律,传授自己的技艺。但我不太想去做这件事,因为我的舞蹈有点特别,不是那种从老师那儿学来、然后又可以在传承给学生的常规舞蹈。我跳的是一种感觉一种神韵,我的舞蹈从作品来讲其实很简单,有基础的人可能对着录像带半小时就学会了。就像佛祖布道,一大堆弟子等着他讲话,但佛祖只是拈着一支花微笑,弟子迷惑不解,但佛祖说:“我已经讲过了啊,当我拈花微笑的时候。”就是这个道理,我无法用言语或者简单的技艺来传授自己的艺术。而《云南映象》就可以说是一所学校,舞台就是学校、表演就是学习,纺线、插秧、生命之爱,都从生活中来,不是可以教的。我的演员们不是把舞台当舞台,而是当作田野、土地、草场。从云南到北京,30多年来我觉得自己从未离开过那片田野,总是生活在旧时场景里,就像在田里劳动,高兴了丰收了就要起舞,我永远不会把关于舞蹈的一切当作付出、当成职业,这是我的生活方式和本心需要。 (日京/编制)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