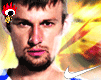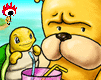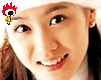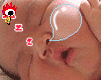| 汉语写作的意义(文论天地)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15日06:04 人民网-人民日报 |
|
恒沙 人们常常只意识到生态世界的失衡,悲叹地球上每天都有物种在消失,而忽略了语言世界的失衡,其实世界上每天也有语种成为历史,而可怕的是伴随着这种语言消逝的可能还有使用它的文化、疆土乃至族群。汉语虽然还不至于到生死存亡的境地,但相对英语,今天汉语的地位也值得关注,一些人产生了所谓的“英语崇拜”情结。在网络化时代,英语已经成为“准世界语”,由“微软”、IBM、“康柏”等跨国公司所支配的这个虚拟世界是以英文为格式和标准的,英语是进入网络世界的通行证;在当今大众文化流行的传媒化时代,美国几乎控制了全球3/4的通俗文化消费市场,《蝙蝠侠》、《泰坦尼克号》、《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在全球的流行与卖座,使得世界人民对美国文化产生了一种认同与向往,新的文化帝国主义正在以技术与娱乐的方式征服世界。当代中国青少年的“英语崇拜”与他们不断接触欧美影视、流行歌曲有关。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作家余光中就写下了《哀中文之式微》,感叹现代中国人母语能力的下降。如果不及时调整,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学习古汉语要比学习外语还难。从历史来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汉语和汉语写作饱经磨难,作家白先勇总结现代汉语的命运时说:“百年中文,内忧外患”。其外有西方语言的冲击,现代汉语严重欧化;其内则是母语的自信心和自觉意识不断衰微,中文成为追逐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遭到修葺的对象。没有一种语言像中文那样,在这一百多年来经历了如此重大的变革。从晚清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言文一致”运动开始,汉语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推行世界语、汉字的拉丁化、语言大众化和解放后的繁体字简化方案,80年代的电脑化挑战等等,面对民族性生存危机和现代化召唤,渴望融入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过激口号。 作家余华说:“像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我一直认为,对中国新汉语的建设与发展的贡献首先应归功于那些翻译家们,他们在汉语与外语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既用汉语传达了域外作品的神韵又同时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性……”当代中国作家几乎都走在这样一个介乎被“欧化”的中文与被中文化的带翻译腔的“西文”之间的“中间道路”上。创作界如此,而批评和理论界也难以超拔,一百多年来,我们学术话语“西化”色彩浓重,从概念、范畴到理论命题,我们都很少使用传统古典文论的东西,所以,几年前文艺理论界发起了“文化失语症”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等学术大讨论,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延续和创新传统文论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不能回避,那就是“文革”语言的影响,“大批判语言”、“样板语言”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套话,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为抵抗这种模式化语言的束缚,主动选择了“西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加速了汉语传统的断裂。 语言不只是一种表达工具,它跟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它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踪迹,成为延续历史与未来的血脉。如果说任何文化的特性都展示在自己的语言中,要认识一种文化,只能从语言出发,那么,保护语言其实就是保护文化,放弃母语其实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传统和历史,放弃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基因。作家韩少功说: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唯有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在历史与现实、“内忧”与“外患”的多重夹击中,汉语如何延续其传统的血脉,创造新的辉煌,这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个急迫的问题。我们能否意识到“中文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那曾经被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鲁迅骄傲地向世界展示过的,延续着几千年中华文化命脉的,最切近我们心灵的母语呢?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呼唤树立汉语写作的自信心与自觉意识。 虽然这一百多年来汉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看到,在这一百多年的短暂的汉语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作家依然把汉语的魅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鲁迅、沈从文、老舍、钱钟书、赵树理、汪曾祺……现代汉语在他们手中展现出强大的应变能力、再生能力和创造能力。现代中国作家为我们重新认识汉语的生命力和魅力提供了无数的实例和典范。现代作家几乎都从传统语言中吸取了许多营养,并使传统文言与白话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让我们重新发现了传统语言的重要价值。比如冰心就是在“白话文言化”和“中文西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独特的“冰心体”的,再如闻一多提出汉语诗歌的“三美”(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张爱玲模仿《红楼梦》的语言,老舍、赵树理等对方言、俗语的艺术化处理等等,可以说传统性、民族性、大众化一直都是现代作家不断追求的目标。新时期以来,许多中国作家也自觉地向传统文言和白话学习,如朦胧诗人吸收了古典诗歌重“意象”,重语言的“不透明性”和暗示性的特点;汪曾祺、贾平凹、阿城、韩少功、何立伟等继承了传统古典美学精神并加以大胆创新,在“神气、音节、字句中苦吟”,追求典雅的“意境”和诗化的“韵味”。汪曾祺对古典式节奏和韵律美的自觉追求,贾平凹对古汉语词法、句法和线形叙述法的汲取,充分展现了汉语典雅的风格,体现出传统文言和古代白话的无穷魅力来。何立伟提倡“汉语表现层的垦拓,促成文学作品琅琅一派民族气派的美语言”,等等。 因此,确立汉语写作的自信与自觉需要对汉语精神进行深入的体认,重新发现汉语的“诗性品质”。应该正确认识中文与西方语言的差异,否定简单照搬西方语法来衡量中文的行为。语言学家黎锦熙、王力、吕叔湘等都不同意用西方语法来套汉语,认为要建立汉语的语法系统,“应是从本国人民的语言归纳整理出来的,不应当沿袭外国语法”。汉语在表达上的自由度和创造性可以和任何一种语言媲美,我们不要片面地认为英语是“准世界语”就盲目地加以崇拜,其实中文在许多方面都有英语难以企及的地方,比如对仗,在这一修辞格上中文就是强势,而英文是弱势。同样,中文的简洁、典雅、含蓄和形象都是字母文字很难相比的,特别是汉字的象形、会意、形声等特点,使得汉字天然具有形象性,用作家汪曾祺的话说,中国人是用汉字来思维,汉字可以“望文生义”,“浩瀚”必非小水,“涓涓”定是细流。白居易《琵琶行》:“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四个带“扌”的汉字,直接将琵琶女宛转优美的姿态和高超的弹拨技艺展现了出来。杜甫《兵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前半句写动作,后半句写感觉,前七个字中就有四个动词,贾平凹说这七个字就能拍一段很长的电影,其形象、简洁与自然,都是字母文字很难达到的。 汉语与英语的区别不在其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在于体验世界的不同。汉语沉淀着华夏民族数千年来感知世界、体察世界和呈现世界的诗性特征,在全球化的今天,汉语的这种诗性特征成为我们解放想象力,体验自由的重要方式。文学能否把我们从这种自动化的麻木的日常生活惯性中分离出来,能否展现民族、地域和个人的性格和精神?作家是否放弃了提升人性、培养德性、守护价值的重任,而沦为庸俗化、商品化生活形态的麻醉剂?文学语言能否让我们重新焕发对生活世界独特的感觉与不倦的激情,能否穿透表面的一致去还原生活的千姿百态和千差万别?这将是评定当代写作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作家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提供独到的艺术技巧,更重要的是能否贡献独特的感知、体验世界的方式,还原生活与存在的意义,正如莫言所说,“写作就是为了使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汉语是一种相当感性的语言,在表达人的内心感受和体验上比字母文字要直接、自然。汉语没有冠词,无位格、时态、语态等变化,不用或者少用连接词,它不同于其他逻辑规则很强的语言,语言规则的逻辑化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先将感知到的世界加以了重组和秩序化,把具体的对象整理成抽象的概念,因此,阅读这样的语言要求我们首先把抽象的概念还原为具体的感性对象,才能在心中唤起对物象的感知与体验。而“汉字每个字都像一张充满感情向人们诉说着生活的脸”(诗人郑敏语),用美国语言学家范诺洛萨的话说,汉语汉字充满动感,不像西方文字被语法、词类规则套死;汉字的结构保持了其与生活真实间的暗喻关系;汉字排除了拼音文字枯燥的无生命的逻辑性,充满感性信息,更接近生活与自然。汉语,特别是文言,在语法上比印欧语系的语言也要灵活自由得多,可以超脱英文那类定词性、定物位、定动向、属于分析性的指义元素而成句,而更直接地呈现感觉到的真实世界。王力先生说,“西洋人做文章是把语言化零为整,中国人做文章几乎可以说是化整为零”,中文能“随物赋形”,重“意合”而轻“形合”,所以中文保留了更多感性的东西,更接近人的瞬间体验而非理性思维。 在确立汉语写作的自信与自觉时,应该处理好语言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强调母语写作并非就是否定外来语,更不是简单地排斥英语,拒绝外来文化,搞文化封闭主义,而是强调语言与文化的平等和互补。伟大的作品绝不属于某个地方、国家或语种,它们都属于“世界文学”,它们的存在证明了每一种语言的伟大。融入世界与保持自我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与战斗,海纳百川为其大,世界因为其丰富性而成为世界,而每一个民族和个人也因向世界贡献其“特色”而意义永存。 《人民日报》 (2004年06月15日 第十六版)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