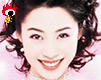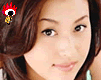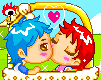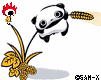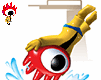| 民族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苏晓星新著《苗族文学史》略评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23日10:36 贵州日报 |
|
据我所知,这是目前国内的第二部苗族文学史。 第一部《苗族文学史》的写作,始于45年前。从1958年作协贵州分会开始编印苗族民间文学资料算起,到1961年完稿,前后共用了三年的时间。然而,事隔包括“文革”在内的20年,直到1981年,方才得以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著者署名为“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执笔者为田兵、刚仁、苏晓星、施培中。那是一部“集体”著作。以“集体”的方式著述,在那个时代是颇为常见的,利弊皆显。也因此,在该书的《后记》(写于1961年)中,编著者十分坦率地承认“仍感到有如下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够好”,他们列举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即:资料的运用问题,两种文化的斗争问题,语言文字和文学的问题,远古神话和汉族神话的关系问题,口头文学为何如此丰富并能长篇保存的问题,苗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比如资料运用方面,编著者就坦陈:“贵州方面的多些,云南、广西、湖南的就少些;湖北、四川、广东方面的几乎是没有。就以贵州的资料来说,黔东南聚居区的较多,西部、北部地区的就少些;中部地区的更少。这当然就影响到《苗族文学史》的全面性、圆满性和正确性”。虽然这第一部《苗族文学史》留下的诸多遗憾,是历史和环境局限使然,但如此诚实坦率的治学态度,在今天的学界却十分罕见,弥足珍贵。也因此,苏晓星作为始作俑者之一,甘愿再次“把编撰新本《苗族文学史》看作一项工作任务”,“下定决心使新本大大超出旧本的水平”。他从1987年开始重新收集补充资料,到1995年完稿,再到2003年12月出版,历时17年。此时的苏晓星,是当年执笔者中唯一的健在者,已是73岁的老人。 我之所以要回顾这段历史,自然是为了说明历史的曲折和著述的艰辛。而初读这部53万言的新《苗族文学史》(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之后,则更觉其得之不易。 我曾在主编的《20世纪贵州文学史·总序》中表述过这样的认识:“治史的关键有二:史识,史料。史识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史料也不能没有史识的爬梳。”治文学史,首要的“资本”是“史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治苗族文学史,与治汉文学史相比,最大难题就是史料得之不易。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苗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字。近现代各时期,曾有过一些苗族知识分子尝试创立自己民族的文字,也有如英籍传教士柏格里等创造“老苗文”,但都未有成功。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在对苗语进行普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了拼音苗文并加以试用推广至今。这就是说,这部书中记述的苗族文学,从原始社会直至今世的1995年,跨度极大,但在苗族书面(也即是用汉文书写的)文学发轫之前(大约是在明初宣德年间,即公元1426年左右)的若干世代,苗族文学作品均无文字记载、统统无籍————无苗族自己的典籍可考,全靠口耳相传。由于旧时代的民族偏见,受封建正统观念影响的文人,对少数民族文化(其中也包括文学)采取漠视态度,不闻、不问、不采录、不参与;即使有所采录记载,也多有零碎、皮毛、偏颇、歪曲甚至歧视之弊。即使是在苗族书面文学产生之后,苗族的口头文学仍然在不断变化发展,仍然需要研究者做出切实的把握和判断。这些,都是需要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对民间“活形态”口头文学的田野考察和大量汉文文献的爬梳),才有可能去充实那“无籍可考”的巨大空白。更何况,由于苗族分布地域广,方言和支系众多,同一母题的口头文学作品往往会出现多种不同的口头“版本”,情况复杂;还有许多不能确切判断其产生年代、只能根据内容形式等推测其形成时期的口传作品……凡此种种,均使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成倍增加。苏晓星在《后记》中大略介绍了自己搜集资料的过程,实际的难度远胜于此。 现在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这部文学史,全书746页,作者竟用了几近一半(345页)的篇幅,来记叙书面文学出现之前,苗族口头文学的发生、发展、流变,以及其间多姿多彩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作品。可以说是基本上解决了第一部《苗族文学史》中存在的最大缺憾————资料不足的问题,堪称为一部资料充实、考据翔实的苗族文学大全。所谓“考据”,就是考核、考查、考索所收集到的证据、依据,并作出判断。从这部书运用爬梳史料、整理典籍、考证辨伪的方法和手段,研究苗族的各种文字形式及口头流传的文学作品文本中,可以看见苏晓星使用的正是中国传统的朴学家们治史料之学的方法,无论是参看古籍,还是听取传闻,所持之据大多有一定的可靠性,其功夫在于舍粗取精、由表及里,并在有充分依据时去伪存真。从方法论上,我甚至感觉到既有一点乾嘉学派的遗风,又有一点“疑古”派与“释古”派相结合融通的某种意味。 治文学史,“史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学史研究,既要掌握充分的资料,又必须具有“史识”。如果说,资料有时候可以借助于别人搜集的成果,“史识”则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独到的见解,能够从大量的资料中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文学史具有的历史科学性质,要求治史者必须在研究中强调“历史眼光”,即所谓“史识”。用王瑶先生的话来说,“最重要的是,把一切文学现象都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与消亡的。”这部《苗族文学史》为读者记叙了苗族不同类型和形式的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神话的盛衰,传说的更替,歌谣的流布,说唱文学的勃兴,以及各种仪式歌、苦歌、反歌的变异……在进行苗族文学历史的叙述时,苏晓星并没有把任何文学现象凝固化、绝对化,而是用变动、发展的观点去考察文学历史的运动。在这里,一切口头的或书面的文学作品、一切无名的或有名的作者,都是历史发展线索上的一个环节。这个特点,只要我们在阅读此书时稍加注意,是不难发现的。 但这并不是说,这里的历史主义是“相对主义”的。我们不能够因为历史永不停息的变动,便忽视了其中包含着的某些恒定不变、具有永恒价值的因素。在苏晓星所记述的苗族文学流动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苗族先民创造的丰饶的文化土壤上,孕育了苗族丰富的神话、传说、史诗、民间故事、劳动歌、祭祀歌、巫辞、理词等等,这是苗族文学之源,苗族人民在这样的民族文化环境中成长、壮大,其中的优秀文化传统作为某种“基因”继续以“活形态”存活于民族民间生活之中,呈现于后世的苗族文学作品和民族精神之中;也有一些随着民族的交融、文化的交流而进入到其他民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化与文学的紧密关系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对苗族而言,其史前时代的文化变迁,正是考察其族群迁徙、文学交流的重要线索。前辈学者如闻一多在《东皇太一考》、姜亮夫在《楚辞今译讲录》中,也都曾把活形态的苗族文化和一些现代苗族的民俗资料,引入对民族文学史的研究之中。这是很值得借鉴的。这部《苗族文学史》对此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和体现。当然,一种文化流传到现在的形态,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古代的形态,它在流传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必定会有消减、增添、变异、优存劣汰的种种变化。作为后人,我们只能去努力寻找出它们之间的某些文化“基因”,并对它的延续轨迹加以描述。这就需要研究者具有横跨古代(汉文)文学史、民族文学史、民间文学史及民族史的学术功底。在我看来,苏晓星数十年来对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积累,以及他在民族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使他具有了描述苗族文学历史的扎实功夫,成就了一部新《苗族文学史》的诞生。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看到了这部《苗族文学史》表现出其“史识”的另一个方面,它十分关注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联系,苗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的联系,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苗族方言区(东部湘西方言、中部黔东方言、西部川黔滇方言)、不同的苗族支系文化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并呈现为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联系,即强调了“历史的联系”的观点。特别是文学与时代的联系,是一种最为重要、也最为基本的历史联系。苏晓星正是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之中去解释各个时代的文学现象。重要的是,这种解释和揭示是客观、具体、而非主观臆断的。我们可以从他所划分的四个文学时段中,清晰地看到其中“历史的联系”的脉络。在他所理清的苗族文学历史发展的线索中,构建了一系列有因果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从中体现出规律性的东西。这种理论的抽象和概括,并没有损害苗族文学“典型现象”特征的丰富性、具体性和个别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十分看重苏晓星把“历史过程”与“历史联系”的观念和方法引入民族文学史研究之中,从而使这部《苗族文学史》成为一部尊重历史事实、从历史实际出发、正视历史、再现历史本来面貌的民族文学史著作。 在这部《苗族文学史》中,关于苗族历史的分期,苏晓星采信的是《苗族简史》(《苗族简史》编写组编写,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框架,即“原始社会”、“封建领主制社会”、“封建地主制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四个时期,并据此划分苗族文学的历史分期。需要指出的是,据我所知,在《苗族简史》之后出版的《苗族史》(中国少数民族专史丛书之一,伍新福、龙伯亚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苗族通史》(上下册,伍新福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中,关于苗族封建社会发展的形态问题,均认为各地区苗族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以及封建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是先后不一的。它们认为,有一部分苗族首先产生和形成了封建领主制经济,有一部分(主要是“生苗”)则直接发展了封建地主经济;而土司制度的基础也并不单纯是领主制经济,土司土目中有一部分是封建领主,对包括苗族在内的“土民”进行农奴式的剥削和奴役;另有一部分土司土目虽对辖区内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但实行的主要是租佃制剥削,其经济形态属地主经济;还有部分土司土目曾实行过奴隶制,对辖区内包括苗族在内的“土民”进行奴隶式的奴役,后来又才逐步转变为租佃制的剥削。这两部“苗族史”都认为,过去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先有领主制后有地主制,土司制等于领主制)是不符合苗族历史发展实际的。我没有研究过苗族的历史,也不清楚史学界、特别是苗族史学界对这些观点的认同度如何。我只是想,这部堪称为民族文学研究重要成果的《苗族文学史》,如果适当汲取苗族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加以合理的阐释,或许会有更为丰富精彩的言说,更逼近于苗族文学与社会发展的历史真实。 最后,我还要突出地说明,完成了这部《苗族文学史》的苏晓星,是一位以小说创作为“主业”的著名彝族作家。以小说家来治文学史,以彝族人来治苗族文学史,从28岁“写”到73岁————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安排,也有个人的机缘。偶然耶?必然耶?而在我看来,这也就是历史。 作者:何光渝 来源:贵州日报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