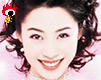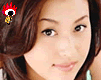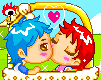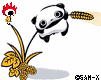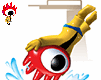| 《借我一生》:回应批评不“忏悔”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23日11:45 大华网-特区青年报 |
|
在经过足够的“造势”之后,备受关注的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已由最新一期《收获》杂志刊出了五卷中的“童年”和“文革”两卷。 全文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其中余秋雨以大约十万字的笔墨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一段的经历,对一些之前颇有争议、读者也非常关心的问题,如“是否参加过‘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是否为‘石一歌’成员”、“在《朝霞》杂志社工作”等做了“自我阐释”,并不失时机地对一些批评如“文化口红”等做了回应。 关于“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在《借我一生》第二卷第四章“冬天的斯坦尼”第一节中,余秋雨描述了自己加入“社会大批判”的过程。 1968年秋冬之间,进驻上海戏剧学院的工宣队找毕业生谈话,在与他谈话时,一位小王师傅告诉他,上海的几家报纸编辑要找一些空闲的专业人员,写几篇批评旧俄理论家的文章。工宣队听说戏剧学院表演系徐企平是这方面的专家,要余秋雨跟他一起去。 到文汇报之后,报社文艺组的编辑安排余秋雨等几个比较空闲的专业人员讨论旧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后来,当时已经参加了市里一个写作组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胡锡涛要写一篇评斯坦尼的文章,由于不太懂表演,想让他们帮忙做些文字准备和专业咨询,双方在观点上非常对立,余秋雨的一篇《关于“从自我出发”》被胡锡涛“枪毙”。两个月后,余秋雨随同学一起下乡。 在本章第四节,余秋雨援引了胡锡涛2000年在《今日名流》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片段,议论说:“在读到文章的当时,我正陷于一批文人捕风捉影的诽谤狂潮中,诽谤者们虽然口气越来越大却始终找不到丝毫证据,最后只能咬定我批判了斯坦尼,并由此推断我参加‘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关于“石一歌” 第七章“吴石岭”的第五节中,余秋雨描述了自己1973年参加鲁迅教材的各高校联合编写组的情况。 当时余秋雨已回到上海戏剧学院,每天挖防空洞。某天,一个叫王政的宣传队员找到他,给他看一张落款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育革命组”的油印通知,要他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青年教师的身份,参加一个鲁迅教材的各校联合编写组。 余秋雨写道,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组长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副组长是复旦的教师,组内有一大半是工农兵学员。编写任务其实很轻,工农兵学员在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一些鲁迅的小故事,用的笔名叫“石一歌”。 而各校来的青年教师在为工农兵学员注释几篇鲁迅作品,在为他们写一本通俗的鲁迅生平,余秋雨分到了广州一段。后来听说还要为学员写几个与鲁迅对立的人物的小传,他选了胡适。但刚写了一个开头就觉得没有意思,不想写了。按照余秋雨的说法,他“流落复旦的时间很短”。 关于《朝霞》事件 “《朝霞》事件”具体发生时间余秋雨并未点明,只说写作组要求他和一个同学一起去编一份鲁迅资料,而资料没有编成,便遇到了“奇怪的《朝霞》事件”。 余秋雨写道,当时《朝霞》杂志由写作组的一位陈女士实际主管,倾向极左,质量不高,由于几篇文章被“工总司”抓住了尾巴,牵动上层,写作组中的朱永嘉、王知常等人主张脱钩,陈女士离开上海“养病”去了。于是便发生了一件对他很“不仗义”的事情。朱、王二人想找一个写作组之外的青年人去做脱钩过渡,心急火燎中便顺手“逮”住了他,却没有向他讲清全部危险背景,只说是“工总司”的一批人在捣蛋。 于是余秋雨便与一位姓陈的青年工人一起去了《朝霞》,但身份极为含混,似乎是为陈女士做点联络工作的。当时他在《朝霞》待了三个月,编辑部在两位老编辑的领导下继续工作,而他则在编辑部外面的一间屋子里办创作讲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剧的写作技法。三个月之后,“工总司”斗争矛头别移,陈女士回来重新主事,朱、王也没说一声感谢,就完了。 余秋雨这样描述后来发生的事情,“后来我突然听说,这件事不仅王洪文亲自发了话,在上海的市委所有领导都有批示,批判这个杂志,‘工总司’如果真来‘踏平’,具有充分理由,但写作组居然全都瞒着我!”“当时的写作组,在‘工总司’面前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弱者,但他们怎么能够把自身灾难悄悄地转移到一个年轻人身上呢?”他质问朱、王二人的结果是,朱永嘉说:“你年轻,怕你知道了紧张。”王知常说:“人啊,知道越少越安全。” 关于“自我清查” 1976年冬天至1978年冬天,是余秋雨印象最深的历史转折期,在第九章“隐秘的河湾”中,他详细写了自己这两年接受清查的情况。 三中全会后,清查组要求他写了一份自我清查,里面提到三个问题,一,他曾帮助在外地农场一起劳动过的残疾人沈立民,从邮局转寄一封车间工人集体签名信给当时分管工业的市政府领导马天水,马天水后来犯了政治错误;第二,十年间他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但在复课后又一次对自己所在学院表演系编的一份台词教材,提出过不恰当的口头意见;第三,他生病期间,曾帮一位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工人从文字语法上修改一篇谈《红楼梦》的极为幼稚的千字短文。 清查组的人告诉他,这篇清查文字“太幽默”,可能会做些修改,但后来没有回音。 余秋雨接着写道,二十多年后,由于一场笔墨官司,他费尽周折找到了当时的材料,读过的人认为不知所云,他估计,自己的文字一定被人改坏了。 关于“金牙齿” 在《借我一生》的第二卷中,余秋雨多处提了一个被他称为“金牙齿”的人。 第一处是在第七章第六节,他写道,“我们这个高校联合编写组里掺进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比较奇怪。”这人“一笑,露出两颗发出铜绿的金牙齿”。他还曾经策划了捉弄这个“金牙齿”的恶作剧。 另一处是在第九章九至十一节,他被揭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因为“金牙齿”向上揭发在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时,余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而余秋雨写道,他当时离场的原因是一位教师突发疾病,他和一位年轻人将这位教师送回家中,当时“金牙齿”就坐在边上,完全知道他们为什么中途离场。 余秋雨认为,“本来在‘文革’中,凭他与编写大学教材毫不相干的奇怪身份,凭他与上海几个工人造反司令的接触,我一直怀疑他在教材编写组中担负着某种耳目的角色。” 关于“文化口红”和“姓余的青年” 在文章中,余秋雨还对近年来一些批评意见作了回应。 如第一卷第五章中,他写自己初中时,美术老师要他做模特儿,只穿内衣站在讲台上,让大家画。结果男同学画的他,多数是裸体,女同学画的他,几乎都涂满了口红,还用很大的字体写了他的名字。美术老师告诉他,“美术不同于照相,画你,其实是画每个人自己。那分数不属于你,只属于他们。” 余秋雨这样写,“这段话,几十年以后我还拿来送给那些把文化声誉说成是‘文化口红’的评论者,笑他们怎么做起了我初中女同学们早就做过的事。” 而在写到自己在文汇报社工作时,因为贫穷忍饥挨饿的时候,余秋雨将笔锋转到了一位对他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姓余的青年”,他写道,“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我好奇地去见了这个年轻人,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李凌俊)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