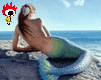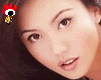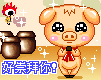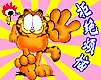梁小斌
“年轮”是个矛盾的词,按照字面意思,它应该代表着某种速度,或者对细节的忽略,但实际上,这个词给人非常缓慢的感觉,缓慢到让人联想到马车、烛火以及生命的冬季,后面这些意象非常诗化,在我们的国度,诗总是和某种农耕情绪有关,确实,“年轮”最初的意义来自树木,来自漫长岁月在一个封闭体积内的疯狂运动,这种运动类似于轮子滚过的痕迹,而当我们开始广泛地注视这种运动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力量时,一首诗便诞生了。我甚至觉得所有被称为诗的东西,不过是对“年轮”这种现象的反映和追问,我们可以为它总结出以下特征:封闭的核心、非线形、清晰、变形、对灾难和丰收的双重敏感……
促使我对“年轮”作这么多描述的起因是一本散文集,作者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这代人曾经有过自豪的称呼———“共和国的同龄人”,这种带着政治光荣的集体命名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如果我愿意相信代沟,如果“代沟”说明的是一部分永远不会对另外一部分人发生兴趣并试图理解他们,那么,我在看我的同龄人所写的文章时,我就是在看我们自己的断代史,一种直接塑造和饲养了我们的思想器官的营养,这种营养越来越难以重现了,事实上它也不可能重现,在这个意义上,我又常常会把这本叫做《清唱》的散文集看作某种时代情绪的墓志铭,上面深深地刻着两个字:年轮。
有没有特殊的时代呢?大多数人常常把“文革”十年或者更长的一些历史看成特殊的时代,把活动在里面的我们看成命运不济的人群,这或许是出于政治的、历史的角度考虑,而作为一个直接面对世界本身的写作者,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相对于任何其他的一段时间,另外一段时间必然是不同的,没有普遍性的历史,只有普遍的人性。每一次翻开这本书,都仿佛和我自己曾经的一部分生活相遇,甚至更深入,我就是在书中所揭示的人性基础上继续活着,看这本书我常常想起柏林的一句话:道德上的迟钝是我们准确判断事物的基础,我和崔济哲生命状态最积极的一段时间,绝对是道德感过度敏锐的时代,而一个道德兴奋的时代往往不给人性留下回旋余地,这是最让人感到劳累的事情,《清唱》正是从这种劳累中开始表达善良和爱,美和沧桑———如果单单是这样,我还不感到震动,如果单单是这样,我只能想到我的另外一个同龄人所表达的粗浅口号:青春无悔。事实上,人生过程在任何一个个体身上都展现出足够的丰富性和残酷性。这不是悔恨不悔恨的问题,而应该站在空气的深处,光的尽头来打量我们年过半百的生命,只有站在这里,才靠近了“年轮”哲学:万千荣辱在我们的时间和身上碾过,它也在一切人、一切时间那里碾过。我们的梦与怒、痛苦与呼救都将成为尘土的一部分,但这是光荣的尘土,是漠漠年轮永恒的回声和抵抗。
我珍视《清唱》赠给我的朴素思想,正因为它是诗性的,普遍性的,同时也是拒绝浪漫化的升华的,在作者清点他一生所注视和聆听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的时候,情境非常具体,言语极度克制,这同样是某种代际特征,我们这一代人犹如离开熔炉的铁水,见识过最惨痛的煎熬,这煎熬至今还在我们坚定而恒温的内心中起作用,我们已经开始对往事着迷,并利用回忆的长镜头和分析的钝剪刀来确定自己的情感方式了,《清唱》的第一部分是对作者父亲的追述,这种追述在客观性的后面隔着隐隐惊雷,它永远不会爆炸,不会体现为今天的流行语态,我们在最适当的年龄被剥夺了说“我爱你”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并未消失,在更长也更深重的承当中,它化为“难言的恩情”,丈量着父子两代人之间的心灵距离。
这种丈量在我和已经离世的父亲之间也一再出现,当我再次诵读崔济哲的这一部分文字时,我感到深深的紧张和欣慰,并为辽远的人类情感流下泪来。
《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31日 第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