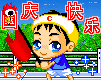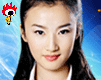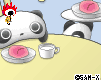柴火·蜂窝煤·液化气·电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01日09:18 海峡网-厦门日报 |
|
——家庭燃料的变迁 征文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从古以来一直是家庭的主要燃料。后来蜂窝煤、液化气先后走进了我们家。家庭燃料不断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所生活的土地上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我的父辈和我生活过的厦门古镇——马巷镇,亲历了这几次家庭燃料的变迁,回顾过去虽感慨万千,却是像倒吃甘蔗越吃越甜。 小时候,我就时常依偎在母亲的旁边,一边陪母亲烧火做饭,一边听她讲小时候上山打柴的故事。儿时的故事,红红火火的炉膛,烧焦的干柴味,一起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家的村庄路口有一大片空地,屹立着三棵葱郁的大榕树,炎热夏季时是村民纳凉的场所,同时又是远近村庄贩卖柴草的集市。每逢周末,四面八方的村民,或肩挑,或用马车驮着,或慕名而来买柴草的。讨价还价声,马的鸣叫声,相识的人互相问候声,杂糅在一起,汇成一首乡村生活的独特交响乐。柴草以十斤论价,每十斤虽只有几分钱,但却是一些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买柴草,要看柴草的品种,还要观察柴草的干燥情况,越是干燥的柴草销路越好,价格也较贵。记得逢年过节时,父亲常要到村口,买一些干草干柴准备过节时用。而今这一片空旷的土地已被鳞次栉比的楼房取代,再也见不到昔日柴市的热闹情景,只有郁郁苍苍的老榕树犹存,似乎在述说着当年的故事。 我懂事时常常要烧火煮饭。那时大人早早就要出门劳动,母亲把米淘好,在锅里放适当的水。中午和下午,邻居的烟囱冒烟了,就是我煮饭的时候了。烧柴火烟特别多,一顿饭下来常常要被熏得两眼泪花流。家庭经济逐渐好转,父亲不再上山打柴了。而我和妹妹还经常到村外拾柴火。我最喜欢拾桉树的落叶。桉树叶大,掉到地里久了就与土沾在一起,不方便打扫。有时就要拿一根铁棍(可作烧火棍用),下端磨锋利,上端拧成一个圆圈,方便手拿,看到树叶,用力一刺,刺成一团后,从上往下一推放到箩筐里,这样周而复始直至满载而归。我上学时仍要继续充当“火头军”的角色。放学回来,不仅要忍受饥肠辘辘的折磨,还要取火烧柴做饭。我家有六七口人,煮这么多人吃的稀饭一般要三四十分钟。每逢梅雨季节,阴雨绵绵,空气湿润,有些柴草发霉,拿起就是一股腐烂气味,直熏得鼻头酸软。柴草不时熄火,既要点火又要扇风,常常累得焦头烂额还煮不成熟饭。而炎热夏季,酷暑难耐,拾柴起火,既要承受高温的煎熬,还要忍受呛人的烟雾。一顿饭下来,不仅汗流浃背,而且“两鬓苍苍十指黑”。 大人到田里劳动,家里的“火头军”大都由小孩担任。当时每家每户都有储存着许多柴火的“草房”,紧邻“灶脚”,很容易酿成火灾。“火烧厝”时有所闻。小时邻居家着火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瓦房突然冒出浓烟,火苗蹿出屋顶有四五米高,弥漫的烟雾夹带着四处漂浮的灰尘,今天想起还叫人后怕。大火蔓延起来房屋十有八九坍塌,屋内杂物基本上都化为灰烬,只剩下几根已经断裂、被烧黑的木梁。 我读高中时,恰逢改革开放,北方的煤源源不断运来,我的家里开始使用蜂窝煤炉了。煤炉买回家时,那晚我高兴得睡不着觉。不过烧蜂窝煤也不是那么简单。先是买煤运煤要费一番工夫,接着要到村外挖红土。找一个晴朗的日子,家里劳动力齐出动,把煤配一定的比例红土加适量的水翻均匀,再用印蜂窝煤的器具印成蜂窝煤,让它们排成整齐的队形,然后在太阳下暴晒,把湿润的蜂窝煤烤成可以搬运的成品煤储藏起来。有时刚刚印好蜂窝煤,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只能眼睁睁看着印好的蜂窝煤付之东流。烧蜂窝煤比起烧柴火不仅简捷省时,而且炉火旺。不过仍要忍受那呛人的煤气,也常听说有些家庭发生煤气中毒的事。 而今我在都市里拥有一套一百多平方的三房两厅居室。厨房用的是锃亮的液化气灶,只要一拧开关,液化气“嗤”的一声就自动点火。液化气用完了,一打电话自有工人送罐上门。整洁的灶台上是光亮的抽油烟机,掌勺时再也不用担心油烟之苦了。 小康生活从厨房开始,随着经济收入不断增长,一些带“电”的厨具也不断进入我的厨房,如电饭煲、电压锅、电炖锅、电炒锅、微波炉等。有了这些高科技的电器,一日三餐省去了很多麻烦,可以同时做几件烹饪的活。在厨房忙碌的时间越来越少,可烹饪出来的食品却越来越多,越来越丰盛可口。 现在很多人可能难以理解柴的重要了,柴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淡忘了。不过每当我在厨房的时候,总要想起过去那段岁月,想起那散发着青草般气味的柴火,想起那整齐划一的蜂窝煤。燃料的变迁,演绎出一段辉煌的历程。亲历这段历史使我深刻体会到:多姿多彩生活就像那煎炒炸烹煮出来的食品一样丰富多彩。 (苏志民)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