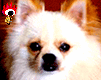|
中国西部网消息 (记者王艳明)随着首部全面反映莫高窟北区考古成果著作《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今年全部出齐和莫高窟北区加固工程本月底的开工,占莫高窟总洞窟1/3的北区首次揭开了神秘面纱,而北区新发掘出的众多珍贵原始资料,也消除了人们对“敦煌学”研究将因材料被挖掘殆尽而走下坡路的疑虑。敦煌研究院保护所所长王旭东说:“从本月28日起,历时约一年的莫高窟北区加固工程将拉开帷幕,这是历史上首次对莫高窟北区实施大规模加固维修。”
集壁画、彩塑、建筑于一身的敦煌莫高窟,被公认为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连续营造时间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长廊和佛教艺术殿堂。但就在如此闻名于世的世界文化遗产之内,人们关注的只是有壁画和彩塑的南区,而北区几乎被遗忘。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足够的考古信息和研究成果,莫高窟北区崖面上一片荒凉的“破洞子”很少有人问津,就连学术界也在观望。北区崖面上的洞窟数量有多少?洞窟形制有什么特征?开凿数以百计的洞窟又有什么用途?它们在莫高窟石窟群中占有什么地位?没有人能够做出回答。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1988年至199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敦煌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对莫高窟北区先后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今年由文物出版社全部出齐的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就是这一系列考古的集大成之作。
曾主持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彭金章说,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中,长期以来人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基本都有了解答,尽管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对于敦煌遗产来说,莫高窟北区考古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考古新发现。
通过此次系统考古发掘和研究,专家们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其中新编号洞窟243个,加上南区已知的487个洞窟,莫高窟现存洞窟“新增”至735个,基本恢复了唐代碑刻中莫高窟“窟室一千余龛”的原始面貌。同时,专家们还发现了“前室和一个后室”、“前室和双后室”、“前室、一个中室、一个后室”等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洞窟类型。
彭金章说,除了洞窟的数量之外,北区的性质如何,古人凿此有何用途,一直困挠学术界。过去有人推测,“北区洞窟是画工和塑匠的住所”,但在数年的发掘和研究中,不但没有发现上述资料,反而发现了禅窟、僧房窟、瘗窟、廪窟和礼佛窟等洞窟类型,从而证明,北区是当时僧众生活、居住、修禅以及死后瘗埋的场所。依托敦煌石窟艺术和藏经洞出土文献,上世纪初,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产生。近一个世纪以来,“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几乎成了敦煌学界的“金科玉律”,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和可用新材料的挖掘殆尽,许多人担心,敦煌学会不会在新世纪走下坡路。莫高窟北区的考古新发现,无疑消除了人们的顾虑。
彭金章说,在北区出土的诸多遗物中,首屈一指的要数回鹘文、藏文、梵文、婆罗迷文、回鹘蒙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等多种民族文字的珍贵文献,它们的发现尽管与上世纪初藏经洞“宝藏”不可同日而语,但其珍贵价值也让学术界吃惊不小。如汉文《排字韵五》文书是失传已久的佚书,西夏文《碎金》、《地藏菩萨本愿经》、《番汉合时掌中珠》残页都是国内甚至世界上现存的孤本,另外发现的回鹘蒙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文书还是敦煌地区首次发现。
除文字资料外,在北区出土文物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波斯银币、西夏钱币、回鹘文木活字等,这些都是敦煌地区首次通过科学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另外,北区还出土了一批铜器、木器、铁器、陶器和棉麻毛丝织品等。专家指出,这些文物同样有较高的考古和研究价值,将对敦煌学研究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展示是所有文化遗产自觉承担的社会功能,敦煌也不例外,从1979年开放至今,先后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万人次的游客参观了莫高窟。但随着游客的逐年增多,脆弱的壁画和彩塑已经不堪重负。如何“解放”洞窟,为世人所共同关注。
近些年,敦煌研究院试图通过参观预约、打造虚拟洞窟等方式来缓解保护压力,但面对蜂拥而至的游客,仍是收效甚微。因此有人提出建议,“开放北区将是分流游客的一个重要方式”。随着北区系统考古的完成和加固工程的即将展开,北区向游客开放提上了历史日程。敦煌研究院保护所所长王旭东说,在此次北区加固工程中,除对崖体进行全面加固和维修外,敦煌研究院还将选择一批洞窟建设相关基础设施,为开放做准备,一年之后,北区将成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
敦煌保护实现了三大跨越
从1944年至今,敦煌保护事业先后经历了文物守护、抢救加固和科学保护三个时期。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李最雄说,这三个时期就是敦煌保护的三大跨越。
“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破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着大自然和人为毁坏的厄运。”这是1944年常书鸿等人初来莫高窟时见到的情景,他的回忆文章保存了这一珍贵历史资料。
常书鸿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是敦煌石窟保护与研究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敦煌保护事业在千疮百孔和“一穷二白”中起步。由于正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受人力、财力所限,直到1949年,当时所做的一些保护工作基本上只能达到一定的看守作用。1950年,国家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了对敦煌石窟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并于1961年确定敦煌石窟为首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1963年,莫高窟历史上最大的抢险加固工程正式开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拨付100万元作为专项资金。
李最雄说,除了莫高窟浩大的抢险加固工程之外,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人们还对1250多平方米濒临脱落的壁画进行了边沿加固,对260多身倾倒和骨架腐朽的彩塑进行了抢救,对莫高窟象征性建筑九层楼进行了维修,对敦煌石窟的重要组成西千佛洞进行了加固等。作为不可再生资源,敦煌壁画、彩塑等都有着文物脆弱、保护艰巨等特点,为了使这一优秀遗产更好地保存,科学技术成了延缓敦煌遗产衰老的重要手段。
李最雄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量先进科技不断引入了石窟保护的各个方面,如石窟地质与环境调查,环境监测与质量评价,用新技术、新材料加固石窟,综合性防风固沙,用数字技术对壁画信息进行储存,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采用计算机建立石窟文物、工程和保护修复档案等。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新技术、新材料、新手段的不断引入,极大丰富了敦煌遗产的保护技术和保护手段,有效改变了石窟内部及其环境的保护状况,使敦煌遗产的保护工作从原来的抢救性保护,过渡到了科学保护阶段。
敦煌保护的成效显著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3000平方米病害壁画得到修复和进入莫高窟窟区的积沙减少了90%,成了两个可以量化并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但在成绩面前,敦煌人也清醒地认识到,敦煌遗产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保护对象特殊,未来保护依旧任重而道远。如大量的病害壁画需要修复,威胁莫高窟的风沙还没有彻底治理,游客日益增多对文物的破坏还在不断加大。这些都需要通过积极的科学探索,用新技术和新手段去解决。
边陲小镇 世界瞩目
能引起全球学者的共同关注,并不断从事相关研究,敦煌石窟影响的不断扩大和敦煌学的崛起已经使敦煌这个边陲小镇,变成了弘扬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基地。
依托敦煌石窟艺术和藏经洞出土文献,上世纪初,敦煌学产生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柴剑虹说:“莫高窟是敦煌学的发祥地,应该成为全世界最权威、最完备、结构最科学,而且使用最方便的敦煌资料中心,这也是保护敦煌事业能均衡、持续、有效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石窟考古、艺术和文献研究领域,敦煌研究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通过数十年不懈努力,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已经出版专著180多种,发表论文2600多篇,对敦煌和莫高窟的历史、地理、艺术、内容、文化和佛教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揭示,改变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局面。
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不无感慨地说:“必须承认,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现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在未来的发展中,除在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和研究理念与方法上需要创新外,敦煌研究院还要成立三个机构:敦煌学信息国际中心、敦煌学国际出版中心、敦煌学研究国际基金。逐年升温的学术交流,使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涌向敦煌。研究敦煌、传播文化,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了弘扬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一个特殊形式,许多人正是通过专家学者和敦煌了解了中国文化。
除了敦煌显学研究和交流产生的影响外,敦煌石窟的无穷魅力正在吸引着海内外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爱好者纷纷涌向敦煌。据统计,从1979年开放至今,20多年来,先后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万人次的游客参观了莫高窟。在这之中,不乏一些外国政府首脑、要员和国际知名人士。为了让人们更加充分地了解敦煌,每年敦煌研究院除了举办各种国内、国际的交流活动外,还要将学术界有关敦煌石窟的最新研究成果传授给讲解员。“这样做才能让敦煌学从书斋走向大众。”敦煌研究院接待部副主任李萍说。
敦煌研究院已经培养了一支中国一流的讲解员队伍,他们能用英、日、法等六种语言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讲解敦煌文化。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走近敦煌,敦煌莫高窟开始向所有中小学生免费开放,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离退休干部也能凭有效证件进行免费参观。樊锦诗说,展示是任何文化遗产自觉承担的社会功能,但绝不能以牺牲遗产和文物为代价,为了更好地处理好保护与文化弘扬、传承间的关系,目前敦煌研究院正在用数字技术建设虚拟洞窟,同时敦煌研究院还在筹建一个综合游客服务中心,以解决国内、国外参观者的更多需求。
敦煌已成为中国文物保护的国际合作典范
在莫高窟昏暗的洞窟和狭窄的栈道上,经常能看到外国专家和中国专家共同工作的身影,为了使敦煌遗产传之久远,敦煌研究院不断在国际合作中寻求发展,取得不少成功经验。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不可否认,外国保护机构和组织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为敦煌保护的新力量,从资金、技术、人才到设备,源源不断的国外支持和帮助,使敦煌保护的技术水平、管理经验得到了提高。国外力量参与敦煌保护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近20年来,已经有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美国西北大学、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日本大阪大学等多个国外机构和组织参与了敦煌的保护。
他们在石窟内外环境监测、风沙危害治理、壁画病害机理研究、保护材料筛选、壁画修复科研及洞窟数字化拍摄、人才培养等方面与敦煌研究院进行了多项合作。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进行的以莫高窟85窟为主要对象的长期合作。该项目是《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指导下的第一个保护试点,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又是国际合作产物,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联合制订。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所长蒂姆·伟伦说:“通过不断努力,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和共同目标,莫高窟85窟的项目实施是良好的,这是在盖蒂与国外机构合作项目中最成功的一个。”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这是中国文物单位与外国组织合作时间最长、效果最好的一个项目,在15年的持续合作中,我们的保护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学到了许多国外先进的文物保护和管理经验。”
中美双方在莫高窟的保护合作,受到了中外专家的广泛关注,他们认为,这是国际文物保护领域的合作典范,所取得的成果,不但解决了莫高窟本身保护中的诸多难题,而且对丝绸之路其它石窟和古遗址的保护都有借鉴意义。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持续一个长期的国际合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在文物保护上,每前进一步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可敦煌研究院在与国外机构、组织联合保护敦煌遗产中,却做到了进展顺利和成效显著。樊锦诗说,敦煌研究院选择的都是技术水平高、信誉好、实力强和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合作伙伴,他们在文物保护技术、修复工艺和管理经验上都是世界一流的。另外,在合作保护中,选择的都是双方感兴趣的项目,都是敦煌文物保护中亟待解决又无法解决的课题,保证了敦煌国际合作项目的有效开展和持续进行。
60年“面壁”锻造“敦煌精神”
今年是敦煌研究院建院60周年,同时也是敦煌保护与研究事业的奠基人常书鸿诞辰100周年,从下半年起,一系列纪念和研讨活动在敦煌陆续展开,弘扬敦煌人60年坚守大漠的“敦煌精神”就是主要内容之一。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我们是在沙漠戈壁中搞保护,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巨大汗水和勇气的付出,并能耐住寂寞和孤独的挑战,敦煌研究院几代人努力工作而形成的‘敦煌精神’,是我们前进中的动力,这一点永远都不能丢。”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石窟文物保护机构,敦煌从此结束了历史上无人管理的状态,常书鸿等第一批守护人不光成了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的奠基者,同时也成了“敦煌精神”的创造者。“灯是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是用木头剜成的,灯苗很小,光线很暗;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主食是河滩里的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韭菜。”这是第一代敦煌人1943年到达莫高窟后的第一顿晚餐,而这样的生活此后在莫高窟延续了几十年。
在老一代敦煌守护人中,范华是唯一在世并60年没有离开莫高窟的人,在莫高窟搞了一辈子后勤工作。范华说,在敦煌事业的初创期,敦煌人睡的是土坑,用的是土坯做支架的桌子和书架,甚至连沙发都是土坯砌成,然后铺上旧棉絮,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制家具。直到1962年,莫高窟还没有电,而上山(上莫高窟)和进城(到敦煌县城)时,常靠一辆旧牛车,往返一趟,至少一天一夜。1965年,才迎来了第一辆轿车。
由于参与并体验了敦煌人早期的艰苦创业历程,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施萍亭用“打不走”形容了敦煌人的精神情感,并发表了题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的文章。她说:“敦煌人的生活、工作是苦的,然而,敦煌人除了因孩子上学不便而感到有点内疚外,他们似乎不感到什么苦。”常书鸿、史苇湘等顽强地留了下来。施萍亭说,那个时候,他们都是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如果想离开敦煌,易如反掌,但谁都没有这样做,甚至没有这样想。
时至今日,与其它地方相比,敦煌的工作条件、生活环境及各种待遇等还存在一定差距,可敦煌研究院的数百名研究者、讲解员、保卫人员等却长年坚守在大漠戈壁,甘于与寂寞和清贫为伴。“离开敦煌几天就会想敦煌。”仅仅来敦煌工作4年,魏丹已经成了新一代“打不走”的敦煌人。她说,院里很多年轻人同她一样,之所以选择在大漠戈壁扎根,除了敦煌艺术的召唤之外,还有一种精神在感染着他们。为了让“敦煌精神”世代相传,今年8月,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暨常书鸿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常书鸿铜像也永久地屹立在了大泉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