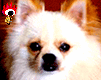张耀南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个追求“大智”、“大知”的传统,什么是“大智”、“大知”呢?从眼前与长远的角度说,能够看到长远的就是“大智”,立足于长远建立起来的知识系统就是“大知”;从局部与整体的角度说,能够看到整体的就是“大智”,立足于整体建立起来的知识系统就是“大知”;从自我与他人的角度说,能够看到他人的就是“大智”,立足于他人建立起来的知识系统就是“大知”;从人类与宇宙的角度说,能够看到宇宙的就是“大智”,立足于宇宙建立起来的知识系统就是“大知”。
儒家方面讲“大智”、“大知”,我们可以举荀子与张载作代表。荀子讲:“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知之在人”是讲“私理”,“知有所合”是讲“公理”;“私理”为“小”故有“知”之名,“公理”为“大”故有“智”之名。荀子又撰《解蔽》篇,专门论列“小知”之“偏”;又以“曲知”指称“小知”,认为任何一门具体的学问都存在偏颇,都只看到了“道”的一个方面,都是有“蔽”的。在张载的理论中,“德性所知”就是“大知”,“见闻之知”即是“小知”。张载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见闻之知”是“蔽塞”于某一领域、某一层次、某一时段的,故不能“大”。若能冲破“蔽塞”而“打通”各领域、各层次、各时段,就是张载所谓的“神化”。他认为“智力”指“小知”,“穷神知化”的功夫决不是“小知”所能勉强为之的(《正蒙·神化》),“知化”就是“以大知去打通”。“穷神知化”一段话,就是强调“大知”对于“小知”的优先地位的。他又讲到“合内外于耳目之外”(《正蒙·大心》)的知,这种知实际就是“德性所知”,就是“大知”。“小知”是“合内外于耳目”,以为“耳目有受”即是“有知”;殊不知这样的知只是一“偏”之知、一“隅”之知、一“方”之知。
道家方面讲“大智”、“大知”,我们可以拿老子、庄子作代表。我们解释老子所说“恒使民无知无欲也”、“绝圣弃知”、“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之类的话的关键,就是要区别“大智”与“小智”、“大知”与“小知”。老子反“小智”、“小知”,所以他有一个“反智论”;老子又主“大智”、“大知”,所以他又有一个“主智论”。老子讲“使民无知”,是无“小知”;讲“绝圣弃知”,是弃“小知”;讲“民多智慧”,是多“小智”、“小慧”;讲“将以愚之也”,是让民获取“大智”,因为“大智若愚”;讲“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是以其“小知”;讲“以知知邦”,是以“小知”治邦;讲“以不知知邦”,是以“大知”治邦,“大知”的特征是“不知”。庄子则提出了划分两种知的标准,他用“知有所待”(《庄子·大宗师》)来指称“小知”,待就是条件,就是前提。他又用“知无所待”来指称“大知”,无待就是无条件,就是无前提;而无条件、无前提的知识,就是“大知”。简言之,“小知”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时效;而“大知”却能超越一定的条件、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时效。庄子特别强调“大知”对于“小知”的优先地位。他批判世人局限于“小知”的立场,认为那是尊“小知”而弃“大知”,他称为“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庄子·则阳》)。
法家讲“大智”、“大知”,我们可以拿韩非、商鞅作代表。在韩非的理论系统中,“小智”即是不“圣”不“通”之智,其不“圣”不“通”的表现,就是“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简言之,就是因小失大、鼠目寸光。以此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民智”一词在韩非那里不是指“人民之智”或“百姓之智”,而只是“小智”的一个代名词。“中央”欲“厚民产”,“民智”以为“酷”;“中央”欲“禁邪”,“民智”以为“严”;“中央”欲“实仓库”、“备军旅”,“民智”以为“贪”;“中央”欲“禽虏”,“民智”以为“暴”。凡此之类,足证“民智”是见小而失大、见近而失远的一种智,足证“民智之不可用”,至少足证“民知之不足师用”、“民智之不足用”。说“民智之不可用”,确有“反智”嫌疑;说“民知之不足师用”或“民智之不足用”,却不能断然判为“反智”。“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韩非子·显学》)一句话,明白表达出韩非的追求:“小智”不足用,所以要“求大智”;“求圣通之士”就是“求大智”;因为“大智”正是以“通”为特色的。他还讲“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就是认为国家应当让有智慧有知识的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华,国家可以用他们的智慧来进行决断,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才能够拥有无穷无尽的智慧。这是一种“大智慧”。商鞅也有一些主智、主知的言论,如他讲:“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而知万物之要也。”(《商君书·农战》)又讲:“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商君书·靳令》)“知万物之要”、“知物之要”明显不是“反知(智)”的言论,至多只是反“小知”、“小智”。商鞅想要说明的是,圣人、开明的君主之伟大,并不在他们能够将天下万物全部都认识到,而在于他们能掌握万事万物的要旨,假如圣人、开明的君主能够掌握万事万物的要旨,他们就能够将天下治理好。
我们在现代社会研究“大智”、“大知”观念,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中国有没有知识论的问题。以“小智”、“小知”为基础,可以构建一种知识论;以“大智”、“大知”为基础,也可以构建一种知识论。中国古代思想家,既有“反智”的言论,又有不“反智”的言论,好像是自相矛盾的。其实只要我们区分大知与小知,这些矛盾的言论就可以很好地得到理解。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知识论,其实中国有中国的知识论,可以称为“大知识论”。西方的知识论只是人类全部知识论中的一种,不能说没有西方式的知识论,就是没有知识论。第二,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中国知识论的发展脉络。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大知思维”和“小知思维”的对立。在这个对立中,“大知思维”一直居主导地位;明末清初,西方科学思想传入中国,中国传统的大知思想才渐渐地萎缩,但也为迎接西方思想做好了准备。因为如果仍旧沿着大知的思维方式走下去,西方的科学思维将不能够为我们所接纳。这不仅因为传统社会视科学为“雕虫小技”,而且在大知的审视下,科学思想属于小知,属于不被人们重视的知识。第三,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弄清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看重的知识,是一种能够打通各科学的、贯通的知识。西方近现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科学”,在中国文化的“大视野”中都是“小知”、“小学”;“大知”、“大学”是超越具体“科学”的,超越的方式就是“打通”。换言之,“大知”与“大学”所追求的,是通行于天界、地界、人界的“公理”,而不是局限于某一领域、某一层次、某一时段的所谓“私理”。这恐怕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之一。第四,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追求。中国文化关于大人人格的观念,本质上包含“大知”、“大仁”、“大勇”三个层面。“大知”是根本追求之一。我们不能因为大知只是一个理想,就否定它的价值。对大人理想的追求和对大知的渴望,在现代仍不无它的时代意义。世界上也许永远找不到几何学意义上的圆,但人类可以一步一步寻找到接近于、类似于几何之圆的圆,人类会通过自己的努力逼近理想圆。中国文化对大知的追求,就是要找到一个理想中的几何之圆,找到一个超越学科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也许不存在,但努力追求它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