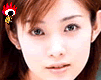《诗经》中的时间意识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8日15:15 人民网 |
|
张蕾 与西方人对时间的覃思相比,中国哲人更早开始了对于时间的妙悟。孔夫子从黄河滚滚东去不舍昼夜领悟到时间的永恒,庄子以“白驹过隙”喻指人生的短暂。这种对时间的诗性感受方式,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国哲学的诗意与情趣。追溯哲人的诗性思考,我们会发现《诗经》的导源作用。《诗经》以诗歌的形式传达了先民对于时间的感受与思考,从中可以谛听到个体意识由蒙昧朦胧向觉醒迈进过程中坚实的足音。 《诗经》中出现了大量的时间名词与时间副词,在诗人而言并非刻意为之,实在是基于先民对时间的深切感受。这种感受大致包括三个层面:时序感受、心理感受、生命感受。 《诗经》是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先民对时间的感受与农时、物候息息相关。大而言之,春秋代序为年,而“春”、“秋”、“年”的本义都与农业有关。在古人看来,季节首先意味着劳作收获,是他们的生命方式。小而言之,日出日落,月令交替,决定着先民的生活节奏。《豳风·七月》最为集中地表现了先民在时间流程中对于大自然的律动的把握。全诗按月排比,平铺直叙,非常适宜于表现时间长河的平缓匀速流淌。先民随着自然的律动呼吸,平静地接受自然的恩赐,“当耕而耕,当蚕而蚕,当作而作,当息而息”(黄熏《毛诗集成》)。《七月》正是通过逐季逐月地展示与之相应的特定意象,完成了这幅年年岁岁循环不已的风俗画卷。 与《七月》将喜愠消融于时序的写法不同,行役诗的抒情主人公感受时序则满腹牢骚。《小雅·采薇》前三章以植物的生长暗示时间的变化,“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刚止”,表明士卒滞留边地时间之长;“心亦忧止”、“忧心烈烈”、“忧心孔疚”是久役难归所产生的激烈情绪。末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诗句敏感于“往”与“来”中时序的变迁,生发出沧桑之感,以至“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将哀痛之情推向极致。 如前所述,时间或曰时间词本身并无情感因素,只有它与特定意象联系在一起才会触动人心,产生诗美。对于时间,不同心态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相爱的青年男女对离别时间的心理感受自会与他人不同,盼归的少妇对于黄昏的心理感受也异于常人。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将时间分为“内在的时间”与“客观的时间”、“世界的时间”,所谓“内在的时间”即根据主体自身的体验去把握时间,亦可称之为主观时间。《王风·采葛》、《郑风·子衿》“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的诗句绝妙解说了客观时间与主观时间的区别。至于《王风·君子于役》首次将“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的黄昏景致与伤别念远联系起来,正是盼归少妇对于黄昏时节的独特心理感受所致,这种心理感受经过后世诗人不断的体味与复现,无疑具有了原型的意义。正如清人许瑶光所言,“已使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黄昏”。“黄昏意象”作为文人对于时间的独特心理感受长久地留在古典诗词中。又如黍离之痛亦具有原型意义,它的产生恰恰也基于时世变迁对诗人心理造成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时间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先民从对时间的感受中体悟了生命的存在。时间的漫长越发反衬出个体生命的短暂,时间的易逝又促使他们思考如何增加生命的密度,提高生存的质量。这种思考使《诗经》不惟停留在具体感性的抒情叙事层面,某些诗篇还蕴含着哲思的萌动。比如蜉蝣是一种朝生暮死生命极为短暂的昆虫,诗人由此联想到了人生,蜉蝣因之具有了象征意义。《曹风·蜉蝣》接连三章,反复咏唱“心之忧矣,于我归处”,“心之忧矣,于我归息”,“心之忧矣,于我归说”,可见焦虑之深。因为诗人已经认识到人生的归宿与蜉蝣的归宿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生命不可逃避死亡的规律。 随着先民对于生之无奈的意识由朦胧逐渐明确,他们的心灵便不断地被焦虑所困惑,如何寻求缓释与解脱焦虑便成为先民时常考虑的问题。他们思考的结果是,立足当下,及时享乐,以乐消忧,即《秦风·车》所谓“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今者不乐,逝者其亡”。及时行乐的思想正是在岁月易逝的残酷现实催逼下产生的。如果联系时间意识的觉醒来看待及时行乐思想,其合理之处正在于为时间焦虑找到了缓释与解脱的对策,不失为一理性地应对人生的态度。 在时间的三个维度即过去、现在、未来之中,先民最为关注的是现在。因为抓住了今朝、今日、今夕,生命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古代史诗的不发达,除了过早确认了诗歌“言志”的单一功能之外,或许也与先民历史意识淡薄,对于“过去”这一时间维度的忽略有关。《大雅》中的史诗都带有祭祖性质,或许可以解释为只有在特定的时日,先民才会怀着宗教的虔诚,推移历史时间,而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它们更瞩目当下,充分感受正在行进的时间流程,品味具体实在的“冬之夜”、“夏之日”带给他们的苦与乐。 孔子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概括《关雎》,这一经典的评点被视为《诗经》的整体基调,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主要的美学倾向。先民对于缓释时间焦虑所作的思考也未越出这一底线。因此如果将表现先民时间意识的诗篇拾掇起来做一个整体观照,就会发现及时行乐决不指向放纵情俗,堕入享乐主义深渊无力自拔。在宣扬享受当下的同时,又不忘乐而有节的警戒,这种辩证思维是先民理性意识深化的反映。《唐风·蟋蟀》等诗对于时间的那种隐隐焦虑,到了《离骚》中则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时间意识流贯《离骚》全诗。如果说《诗经》中的时间意识开启了后人对生命意识的思考,那末《离骚》则进一步将伤逝主题与功业意识联系起来,从而对时间的思考更为凝重。而先秦哲学家尤其是道家融通宇宙的审美襟怀则又使诗歌境界进一步开拓。后世绵延不绝的对于生命的喟叹,便是它们合力作用的结果。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一面高唱“为乐当及时”,一面又低吟“立身苦不早”,到曹操将“人生几何”的慨叹导向“天下归心”的期盼;从张华“功名宜崇速”的渴望到陆机“日归功未建”的惶恐;从阮籍“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的无奈,到陶渊明一面饱受“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的痛苦煎熬,一面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旷达予以排遣……一部古典诗歌史从主题学角度看也构成诗人贤哲对于时间意识不断强化与深入的历史。而在这部主题诗史中,《诗经》同样处于源头的地位。(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光明日报 日期: 2004年10月27日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