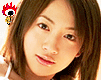朱亦兵 把家打包回中国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1日18:21 青年时讯 |
|
2003年12月初决定回国,2004年2月27日踏上行程。告别生活了21年的欧洲,六张飞机票买给四个人和两个大提琴…… 生活在龙卷风中心 从今年二月底到现在,朱亦兵回国八个月的时间。回想这忙碌的八个月,他数着指头总结:“告别21年的海外生活、布置这么大一个家、两个孩子和学院内外的很多工作。”但这些不是朱亦兵的目的,他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的生活和活动范围。 朱亦兵特别喜欢乱,他的乱指的是规划上很差。而他自己,就好像在龙卷风中心最安静的角落。“周围越乱我越不乱,周围越忙、越嘈杂、越毛躁,我越坦然,越能坚持自己。我做事的目的要尽量在短时间内,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活动范围。” 这种有的放矢的状态被朱亦兵比做下棋,“国际象棋的最低目标,就是吃掉对方的国王。目标和棋艺高低没有关系,即使我棋艺不高,最起码的宗旨我也知道。要是下中国军旗,最高的目的就是把对方的军旗翻出来,夺别人军旗,否则你不知道炸弹在哪里炸,工兵怎么派。” 朱亦兵认为,目的和追求不是完全一致的概念。人的生活、事业和他所要走的道路……都是应该有一定的追求的,在追求里面包含一些目的。追求和目的是生活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把两个东西经常联系在一起,形成逻辑,那生活会很有意思。” 听爸爸讲将来的事情 朱亦兵在追求自己文化的根源,这种追求和他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大关系,父亲朱永宁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也是朱亦兵出国学琴前的老师。“我父亲是音乐家,是一辈子为了大提琴演奏和教育事业付出了一切的人。但是可以说根本没有条件和机会实现他的事业理想,虽然他是非常有能力的音乐家、演奏家。所以可以想像他在我身上投入了多少心血,他不仅是家长还是老师。他一辈子的理想、计划都下意识地寄托在我的身上。”父亲不仅告诉朱亦兵音乐怎样演奏,也告诉他很多现在才懂得的道理。“那时候我不懂,而且也不听他的,因为他讲的都是将来的事,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讲以后的事情。” 虽然出生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八岁才随父亲学琴,但朱亦兵的生命一朝开始和大提琴产生交集,就放出异彩。1976年5月1日,十岁的朱亦兵参加北京少年儿童文艺汇演,得到优秀表演奖。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西洋乐器在台上演奏是件非常轰动的事情。那年汇演的优秀作品在北京巡回演出了100多场,朱亦兵的母亲在幕后为他钢琴伴奏,他一个小孩子独自在大舞台上表演。13岁的时候,朱亦兵在中国唱片社录制了一张独奏唱片,是中国“文革”后第一张有外国作曲家作品的唱片。朱亦兵说,“我觉得我那时候的大提琴演奏是我一辈子最炉火纯青的,神童都有高峰,无论从演奏技巧到音乐的感觉都没有再超越十二三岁的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朱亦兵和妈妈在家里合作练琴的一段录音,辗转传到国外,大提琴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元老,法国的皮尔弗涅大师,通过很多外交途径回信说他非常感动,而且惊奇得不得了,他要这个小孩子一定到欧洲学习,由他负责一切费用。 这样的信来了好几封。直到今天,朱亦兵还清楚地记得父亲给皮尔弗涅大师回信的内容。朱亦兵还能一字一句地背出来:“谢谢您的关照和赞赏,我们拉大提琴的后辈们一辈子敬仰您、崇拜您。但是我的孩子现在还太小,他得在中国高中毕业,他首先得具备最起码的中国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以后他要去哪里我都不会拦着。我现在非常理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得先做一个中国人。” 学会做个幸福的人 17岁高中毕业以后,朱亦兵考入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但有个疑问曾经纠缠了他很多年。20岁到30岁的阶段,朱亦兵一直有过这种疑问,我如果当时出去,在大提琴演奏上可能比现在有更好的成绩,这个想法延续了很多年、演变了很多年,“我总想为什么他会拒绝,父亲一生对我有这么大的寄托、热情和投入,而且他自己为了大提琴事业可以贡献一切,更别说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后来我才想通了,而且真正明白父亲的意愿,这也就是我回国教学和今后的追求、目的和计划最主要的出发点。如果当时命运不是这样走的,父亲不是这样决定的,我不会坐在这里,我不会回来。” 朱亦兵解释:“如果要一个人13岁出国,从这么小开始让他在国外20多年,那么不知道他的语言会往哪边倒。因为这个阶段最重要,而且非常敏感,一个人这时候开始确立自己文化体系的根基,虽然还没有完全站稳,但是已经开始。成人,是说这个时候你有选举、结婚等很多权利,但这不只是生理上的成熟,在心理上、文化上的成熟更重要。那么如果我13岁出去,我最重要的几年就不是在中国文化里成型,我就不会想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源头。” 朱亦兵毫不掩饰对父亲的尊敬,他说父亲当时的想法,毫无疑问是很有远见。“虽然我们没有沟通,我肯定我父亲为我做这个决定时候想的是,我为自己的孩子做出决定,他将来一定是个幸福的人。 有的人可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明星,成为音乐家,非常光彩。但我父亲的想法是有更高的境界,是我刚才说的东西,是真正的智慧。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毫无疑问特别大,你知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后,你去做什么事就不重要了。我父亲一辈子投入到艺术中,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让儿子做一个大提琴家、艺术家,而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家庭就是要在一起 回国是朱亦兵在一刹那间冒出来的想法,但却是从下意识演变到有意识,是蕴涵在吃饭、看报纸、看电视的普通生活里一个长期演变过程。“说白了就是感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觉开始不对了,人说一杯水是一滴一滴水积成的,最后总有一滴水要溢出去的,这里有很多很多原因。” 朱亦兵全家定居在瑞士,那里是“世界上最美的花园里最好的地块上最完美的一角”,条件非常优越,朱亦兵的一双儿女在那里出生长大。女儿今年七岁,正好是入学的年龄。上学就是走向成人、走向社会的第一步。这个时候,朱亦兵开始认真考虑举家回国。“我们确实在想,如果我们有一天要回到中国,应该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想再过30年在哪里过日子?我们现在30多岁就开始养老,生活的确优越、懒散,不好的一面就是人开始胡思乱想了。” 多年受父亲教育的成长过程,多年以来对出国问题冷静的看法,从朱亦兵的潜意识里跳了出来。“如果我能为我的孩子们掌舵,那是什么时候,难道是他们在国外长大以后。忽然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紧迫感,因为这是不容你犹豫的事情,孩子上一年级、二年级……初中、高中,时间过了就过了,容不得你等一段时间再考虑。一个表面上是自发感觉的事情,但突然间进入了一种你无法脱身的逻辑,如果你尊重你自己的逻辑,那这个逻辑就意味着:回国。” 2003年12月初决定回国,2004年2月21日全家踏上行程。告别了21年的生活,六张飞机票买给四个人和两个大提琴。海上还有一个40英尺长,装着239个大箱子的集装箱走了七个星期。除了房顶的灯和窗帘,朱亦兵现在北京家里的一切,细小到烛台、花盆、台灯、碟子都是从瑞士带回来的。 朱亦兵说:“孩子的环境很好,很幸福地在这里上学,受这里文化的熏陶。我认识的很多海外朋友,也意识到孩子的教育很重要,有很多人已经把孩子送回来学习。但我觉得如果孩子在这里学习生活,我们也要在这里工作生活,找到家庭的重心在哪里,然后一切要围绕这个重心,我觉得一个家庭就是要在一起。” 朱亦兵说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喝绿茶吃豆沙点心。一不小心,你差点忘记他有在海外生活21年的经历,可马上,他又用流畅的德语、法语和朋友聊天,点心碟子旁边放把精致的小叉子。所有时空的转换在他身上融合得如此默契。 缘起: “朱亦兵和朋友们……”归国专场音乐会的节目单是朱亦兵自己设计的。一张放在节目单封面的老照片,是1970年中央音乐学院幼儿班的合影,4岁的朱亦兵顽皮又略带羞涩地笑着,除了精彩的音乐本身,更让人看到这次演出背后主人公生命历程的回归。朱亦兵很用心地去做,“我花了很多时间说服设计者要用这张老照片,因为很少有人这么做,一开始他们觉得这么做不会让人接受。但我坚持了,因为节目单也代表了我的心意和感觉。”演出前几天的一个偶然机会,朱亦兵的朋友把这张照片送给他,“我一下就知道它该放在什么位置,我说就是它了。”照片的背景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大礼堂,也是朱亦兵和朋友们这次演出的地方。 让朱亦兵遗憾的是,这个细节他没有在节目单上标示出来,“因为我觉得太自然而然了,所有音乐学院的人都知道那是大礼堂。用它放在封面有两个意思,第一是因为照片的背景,第二是它所代表的年代。背景和年代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的根。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背景和年代,每个人都有他的根。毫无疑问我的根就在这儿。” 不习惯没什么了不起 生活中除了音乐,朱亦兵还钟爱各种电子游戏,“生活本身就像游戏,真正的游戏里不光有美好的东西,也有很多残酷的东西,和生活一样,有快乐、满足也有灰色、无聊。生活里消极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你总能从生活的大游戏里找到很多有乐趣的东西。” 朱亦兵一直就是这样积极待事,虽然刚刚回国,不习惯的东西很多,但他说,“我17岁到国外,在国外生活21年,在外面到现在都还有不习惯的东西,但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现在也在享乐,人应该这样才对。如果把你放在人多的地方你才觉得热闹,如果让你学有用的东西你才觉得有意义,就没意思了。我们搞音乐的人从小就都有很辛苦的经历,从最小的时候,可能有人三四岁就开始练习,别的小孩都在玩,我们就坐在家里练琴,每天很多个小时,很苦。再比如巡回演出,也是非常辛苦,但另一方面也很满足,我很幸运和世界最顶级的乐团在一起,我们受到的待遇很高。我遇到的经历是最好的,对于一个乐队乐手来讲,是最美满的最享受的,最辛苦的同时又是最满足的。” 让聪明人学会放弃 2003年9月,朱亦兵20年来第一次接受中央音乐学院的邀请回国讲学。虽然每年都回北京,但是朱亦兵从来没有以专家、教育家的身份回来。这次经历让他感受很深,“我看到中国的发展,这些年轻人确实很聪明勤奋,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对前途的关心让我感到十分震惊。这些都是我们当年离开中国时候不存在的现象。他们希望追求的理念、渴望的理想,但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被满足。”对于有教育理念的演奏家朱亦兵来说触动很大,他反复说:“我就是干这个的,你明白么?如果我人在国外,国内有人有需求,但我无能为力。所以这滴水很重要。” “一般说人生活的成功是靠勤奋和思维,我不赞成这个观点。我们的下一代,这些年轻人不缺乏勤奋、思维,但他们有时候缺乏的是心态,缺乏的是一种坦然。”2003年9月,朱亦兵回国讲学就意识到问题在这里,“他们在勤奋、在彷徨,但是找不到出路。搞音乐离不开灵感和感觉,虽然坦然不一定就能带来某种灵感,但也有很大的关系。不是任何东西都是在强烈的期待之下就能得到,有的时候至少你可以放弃而不是等待,有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在放弃的同时会有其他的所得,所谓感受。” 朱亦兵经常告诉学生,不要期待在生活里你接触的东西都是可以拿来就用的,人的知识不是学了就有用的,人的想法从下意识变成有意识就是个很长的过程。千万不要轻视你一时觉得没有用的东西,要学习,很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你就非常需要它。如果是什么有用学什么,什么赚钱学什么,哪里人多去哪里,别人干什么你干什么,那你永远是在跟着别人走。 放出笼子里的音乐 朱亦兵说自己对东方西方两种文化都有深刻理解,中国的习惯和文化传统,外国人有很大误会或者不理解,我们对国外的文化也一样。朱亦兵认为,这种真正文化上的、感情上的一种教育理念的沟通还非常欠缺。这种沟通也是他搞文化活动和在艺术上追求的东西。 现在,朱亦兵带10个大提琴学生、120个选修课学生,还要指挥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教学任务非常重,与在国外以商业演出为中心的生活有很大不同,朱亦兵坦言:“我不想太多上台演奏,我想搞一些文化上面的活动。为了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古典音乐,这是我渴望达到的目的。”在朱亦兵眼中,西洋音乐就像是关在笼子里的熊猫,虽然是宝贝,但是被关起来。“我要把笼子打开,这是我的想法。虽然很多人不理解,但我的一切理念都是从这里出发。” 10月23日举行的“朱亦兵和朋友们……”归国专场音乐会,各行各业的人都来了。“我很幸运,因为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很多人从前不知道音乐学院在哪里,或者很多没有看过音乐会的人也来了。一个艺术家这样做,有些人不理解,说把这些学法律的、做设计的、搞政治的人找来,他们懂么?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对音乐的享受和热爱,这个价值远远超过追求音符、乐曲这些细节。就比如说我们到美术馆里去看画展,难道只有是专业搞画画的人才能欣赏一幅画的艺术境界吗?” 朱亦兵认为其实音符、曲目、弓法等等本身并没什么意思,“好像朋友、同事、亲戚一起去吃饭,仔细考虑一下,到底我们是为了团聚还是为了吃菜,结论当然是前者。搞艺术也一样,不是为了钻研几个音符和曲目,它们本身确实有欣赏价值,但它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艺术是传播人类情感的东西,是为了让大家从不认识到走到一起,让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走到一起,这是我的理想。” 给演奏一份说明书 朱亦兵对各种机器都感兴趣,每本说明书他都习惯看到最后一个字,直到对所有功能了如指掌。朱亦兵体会它的理念,在体会和理解之后得到自己的结论。机器说明书的理念有时候是错误的,它本来是要给人启发,要告诉别人这个机器有什么功能,是做什么用的,但是有时候它自己都说不清。 联想到自己的事业,朱亦兵说:“舞台下是我的观众,但是我不希望我上台以后,演奏几个曲子,结束了他们就散场。就好像没有说明书,没有理念、没有解释,观众就不理解。机器如果没有说明书,人们就不知道机器是做什么的。所以我为什么演奏这个曲子,拿这个东西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音乐档案· 1966年,出生于北京。1974年,开始学习大提琴。 1983年,考入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 1986年,在瑞士日内瓦第四十二届国际大提琴比赛中荣获第四名和瑞士作品特别表演奖,成为在重大国际大提琴比赛史上获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1989年,考取欧洲优秀乐团之一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是当时欧洲交响乐团中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也是至今在西洋一流交响乐团担任此重任的惟一中国人。 1997年,考入巴塞尔音乐学院学习指挥。 2002年,开始正式指挥欧洲乐团,指挥过德国慕尼黑、哈莱等甲级交响乐团。 2004年,受中央音乐学院聘请,回国担任大提琴教授。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