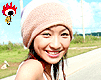|
科学在中国的悲哀陶世龙徐霞客的不幸还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引出的问题:既然古代中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什么后来却落后了?,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不存在,因为本来在科学上就没有领先过。或者说研究这个问题会徒劳无功。都有道理,不过我想,无论原先是不是领先,现在落后的是事实,认识造成落后的原因,很重要,因为如果认识不清,就不能去消除那些障碍科学发展的因素,甚至还可能把它们当宝贝。事实上这个问题已讨论很久很多了,开了不少会,专家们发表了许多文章,印出的书一大摞,我在这里是班门弄斧,讲不出什么理论,仅仅是就一些具体的人和事,谈谈我的认识。时间是1987年,纪念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的活动正在热闹地进行。一天,在侯仁之先生家中闲谈。侯先生突然感叹地说: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徐霞客早于德国的洪堡(1769-1859)那么多年,但自然地理学并不是中国首先建立?是呀!怎么过去就没注意。我说:侯先生你来一篇。他说,你要有兴趣,你写吧。回去就查书,把洪堡的经历和徐霞客对照。我发现,就个人的聪明才智、精神毅力而言。中国人决不比西方人差,徐霞客就是代表;今天在此所见,美国一年一度在高中生寻求科学人才的竞赛结果,前十名一般总有三、四人是华裔;加拿大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比赛的代表中也少不了有几位华裔青少年,都大大超过华人在这些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数,也是证明。所以,我认为科学未能在中国生长起来,不是个人的基因有问题,而是他所处的环境,也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没有适于科学种子生长的条件。将徐霞客的遭遇与洪堡一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两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有探索大自然的高度兴趣和献身精神,有高于一般人的观察记录能力;多次去野外考察,均有一次长达四五年的旅行。再就是都继承有丰厚的遗产,不仅不用操心油盐柴米酱醋茶这些事,还有钱去做花销很大的自费旅行。别的方面一比,徐霞客就差远了。洪堡出去考察前,在弗莱贝格矿业学校上过学,在那里学过地质学;地质学成为一门课程,就是洪堡六岁那一年在这个学校开设起来的。开这门课的魏纳被公认为地质学的奠基人,尽管他提出的水成论有许多谬误。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德国,老地方,仍使用原来的名字,没有“升格”成大学或与别的大学合并。徐霞客青少年时学的是四书五经,那时程朱理学的道统已经成为主流,八股文统治文坛和成为进入政坛必不可少的敲门砖,徐霞客算是看的透,不愿去做“举业”即参加科举考试,而走向山野,考察自然,但在知识上做的准备。最多是看点古今史籍、舆地志、山海图经;而且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落进了唐太宗设下的这个圈套,钻在故纸堆中苦读,希望能像范进中举那样走上升官发财的道路,谁会和他一起去干这种蠢事。因此徐霞客出游,常只有和尚与他作伴。而洪堡那次长途旅行则有法国一位植物学家和他同行。洪堡从美洲考察回来,住在当时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巴黎,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整理考察所得,不惜巨资自费出版了《1799-1804年在新大陆热带地区的旅行》,计三十卷。徐霞客则在时间最长的一次旅行结束后,不到一年就病死在家乡,江阴马镇南炀岐,(图,徐霞客故居,据网站“走遍万水千山”)遗稿未及整理,复经兵祸残缺,等到他的子孙整理刊印出来,已换了朝代,是一百三十五年后,即清乾隆五十二年的事了。洪堡在他的考察成果出版后,于1827年回到柏林,登上大学讲坛,培养了一批学生,他建立了自然地理学,有人承传,得以发展。徐霞客无此幸运,即使他不早逝,游记或许能早点印出,但又有谁会去从他学习,也就是到他为止。洪堡的考察成果在欧洲受到高度重视,俄国沙皇也慕名邀请他去考察西伯利亚的矿产资源;在他逝世后,普鲁士摄政王下令为他举行国葬,全柏林居民为之服丧。徐霞客的游记刊行后,也曾引起不少文人墨客的惊叹,但最多不过是作为奇书以供卧游而已;他死后二百七十三年,才有地质学家丁文江发现这本游记的科学价值。也许有人会说,霞客条件不好,那是他比洪堡早生了近两百年年。但是晚生一点又如何呢?洪堡出生时是清朝乾隆三十四年,正是八股文加上文字狱兴起的时期,手头缺少历史资料,有本剪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翻开一找,在洪堡出生后就找到两条,乾隆四十三年,洪堡九岁那一年“九月,徐述夔诗狱起。十一月案结,本身戮尸,子孙斩监候”。三年后,又有“尹嘉铨文字狱起,旋被处绞”。年表能级下的事件是很有限的,按故宫保存的清文字狱档案,乾隆年间,有三四十起,对思想的控制比徐霞客时代更严密,再没有第二个徐霞客出现。文字狱是大棒,也有胡萝卜。“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高在何处?在当官,这叫做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都是靠读书作官来实现的。事情就如蔡元培曾经指出的,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开辟了通过读经可以做官的“利禄之途”,以后发展为科举制度,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便入其彀中,把聪明才智都耗费在读死书上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1940,良友图书公司初版,1982,上海书店影印,第3页)明、清用八股文开科取士,把这个制度控制思想,扼杀创造精神的作用,发挥到极度。科举制度使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有出头的希望,诱导知识分子去白首穷经,读死书,死读书,直至到读书死。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都出现在先秦时代,后世仅能拾其唾余,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明清,更无足取,都说明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特别是科举及与其配套的一系列的制度,对控制思想、维护封建秩序起了重大作用,我以为这是科学不能在中国生长起来的首要原因。科学是人创造出来的,学而优者都当官去了。没有人去研究创造,何来科学?特别是中国的治学传统,讲究坐而论道,内省以求诸己。宋代的程颢和朱熹,将《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解释为就“物”的本身去了解“物”,有点到自然世界中去认识自然的意思。朱熹自己大概也真的作过一些观察,所以能注意到“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推论出:“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为高,柔者变而为刚”。(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1986,中华书局据清光绪六年(1880)传经堂本点校重排本,第六册,页2367)解释了化石的形成,成为主张中国古代就有科学的证据,但他们说的这个“物”,是把人的主观意识也包括在内的,而且着重研究的还是人的精神世界,对自然界并不重视,而且也没有“格”的方法。一个引用很广的故事是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格”竹子,他在竹子旁边坐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得到,就放弃了。而这个“物”到后来也仅剩下所谓“心”,即人的主观世界,更与科学不沾边了。先秦以后的中国学者,最擅长的是就前人的经典做文章,从书本到书本。在人文学术方面,还有人去做些社会调查研究,为数也不多。更难得有人肯象徐霞客这样到山野中去考察自然。难怪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要说,中国学者做别的学问还行,做地质学不行,但今天的事实已证明中国人其实是能做的,问题出在这个社会推行的制度和因而形成的学风。一旦把这些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桎梏消除,中国学者在探索自然,发展科学上的潜力一定是很巨大的。徐霞客的不幸,非仅他个人的不幸,也放映了科学不能在中国生长起来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