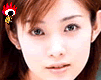数学大师、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的最后岁月 (组图)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9日16:16 新华网 |
|
为表彰陈省身对人类的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来源:金羊网—新快报数学大师陈省身。来源:法制晚报 12月3日晚上7点14分,93岁的陈省身,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微分几何之父,永远停止了美丽的计算。 他的数学,至美,至纯。 他的一生,至简,至定。 陈省身,世界级的数学大师。 陈省身开创并领导着整体微分几何、纤维丛微分几何、“陈省身示性类”等领域的研究。他是惟一获得世界数学界最高荣誉“沃尔夫奖”的华人,被国际数学界尊为“微分几何之父”。 他曾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建原中央研究院数学所、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南开数学研究所。 2000年,陈省身定居南开大学。他殚精竭虑地为把中国建成数学大国贡献了毕生心血。 本报驻京记者 徐 彬 12月3日,从早晨一直到下午5点,陈省身的病情都显得很平稳。他静静睡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一间单独的病房里,神态宁静而安详。他的女儿、女婿,南开大学数学所的几位弟子,还有常年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几位工作人员,不时蹑手蹑脚走到他的床前探望。 从11月30日开始,死神就频频想带走这个顽强的老人——他的心脏,出现了两次剧烈的心房颤动,血压最低降到了63,他多次昏迷过去。而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心脏方面的病症。他也从来不喜欢看医生,像一个孩子一样不喜欢医院的味道,甚至每次体检都要南开大学的校长亲自做半天动员。 真的是老了。在11月25日,他居然主动打电话给他的保健医生,说“我要去看你”,但当时的心电图检查并没有发现问题。到了29日上午,他的护工发现他没有什么精神,也不爱说话了,便赶紧叫医生过来检查,发现他的血糖和心肌酶指标都很高。在大家的劝说下,这一次他才住进了医院。 昏迷,然后是略微清醒一点,再是昏迷。先生在弥留之际说,“我要走了,我要去数学的圣地——希腊报到了。” 12月3日晚上7点14分,93岁的陈省身,这位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微分几何之父,在自己心脏错误的运算公式上打上了一个红色的叉号,永远停止了美丽的计算。 这一刻,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陈省身星”依然在太空闪耀。 一篇未完成的论文 就在11月中旬,他还不断约人到他家里去谈他最关心的4个数学难题,当时他声音洪亮,争论起来精神头十足。 “我很后悔,我们当时应该劝他少做一点、少想一点。每个人都去跟他谈一两个小时,去的人多了,更激发了他研究的热情,这对他的健康是很不好的。”南开大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讲座教授汪徐家事后说。 这4个数学难题,是他在今年10月29日的小型生日聚会上提出来的。头一天,他刚刚过完93岁的生日。他要把这4个题目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并提议大家每三个月碰一次面,每次开两天会,他要亲自给大家做报告,交流最新的研究进展。 其中有一个是六维球面上复结构的存在性问题,他的弟子张伟平称之为“如果谁能在40岁之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就有可能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是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规定只颁发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 “每一个题目都足够耗费一个年轻人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要一辈子来研究,而他同时要考虑这4个重大问题,真是让我们汗颜。”汪徐家说。 对于“六维球面”问题,陈省身留下了一篇未完成的论文。他的生活秘书胡德岭回忆说,在去年SARS期间,为了避免传染,天津市政府和南开大学校方都下达了“禁客令”,任何人都不能拜访陈省身。那段时间,陈老很少下楼,潜心于论文的写作。 初稿出来后,陈省身把文章寄给同行评议。他说以前的文章都是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现在回国定居了,准备把这篇文章投给《中国数学年刊》。遗憾的是,同行反馈回来的修改意见还没有最后完成,他就匆匆离去了。 “他是这段时间体力透支了。”12月6日,在去迎接前来吊唁的陈老生前好友的路上,张伟平还在深深自责。 不光是4个数学难题,在发病前的最后几天,老先生还急着找校方商量建高级学者公寓的事儿。他拿出了在9月份获得的100万美元“邵逸夫奖”奖金,“要建一个和杨振宁一样的高级公寓,能够吸引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前来工作。” 地点选好了,他的担心又来了。11月29日下午刚刚住进医院时,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侯自新校长说,光有好的大楼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的数学。 “放心吧,放心吧,侯校长都清楚了。”工作人员说,他们想让老先生早点休息,可是,侯校长还没走出病房的门,就听到老先生在自言自语:“哪有这么简单?我就是放不下这个心啊。” 这一段对话,可能是老先生在神智清楚时留下的最后遗言。 几何之家 12月6日,阳光终于扫去连日的阴霾。离新开湖不远的宁园,台阶旁,摆放着一些吊唁者送来的菊花,一位学生在纸片上写着:愿陈爷爷一路走好! 宁园,校园东南隅的这座浅黄色的两层小楼,绿树掩映,草木环绕。陈省身1970年代开始频繁回国,自2000年回南开大学定居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门前是一斜坡道,汽车可以直接开上去,也便于陈老的轮椅行进,这样富于人性化的设计,能看出人们对陈先生的尊敬与爱戴。一楼是一个大客厅、厨房和餐厅,二楼除了他自己的卧室和书房外,还有专门的客房。他要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高朋满座的“几何之家”,要让客人能吃能住,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几年来,这个“几何之家”的确成了一个高级招待所。杨振宁、林家翘、彭桓武、杨乐、王元、吴文俊都曾被邀请到这里做客,他们有的住上一个晚上就走,有的一住就是三四天,述述友情,聊聊数学。 他的一个愿望就是推动中国成为世界数学大国。他希望20年后,南开可以成为国际数学中心,就像当年的普林斯顿一样。他曾套用陆游的诗说:“一朝数学大国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许多有前途的中青年数学家就是在这里决定了为南开工作。“我来南开大学,完全是因为陈先生。”汪徐家就是其中之一。 “他有这个凝聚力。”从事数论研究的王元院士说。 但宁园的客厅里没有一只沙发,只有很硬的椅子。工作人员说,这是老先生的主意,“坐在很软的沙发上,容易在一些无用的话题上聊很久。” 不过当这些椅子上坐的是年轻学生时,“无聊的话题”便常常聊起,老先生特别愿意和年轻人谈天说地。很多学生都记得,老先生在对他们说“你们现在的年华是最好的年华”时那幅羡慕不已的样子。 在客厅里还有一块小黑板,老先生常常在这上面向这些学生表演“魔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数字在互相抵消后,最后只剩下一个非常干净非常完美的结果。在这个时候,老先生就回过头得意地盯着这些学生看,等待着他们发出会心的微笑。 “不怎么要紧”的陈省身星 今年6月,陈省身获得邵逸夫奖的100万美元奖金以后,说,“这个钱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所以我把这钱都捐掉就是。我就捐到从前对于我的这个工作、对于我的念书有些好处的,我去过的学校,我去过的研究机关,南开我也捐钱,我们盖盖房子。” 他给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数学研究所各捐了10万美元。他说,这样以后中国科学家去他们那里时会得到方便。 他帮助过很多人。每年,他都用自己的经费选拔一批优秀人才出国深造,而且都是送到世界数学领域最有名的大师身边去。他介绍了很多人去美国。每次他都会说,你要回来哟。但别人即使最后没回来,他也不会去骂。 看到某个年轻的华人数学家有成绩,他就会动一番脑筋,觉得谁强就要去动员他回国。就在11月底,一个喜讯传到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数学所年轻的龙以明教授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这是世界数学领域的崇高奖项,在该奖历史上的5位中国获奖者中,南开数学研究所占了两位。龙以明和前一个获奖者张伟平教授都是陈省身先生从国外“挖”回来的数学家。 他时常请国内外一流科学家来讲学。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他甚至开始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他有一个观点,好的教授好的科学家就是要给本科生上课。他非常认真,一学期中只停过一次课,患感冒还坚持上课。一名学生回忆说。“一接近才发现他是个那么和善可爱的老人。” “陈先生的人格非常完美。”为他写了传记的张奠宙说,“他没有敌人。” 11月2日,国际小行星联合会小行星中心向世界公布,将中国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所发现的永久编号为1998CS2号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以表彰他对全人类的卓越贡献。 11月11日,在宁园,陈省身接受了央视东方时空的采访,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接受采访。 记者:有一颗小行星用您的名字命名了。 陈省身:是的。 记者:以后就有一颗陈省身星了。 陈省身:小得不得了。 记者:您把这个看成是一个特殊的荣誉吗? 陈省身:得了荣誉,这个热闹热闹,看见几个有名的人也有意思,好玩。 记者:好玩。 陈省身:好玩就是,不怎么要紧。 (南开大学新闻中心张国对本文亦有贡献) 陈省身的“微薄贡献”——第一个占领近代科学重要位置的中国人(本报驻京记者 李虎军) “听到陈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都很难过。”著名数学家、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阿蒂亚(MichaelAtiyah)爵士在周一告诉记者。阿蒂亚认为“陈省身的一生非常成功”。 几个星期以前,刚刚度过93岁寿辰的陈省身,还在他一手创建的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作学术报告,讲述着他对“六维球面上的复结构问题”这个著名数学难题的研究进展。 老骥伏枥的陈省身,同时关注着芬斯勒几何和外微分方程等数学课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前院长格里菲思(PhillipGriffiths)今年9月访问南开时,两人就讨论起了陈省身晚年最感兴趣的芬斯勒几何。 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最后一次见到他的老师是在今年11月14日。“那天下午,我们谈到了好多数学问题,陈先生精神相当好。他走得太出人意料了。”吴文俊说。 像陈省身这样到了如此高的年纪,仍然活跃地思考数学问题,“是绝无仅有的”,菲尔兹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告诉记者。 “我的微薄贡献” 丘成桐说,陈省身最主要的工作是在30多岁时做出来的。 “陈省身发表的数学论文很多,其中最惹人关注的有两项:一是‘高斯-博内公式’的内蕴证明以及陈类的提出,开创了整体微分几何的新纪元;另一项是后来在世纪之交成为研究热点的陈省身-西蒙斯理论。”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张奠宙在他新近出版的《陈省身传》中写道。 1943年,陈省身抵达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随后在那里完成了他引为平生最得意之作的“高斯-博内公式”内蕴证明,以及另一项不朽的工作:构建陈省身示性类。正是由于陈省身这些杰出工作,大数学家霍普夫1946年在《数学评论》上撰文称:“微分几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一个中国人由此在国际科学界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丘成桐评价说:“陈先生是第一个占领近代科学重要位置的中国人,比杨振宁他们要早。”张奠宙也告诉记者:“陈省身开创了整体微分几何的新学科,其影响波及整个数学,当代中国能作出如此重大科学贡献的,陈省身应该是第一人。” 杨振宁曾经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而陈省身对此深有同感:“我的微薄贡献是帮助建立了中国人的科学自信心。” 陈省身-西蒙斯理论是陈省身63岁时与西蒙斯JamesSimons合作的成果,这大概是他保持旺盛创造力的一个证明。后来,西蒙斯离开了数学界,改行经商,成为了掌控数十亿基金的大老板。2003年春天,西蒙斯曾租用个人包机,专程从美国飞到中国看望陈省身。 复兴几何学 二战以后,许多人认为微分几何已经“死”了。 1949年夏季,陈省身应芝加哥大学数学系主任斯通(MarshallStone)之邀担任该校几何学正教授。在芝加哥的十年,陈省身周围聚集了一大群极其优秀的学生,包括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做教授的辛格(IsadoreSinger)。辛格与阿蒂亚共同提出的阿蒂亚-辛格指标定理在科学界闻名遐迩,二人因此在今年分享了约70万欧元的阿贝尔奖。 辛格在庆贺陈省身八十寿辰的文章中曾回忆说:“在陈省身的影响下,很多书出版了,学科繁荣起来了。我无需在此强调众所周知的事实:陈省身把大范围微分几何引进了美国数学……半个世纪以来,正是陈省身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微分几何。” 实际上,陈省身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美国。阿蒂亚说:“陈省身在现代几何学的发展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三任所长 陈省身做过三次所长,其中一次是“代理”所长。 1947年,他在南开时的老师姜立夫力荐陈省身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职务。陈省身推辞不掉,只好“代理”。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中研院数学所在大陆的活动就此结束,但包括吴文俊在内的许多弟子日后都成为了中国数学的栋梁。 1982年,在陈省身及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事辛格和摩尔CalvinMoore的共同努力下,该校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争取到经费,建立起美国数学研究所,由陈省身出任第一任所长。关于如何管理数学所,陈省身有一段今天读来仍不无裨益的论述:“办这个所最要紧的是把有能力的数学家找在一起,找来之后就不要管了,让他们自己搞去……现在你要政府拨款或跟机关要经费的话,动不动就要你的计划,可是根据计划能够做出来的东西大概不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最好没有计划,不过这没法子跟管钱的人讲清楚。” 目前,美国数学所正在扩建,主楼将被命名为“陈省身楼”。现任所长艾森巴德(DavidEisenbud)早就希望在揭幕时能请到陈省身,而陈省身也表示很想去一趟的。 陈省身在伯克利担任第一任所长职务之时,便声明只做一届,因为他惦记着南开,惦记着中国。他与胡国定等一起创立了南开大学数学所。由于陈省身在1961年加入了美国籍,1984年9月他被任命为南开数学所所长时,是由专门成立的“中央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特批的。 美食数学 陈省身喜欢和别人合作。阿蒂亚说:“他与很多优秀的数学家如玻特RaoulBott、格里菲思、莫泽J.K.Moser等人都有过合作。”这些合作呢,又往往和“吃饭”联系在一起。《陈省身传》的记载称,陈省身是美食家,喜欢在饭店里招待客人和谈论学术。1991年,丘成桐等编著的庆贺陈省身八十寿辰的文集里,许多祝贺文章里都提到“吃饭”,似乎数学是饭店里做出来的。 格里菲思就是多次享受过陈省身殷勤招待的美味中餐的人之一。格里菲思回忆说,1961年夏天,他在普林斯顿读研究生时,导师让他去伯克利,刚到那里,陈省身就邀请他共进午餐。自此,格里菲思与陈省身、与中国科学界开始了多年的情谊。他告诉记者:“在陈先生的建议下,1980年至1982年间我曾断断续续地在中国度过了两年,帮助建立中美早期的科学桥梁。”2002年,担任国际数学联盟秘书长的格里菲思,又很高兴地看到国际数学家大会首次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举行。 “陈省身总是乐于帮助年轻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阿蒂亚说。早在1956年,阿蒂亚曾应陈省身之邀到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199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设立“陈省身访问教授”计划,邀请一流数学家到伯克利做一年访问研究,第一个被邀请的就是阿蒂亚。本来,阿蒂亚期盼着南开国际数学中心落成时再到中国,大家一起庆祝陈省身的贡献。如今,他却只能怀念2003年9月那些与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宁园共进早餐的日子了。 “陈省身访问教授”计划的资金来自陈省身的一个学生乌米尼RobertUomini。1960年代,乌米尼是伯克利的一名本科生,听过陈省身的微分几何课程,陈省身给过他鼓励。后来,乌米尼读了研究生,在1976年拿到博士学位。20年后,在一家公司当顾问的乌米尼中了2200万美元的头彩。他决定拿出100万美元捐给伯克利,以表达他对陈省身的感激之情。今年2月,乌米尼又宣布追加捐款永久地设立“陈省身访问教授讲席”。 未竟心愿 这些年来,陈省身为中国数学做了很多事情,包括选送年轻人到美国留学、推动设立数学天元基金、推动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举办等。 1988年,在南开大学召开的“21世纪数学展望研讨会”上,陈省身建设“21世纪数学大国”的倡议被参加会议的李铁映称为“陈省身猜想”。如今,在陈省身等诸多人士的努力下,中国数学走出了陈景润那一代数学家之后出现的低潮期,中国数学的实力得到了全面提升,“陈省身猜想”已经基本实现。但是,中国距离“21世纪数学强国”还比较遥远,在张奠宙看来,这可以说是一个“陈省身梦想”。 此外,张奠宙说,“陈先生就像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神,大家都非常敬重他,但或许是距离太远,他内心的一些想法还没有充分实现。” 例如,陈省身认为,数学课题,世界各国目前做得很少。它的主要思想是中国人发展起来的,现在投入大的人力,有可能很快在中国本土上做出世界领先的工作。一个当前不被看好、似乎还不是主流的课题,未来可能是主流。但他的呼吁一时未得到广泛响应,有人觉得芬斯勒几何缺乏实际背景,难以判定其前途;也有人觉得它不够时尚,难以得到别人的关注和认可。最近两年,情况终于开始有所变化,一批年轻人正投入芬斯勒几何的研究。此外,陈省身还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外微分方程。当然,张奠宙说,芬斯勒几何和外微分方程的前景究竟如何,还得由时间来作最后判断。 陈省身忧心的不只是中国数学界。例如,丘成桐提到,国内一些学校请来海外学者做短期工作,对外宣传时却当成是做长期工作,“陈先生不同意这种吹嘘,他认为缺乏扎根在国内工作的人才是不好的”。 “欧高黎嘉陈” 今年6月,陈省身获得了100万美元的邵逸夫数学奖。包括格里菲思在内的国际评委们的评价是:“陈省身是近代几何学宗师,他的数学研究以几何学为中心,持续几近70年,勾划了现代数学的多个范畴。他对当代数学精髓之一的微分几何学的界定,超过其他数学家……今天,陈省身桃李满天下,门生遍布美国各大院校数学系,他在中国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 杨振宁在赞陈省身的一首五言诗中有“欧高黎嘉陈”之说,将陈省身与欧几里德、高斯、黎曼,以及陈省身的导师嘉当这几位人类几何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相提并论。张奠宙说,这只是诗句,但形容陈省身是20世纪几何学的一位领袖,则是获得公认的。 丘成桐也说,陈省身对科学的影响用几句话实在很难描述。2004年12月17日至22日,第三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将在香港举行,他会在这样一个学术场合追忆和评价老师陈省身。 1979年,陈省身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时,学校为他举行了为期5天的国际微分几何会议,从世界各地赶来的300多位数学家用歌声颂扬起他的数学功绩 向陈省身致敬!数学的伟人! 他使得高斯-博内公式家喻户晓, 他发现了内蕴的证明, 他的真理传遍了世界, 他给我们陈类, 还有第二不变量, 纤维丛和层, 分布和叶形! 让我们大家向陈省身欢呼致敬! 一生只做一件事(本报驻京记者 南香红) 人生选择只有一个方向 陈省身基本上是个少年天才。 他只上过一天小学。8岁那年,陈省身才去浙江秀水县城今嘉兴市里的县立小学上学。可那天下午放学时,不知什么缘故,老师却用戒尺挨个打学生的手心。陈省身虽然因为老实没挨打,可这件事却对他刺激太大,从此便不肯再迈进小学校门一步。第二年他考入中学,4年中学之后,于15岁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本科。 在南开,陈省身先生做出主修数学的第一次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数学能力一向比较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上第一堂化学实验课,在吹玻璃管时手足无措,而助教又是严厉著名、外号叫“赵老虎”的。从此他对理化充满畏惧。看来每考数学“必是王牌”的他,是为数学而准备的。 陈省身19岁时考入清华大学读硕士。在清华时的陈省身,对微分几何充满了向往,但未曾入门。“那时候的心情,是远望着一座美丽的高山,还不知如何可以攀登。” 陈省身听了德国汉堡大学数学家W.布拉施克的“微分几何的拓朴问题”,决定去汉堡读书。当时美国退还了庾子赔款的余额,用此款资助的学子是要到美国读书的,而且当时的许多留学生一般也都愿意去美国,但陈省身认为,读数学必须去德国。这是他又一次主动的选择。在他的坚持和前辈的帮助下,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汉堡道路的选择使他有幸接触了布拉施克、E.凯勒、E.嘉当等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的思想和学术。 在汉堡大学开设嘉当-凯勒定理讨论班时,一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但因为艰涩难懂,最后只剩下陈省身一个人,就在那时他懂得了嘉当的魅力。 1936年,陈省身的公费期满,接到清华的聘约,但他决定去巴黎跟嘉当先生工作一年。“这对于我在数学上的研究发展来说确是决定性的一年。” 决定性的一年 1937年陈省身回到国内,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战争几乎会影响和改变每个人的命运,但是战争却没有影响陈省身的数学方向。 陈省身随西南联大南迁。“设备图书什么都没有,条件差,也没房子,记得我和华罗庚、王信忠先生挤在一个房间,因为地方小,连箱子里的一点书都不愿意打开。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也能做出成绩来。” 陈省身在昆明的煤油灯下写出的两篇文章,发表在普林斯顿大学与高级研究所合办的刊物《数学纪事》上,数学家H.外尔和A.韦伊认为陈省身的研究工作达到了“优异数学水准”。遂极力促成陈省身来普林斯顿。他们认为陈省身是“迄今所注意到的最有前途的中国数学家”。 虽然美国卷入战争,但普林斯顿却因战争得福,爱因斯坦、冯.诺依曼、E.诺特等因犹太人或与犹太人有关的受迫害科学家的加盟,使普林斯顿取代欧洲而成为世界数学中心。 陈省身决定从昆明前往美国的普林斯顿。那时的整个世界都陷入大战中,去美国的途径是从昆明飞印度,然后再坐船经过大西洋到达,但是“想到德国潜水艇的活跃,这条路自然有相当危险,但我决心赴美,不顾一切困难”。这一次的离别,陈省身甚至无法先回上海和妻子幼儿告别。陈省身选择了乘坐美国飞虎队的军用飞机走西线前往美国。就算是乘坐军用飞机也是非常艰难的旅行。军用飞机每到一个空军基地,乘坐者就要在基地的房子住下,然后拿一个条子看布告,有自己的名字, 就继续往前飞一段。这样,经印度、中非、南大西洋、巴西到达美国。前后用了一个星期,陈省身终于到达美国。 1943年,无疑是陈省身一鸣惊人的一年。这一年,32岁的陈省身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完成了关于高斯-博内公式的简单内蕴证明,这篇论文被誉为数学史上划时代的论文,这是陈省身一生中最重要的数学工作,因此,他后来被国际数学界尊称为“微分几何之父”。 我得力于吾国两名成语自励,即‘日新日日新’的精神和登峰造极的追求。”陈省身说。 一片安静的天地 陈省身在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和夫人去参观罗汉塔,看着看着突发感慨:“无论数学做得怎样好,顶多是做个罗汉。菩萨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罗汉谁也不知道那个是哪个人。所以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他认为数学的菩萨是黎曼和庞加莱。黎曼不断地开拓了数学的空间,庞加莱把数学的平面和空间推广到了N维,因为有了这两位,其他人的工作只能是“罗汉”。 名利从来不是陈省身的追求。“我读数学没有什么雄心,我只是想懂得数学,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名利,数学不是一条捷径。”陈省身说自己做学问从来不赶最时髦,不抢热门。他不喜欢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心灵》讲述的数学家纳什的故事,他说他和纳什很熟悉,但他和纳什完全不一样。“他是个怪人,他的数学是很好的,但他始终要做难题,想做难题出名,最后做得一塌糊涂。” “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是一件幸事。”陈省身说过,数学有很多简单而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人废寝忘食,多年或经年不决,一旦发现了光明,其快乐是不可形容的。“这是一片安静的天地,没有大奖,也是一个平等的世界。” 1984年陈省身出任了南开大学数学所所长。他在给南开大学副校长胡国华的信中描述他心中的数学殿堂:有一个供人随意起坐的房间,人们在这可以随意讨论;研究室的三面墙都要是高品质的黑板,人们可在上面随便地演算;要有图书室。 “要在国内成立一个基地,培养第一流的数学人才。那基地需有一流的设备,友善的空气。使人工作其中,觉得快乐。” 数学之美 陈省身说,自己一生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数学。天下美妙的事件不多,数学就是这样美妙的事之一。 在陈省身92岁的时候,他自费制作了一些挂历,向公众普及数学知识,这本挂历的名字就叫做“数学之美”。 197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读懂了陈省身-韦伊定理,他感到“真的有触电的感觉”。而且还不止于此,“还有更深的,更触及心灵深处的地方:到头来,忽然间领悟到,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优美这一价值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观念竟然完全吻合,那真是令人感到悚然。这种感受恐怕和最高的宗教感是相同的吧”。 让杨振宁感到惊异的是他和陈省身在不同的领域里研究了20多年,最终竟然“天下归一”。杨马上开着车到陈的寓所,“我们谈了很久,谈到朋友、亲人及中国”并提出了一个迷惑他的问题:数学家为什么会凭空梦想出这些概念? 陈省身回答:“不,不。这些概念不是梦想出来的,它们是自然的,也是实在的。” 他的数学和生活混在一起无法分开。 “有人问我,每天工作多少小时?没法子说,我一直在想。” 也许是因为深切体会到了数学之美,陈省身拥有一个几乎完美的人生。从20多岁入数学之门直到93岁去世,他的脑子像一架机器一样一直为数学运算了70多年。 本文打引号部分出自《陈省身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参考《陈省身传》,张奠宙、王善平著 特此致谢 陈省身:自由心灵,简单人生 这是两年前,2002年4月的一次散漫的访问。访问者梁东元先生是总装备部创作室的创作员。获知陈省身先生去世的消息,他给本报发来了这篇极少人读过的旧文,以作悼念。 他写道,在这样的时候,我对陈先生所传布的自由、简单和快乐有了愈加深刻的理解,也隐约感觉到,也许要过很多年,我们才能渐渐脱却一些浮躁和浅薄,开始领悟陈先生之于这个世界的非同寻常的意义。 2004年12月3日深夜,我正在网上游走,突然看到“陈省身”几个字从眼前倏然闪过……我把两年前采访陈先生时的合影找了出来,放在书架的正中间。在我和陈先生背后的墙上,是一只圆形的石英钟,上面的时针清楚地表明了那个瞬间:2002年4月5日13时13分零4秒。 这场雨从睡梦中就下起来,到中午了还在哗啦啦下个不停。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街道,车辆,树木,路旁的建筑,撑开了的伞,全都湿漉漉的,显然洗去了不少市面上的喧嚣与浮躁,以及与浮躁同样轻飘飘的漫漫扬絮。 从天津西站到南开大学大约要走二三十分钟,出租司机是一位长相粗犷神色生动的中年人,高喉咙大嗓门,非常热情,一路上用他那地道的天津腔跟我们说话。我们跟他说起陈先生,他立马接过话说,陈省身?知道。大数学家,不得了!天津人懂点儿事的谁不知道啊!你要说这陈省身,那可是人才哪。司机一边骄傲着,一边还要左顾右盼,忙着找路旁哪儿有花店,以方便我们给陈先生买鲜花。 甫一坐定,陈先生就颇有些出其不意地说,你们今天应该向我道喜。看到我们面露疑惑,陈先生停顿了一下才解释说,以前患有静脉血栓,前些时候还住了两个来月的医院。今天上午刚又去查了,一看,血栓竟然没了。我们听明白后,忙说这倒真是件喜事,好消息。陈先生如小孩儿一般得意,连连说,是,好消息,好消息。 世界上最要紧的是自由 “对小孩子不能管得太凶,管得太多的小孩子不会有出息。我小的时候上学很晚,但出来以后家里就没再管过,后来的每一步路也都是靠自己。现在好多家长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把孩子管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这样管出来的孩子你怎么能让他将来有自己的发展?” 陈省身先生说,这个世界上,最要紧的就是自由。 梁东元:您回国定居有两年了,在数学方面或其他科技方面,能不能感觉到,国内是否在向上走的一个趋势? 陈省身:是的,往前走。我老是讲,南开的数学现在就很好。在南开,现在我们找了一大批年轻的人才,很不容易。至于有些人出去了,不愿意回国,主要还是国内现在的待遇低了一点。另外,在国外朋友多,工作比较容易,条件很好,有效率。中国的行政部门管得有些多。 梁东元:这个管是指什么个管?是干涉太多吗? 陈省身:嗯,干涉太多。干涉太多,哪怕是好意的,想帮忙的,从长远看效果也不好。最好是不理他,他自己知道该怎么搞。真正的天才是自己蹦出来的。你要知道,顶理想的就是他一个人做工作。大家都鼓吹交流,讲科学需要合作,需要互相帮忙,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真正好的工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一个人的创见是自己努力和灵感的结晶,很少是和一群人讨论的结果。有时候,一个人忽然一下子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你有了这个很好的想法,有时候不见得当时就能知道,也许要等多少年之后,才发现这个方法的绝妙之处。 梁东元:您的话特别耐人寻味。对人才最大的爱护,是给他自由。 陈省身:对极了,自由。最好的科学是发现出来的,不是计划出来的。可是国内你要做什么东西,政府都要你的报告,而看报告的人往往并不真正懂,这也只能浪费时间。 我想,最要紧的是,政府要让大家放开手脚,要多给予支持,不支持科学就不能发展。 不过,有些人是不应该支持的。他不大行,打报告打得倒很好。现在中国出了一种新八股,一二三四,报告打得好极了,真正的工作他却不会做,所以并不行的。奇怪的是,这样的东西竟然还能起一点作用。 做事业首先要学会选择 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人,可以随不同的途径,完成自己的志愿。陈先生在回顾自己数十年的治学历程时,认为这一切结果之所以发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自己漫长人生的每一步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梁东元:我曾看过一个资料。有一次,台湾清华大学请您和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一起参加一个座谈会,中间有位姓黄的教授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研究的方向和领域。杨振宁先生说,大学中有很多优秀的研究生,他们自己和老师都不能预测未来的成就有多大,可是二三十年后,成就却可能悬殊。事后一回想,成功的同学在当时不见得就比不成功者优秀许多。这其中的一个基本道理是,有人走对了路,左右逢源,而有人却走错了路,再努力也很难有大成就。我们知道杨振宁先生曾是您的学生,他的这些见解,和您做学问首先要做出正确选择的观点也是非常一致的。 陈省身:选择有时几乎就能决定一个人整个的命运,当然,这种选择是指关键时刻的那几步。也很难。中间有许多是靠机会。 学会选择,就是要自己知道该怎么走。老实讲,我那时候的选择,我老师都不知道。你自己有时也许不是太明确,但至少头脑要清楚,自己心里应该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比如数学,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一个人应否读数学,怎么样你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数学家?英国大数学家Hardy说过,一个条件就是看你是否比老师强。 梁东元:学生一定要比老师强。这个标准可不低。 陈省身:中国的数学其实是很好的。中国人的数学才能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的数学也是全面的。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像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竞赛,中国就连续多年取得特别好的成绩。 说到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我是支持的,我相信如果一起考,我是考不过这些孩子的。但是,数学竞赛题目都不是好的题目,因为在两三个钟头里由青少年学生能做出来的技巧性题目,不可能有很深的含义。这样的竞赛虽然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但离开研究一个好的数学问题还差得很远,更不能把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奖者等同于数学家。 梁东元:那么,什么才算是好的数学呢?难道还有坏的数学? 陈省身:好的数学就是有开创性的,有发展前途的。好的数学可以不断深入,有深远意义,能够影响许多学科。比如说,解方程就是好的数学。搞数学都要解方程,一次方程容易解,二次方程就不同,等等。这一类的数学是不断发展的,有永恒价值,所以是好的。而不好的数学就是那些仅限于把他人的工作推演一番的研究。还有一些数学虽然也蛮有意思,但也仅仅是一种游戏罢了。 梁东元:究竟怎么样才算不好的数学,这方面应该也有不少例子吧。 陈省身:举个例子,大家也许知道有个拿破仑定理。据说这个定理和拿破仑有点关系。它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三角形,各边上各作等边三角形,接下来将这三个三角形的重心联结起来,那么就必定是一个等边的三角形。各边上的等边三角形也可以朝里面作,于是可以得到两个解。像这样的数学,就不是好的数学,为什么?因为它难以有进一步的发展。当然,你可以把它纯粹当作一种游戏,做事累的时候用来解闷,也是很有意思的。再把话说开来,比如现在世界上,还有国内每年发表的论文,多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平庸之作,只是在已经有的工作上做一些枝节的推广和改进,没有多大的创造性。 当然,选择好的方向,做好的数学,需要很强的能力。有能力做好的数学的人都是用功的,因为重复别人总是容易一些,但你想创新就要用功。 成功者的内心必定简单 把奥妙变为常识,复杂变为简单,数学是一种奇妙有力不可缺少的科学工具。陈省身先生认为,人生也是一样,你越是一个单纯的人,就越容易成功。陈省身先生一再说,人要简单。 梁东元:这里的简单,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简化?就是说一个人应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坚韧不拔做他所选定的事业? 陈省身:以前曾有记者先生问我是如何决定读数学的,我说是别的都做不好,所以就只能读数学了。我不像别人那么多才多艺,所以选择问题时也就十分简单,不用过多分心。 梁东元:简单实际上最不容易。生活中有那么多的诱惑,让人眼花缭乱。人的一生又那么短暂,但却把许多时间浪费掉了。那么,简单是不是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数学思想? 陈省身:既是思想,也是目的。数学思想是人人都可以享用的,像数学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化大为小,也就是把遇到的困难的事物尽量划分成许多小的部分,这样一来,每一小部分显然就容易解决。这样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用来处理日常问题的。 梁东元:在您的一本书中,您曾说,中国的大数学家如刘徽(魏晋时期)、祖冲之(南北朝)、李冶(金、元)等都生逢乱世,但他们却也做出了了不起的成就。 陈省身:只要有了人,有研究的精神,在哪里都能做事情。我一般不参加别的活动,只做我的数学。我现在这个住所叫作宁园,就有这么个意思。 一个人一生中的时间是一个常数,应该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中国人浪费时间的事太多。我已经老了,本来数学是年轻人的事业,但我还想在前沿做数学,多做一点。 梁东元:相信这也是您的快乐所在。 快乐是人生第一要素 陈省身先生总是强调一种快乐人生,把不断寻找和发现乐趣作为生活的动力。快乐就是爱,就是使一切平常的东西变得有意义。陈省身先生说,生命有无意义,包括事业、家庭生活、健康长寿等等,都和快乐有关。 梁东元:一般人都比较害怕数学,可能是因为没有看到数学的美好,没有感到数学的乐趣。同时,可能现在社会上其它一些诱惑也影响到了数学。 陈省身:这些年,因为国家开放,年轻人都想经商赚钱,当然国家社会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做科学的乐趣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在科学上做了基本的贡献,有历史的意义。我想对于许多人,这是一项了不得的成就。 梁东元:现在好像学生选学数学的也不是太多,家长或者社会上的看法也都倾向于别的门路。 陈省身:这是一个现象。现在许多有才能的学生都选择计算机、经济管理等热门学科,但正因为这样,若干年后,数学人才必然会出现紧缺。但是,数学这碗饭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来端的,没有个十年八年的严格训练,做不了好的数学家。那么,不是想出国么?这很容易,只要你做了好的数学家,国内拿了博士学位,到国外去做博士后,甚至做教授,岂不比在国外打工挣学费更好。 梁东元:也就是说,这样才会得到更大的人生乐趣? 陈省身:实际上,解密物理学、生物学的本质奥妙,都离不开数学研究的突破。中国的数学政策,除了鼓励尖端的研究以外,还应该用来提高一般的数学水平。 梁东元:我们读过您七十五岁生日时写的诗,“何日闭门读书好,松风浓雾故人谈”。您的时间太宝贵了。 陈省身:不能再浪费时间,把精力和才华消耗在眼前的一点东西上。要静下心来,我现在九十多岁了,正在走向终点,但我还想为中国做一些事情。 梁东元:很抱歉,我们今天来也是在浪费您的时间。 陈省身:就是,你们这种找我,就是浪费我的时间。不过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事情也有点矛盾。 和陈省身先生告别时,我们说,等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行时再来看望他老人家。我们的本意是想表达一种心愿,一种祝福,但这位银发满头的睿智老人却敏捷地摆摆手,用那始终沉静的语调缓缓说:不要等到那么晚。早点来。(来源:南方周末)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