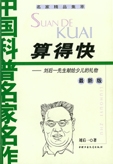此情可待成追忆——优秀畅销书《算得快》背后的故事(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17日16:44 人民网 | ||
尹传红
这是一位跨越了漫漫路途、播撒了数学种子的“园外园丁”,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时及随后的岁月里,它辗转走过了3个家庭、哺育了7个孩子。 这是一份饱含真挚情意、充盈时代气息的记录,它寄予了一位老科普作家的理想、志趣和追求,也熔铸了他行进在科普创作道路上的艰难和辛酸。 我是那7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当初哪里想得到,在幸会《算得快》20多年后,又会与它重逢,并与它的作者一家和新、旧两个版本的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 知识接力 还是先从两年前说起吧。 2002年2月,我回故乡柳州过年。到姑母家做客时,我在表弟的书柜里意外地发现了我那久违了的朋友——《算得快》,不由得惊喜地叫出声来:“哇噻,我的第一本数学课外书!” 已经阔别20年了,眼前这本黄乎乎的小薄册泛着一股陈味,又旧又脏。可我捧着它一页一页地翻看,却感到十分亲切、温馨。只是在一瞬间,书中那4位倾心速算、个性鲜明的小主人公——高商、李月珍、杜小甫和王星海,又在我的记忆中活跃起来…… 瞧,这书的封面上写下了2种姓氏5个孩子的名字,还盖了一个印章,这是怎么回事? 最清楚个中缘由的是我的父亲尹远源。我跟他提起《算得快》,他仍还记得书的封面铺黄底,上边印着小数学迷(高商)的大脑袋瓜儿。前两天,就这本书的来历我再次打电话向父亲问询,他讲了几句后便感慨道:“这是当年你们几个孩子间的知识接力啊!” 大约是在1978年底,父亲从报上得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出的一本数学科普书《算得快》,很受欢迎和好评。一直怀才不遇、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随即跑到城里的几家书店寻觅,但都一无所获。于是,他便写信向北京的亲戚求助。 我的表伯赵一丁很快就把书寄来了,可并不是新的——在书的左上角,还写着我的表哥和表姐的名字(赵平、赵楠)。原来,《算得快》一面世就成了“抢得快”、“销得快”,北京城里竟然也脱销了——后来我听说,《算得快》早年的每次发行,两三天内便被抢购一空。 这本从北京“迁”往柳州的数学启蒙读物,一度成了我课外形影不离的“宝贝”。正是在阅读《算得快》的过程中,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说那一阵我跟大妹妹关系不好,老想“吃独食”,所以在书皮上就只写下我一个人的名字;还学表哥表姐注上拼音,又盖上了自个儿的印章。而大妹妹的名字(尹传剑),显然是由“主持公道”的父亲特意添上去的。我还记得,因为大妹妹用红笔在书中的插图上涂抹描画,我愤怒地训斥了她,我们的关系由此而变得更“紧张”了…… 后来,小妹妹也长大了,于是在书皮上她姐姐的名字下方,用铅笔写下了自己的尊姓大名(尹传志)——我真搞不懂那时她为什么会那么“谦虚”。 再后来,这本书又“传”给了我的两个表弟黄璟和黄瑞。不过,他俩并没有在书皮上留下“墨宝”。顺便说一句,这哥俩对数学很感兴趣,且都考上了名牌大学;老大还获得过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广西赛区第一名,现在德国工作…… 吃了一惊 《算得快》让我记住了作者“刘后一”这个名字。 父亲陆续买来的几本课外读物:《“北京人”的故事》、《山顶洞人的故事》和《半坡人的故事》,作者都是刘后一,可这几本书跟数学一点也不搭界呀? 直觉告诉我,这些书都是同一个刘后一写的,因为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用故事体裁普及科学知识;故事铺陈中的人物都有比较鲜明的性格特征;再有就是语言活泼、通俗、流畅,读起来非常轻松。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工作,在《科技日报》做编辑。1993年夏的一天,一个同事指了指靠窗边坐着的一位文静的女士,悄声对我说道:“知道吗?她叫刘碧玛,她爸爸就是写《算得快》的刘后一。”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可是刘老爷子的忠实读者,前几天还在报上看到周文斌写他的一篇文章呢(《刘后一和少儿科普》,刊于1993年5月29日《光明日报》),真没想到我会跟他的女儿做同事! 碧玛极易相处,渐渐地我们就成了彼此熟识的朋友。她跟我讲了好些她父亲的故事。我在20多年前的那个猜测,总算得到了证实。 缘分还不止于此。想不到我先后竟然又在不同的场合结识了老版(1978年版)《算得快》的编辑郑延慧、新版《算得快》的策划编辑薛晓哲,以及早在70年代末就报道过刘后一科普创作成果的记者周文斌。人生可真是奇妙啊,与《算得快》相关联的这些“巧”,怎么都让我给碰上啦? 从那以后,我想拜会刘老先生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留下遗憾 1996年夏秋之间,我听说刘后一先生病了,便再次向碧玛提出去看看他老人家。第二天老先生让女儿捎来话说,谢谢我的好意,他很愿意见我,只是这一阵卧病在床,家里乱得很,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然而,此后不到半年便传来噩耗:老先生在参加科协组织的一次活动时,因脑溢血突发而匆匆离去。这一天是1997年1月24日。 未能见到“活生生”的后一先生令我痛悔不已。 郑延慧女士告诉我,70年代初她接手编辑需修改再版的《算得快》时,曾到刘后一家去过几次,发现身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的他处境十分窘迫。当时他一家5口,挤在两间大约8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床铺,难找别的空间。他常常只能在办公室里写作到深夜,而后就睡在办公室……一家人全靠他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谁能想到,《算得快》这部累计行销逾1000万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的畅销书,以及同样也很受欢迎的《“北京人”的故事》等科普佳作,竟然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写成的呢? 在女儿刘碧玛眼中,父亲刘后一是一个胸怀大志、勤奋好学而又十分“正统”的人。他父母早逝、家境贫寒,有时连课本和练习本也买不起。寒暑假一到,他就去做商店学徒、修路工、制伞小工、家庭教师等,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他之所以获得渊博的知识和后来写出大量的科普作品,大多靠的是刻苦自学。“父亲也并非‘完人’。虽然他在科普创作的天地中驰骋自如,但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却城府不深,缺乏娴熟的应变能力,这使得他与许多像入党啊、晋职啊等等好事失之交臂。” 与刘后一相交多年的周文斌先生,以十分赞赏的口吻称道他的这位老朋友“淡泊名利”,“有一种与世无争的超脱”,但同时又直率地指出:“我觉得这些优点的另一面即是他的弱点,那就是委屈求全,不敢据理力争,不敢当仁不让。他做了几十年的科研、学报编委和科普杂志《化石》主编的工作,写下了数十部总计200多万字的著作,可直到退休仍还是一个副编审。这一点,我感到不公,他的其他朋友也认为不公,而刘后一本人却忍了。这是我所深为遗憾的。” 在周文斌看来,这一遗憾的背后还有着一个更大的遗憾,那就是科普创作的被轻视。在科技界,有些人虽然对写科普作品不知从何下笔,更不了解科普创作的艰辛,可却对科普作家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狂妄。他们视科普创作为“小儿科”,对科学普及的意义更是一知半解,可却自恃高明、自以为是。这正是我们科普事业的悲哀!“真愿意我们的科普界多一些像刘后一这样的‘副编审’,也真愿意我们的科普界不再有像刘后一这样的‘副编审’。” 园外园丁 “你写了那么畅销的书,若是在我们那儿,有一本就够吃一辈子的了。”80年代中期,有一位来访的外国朋友曾这样对刘后一说。回到家后,他苦笑着跟女儿提起过这事儿,但没说他是如何作答的。他真的会在乎他吃的“亏”吗? 女儿说,父亲长期业余从事科普创作,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然而所得到的稿酬并不多,甚至“不成比例”。尽管如此,他经常拿出稿酬买书赠给渴求知识的青少年,还曾资助了8个“希望工程”的小学生背起书包走入学堂,并将《算得快》等书的重印稿酬全部捐赠给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编辑出版的大型丛书“希望书库”。 他其实是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在他的心目中,身外之物远远不及他所钟情的科普创作重要,因此,在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乃至刁难面前,他都能够泰然处之,而不是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他曾写道:“有的人情愿穷聊闲逛、‘打百分’,却看不惯别人业余给孩子写东西……有的人以己度人,认为你写些科普作品,无非是为了出名,得稿费而已。甚至造谣污蔑,打击陷害。在我看来,我上过师范,学过教育学,为孩子们写作,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也是我的正业。作为国家干部,同时又是园外园丁,有何不可,有何不妥?” 在这篇题为《园外园丁》的文章中,他还戏称自己当年挑灯夜战的办公室,是他“耕耘笔墨的桃花源”。字里行间也透着欢快的笔调:“《算得快》出版了,书店里,很多小学生特意来买这本书。公园里,有的孩子聚精会神地看这本书。我开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与快乐,因为我虽然离开了教师岗位,但还是可以为孩子们服务。不是园丁,也是园丁,算得上是一个园外园丁么?我这样反问自己。”当年,正是了解到一些孩子对算术学习感到费劲,他才决定写一本学习速算的书,以诱发孩子们对算术的兴趣。而这,跟他的生物学专业压根儿就不沾边。 在刘后一先生七周年忌日将至的2003年12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算得快》的最新版,开机便印15000册。半年时间不到,就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欣闻新版《算得快》销售形势看好,又加印了31000册…… 后一先生,我想您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从《算得快》到北大公司里许多人都叫他封老师。的确,他是老师。他是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原北大信息科学中心)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早从1997年开始,他就以石青云院士大弟子身份协助石老师带研究生。现在,活跃在中国生物特征识别领域尤其从事指纹自动识别领域的有名望的青年科学家,大多都是他的师弟。 我最早是从石青云院士那里知道封老师的:“有个冯(石老师将封念成冯的音)博士,是我的弟子,非常有才华,人称大师兄。希望公司能够留住他。我不希望冯博士到国外去。”不久,公司与北大信息科学中心共同建立生物特征识别联合研究所,我见到了这位“冯博士”,才知是姓封,封举富。就凭这名字,这人一辈子都不会受穷。 2002年年初,公司原有的几名主要技术人员离开了公司。正值公司困难之际,封博士受石青云院士和公司之邀,临危受命,担当起公司重组技术队伍重任。当时,不只是公司员工,一向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客户也都十分担心:原有技术人员的离开,北大指纹还行不行?新的技术人员能力怎么样?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并发展公司产品? 2002年5月的一天,他与石青云院士一同来到公司。石青云院士一番简明扼要的介绍让我至今难忘:“他是我的大弟子,学生们都叫他大师兄,在我生病期间替我带学生。他的硕士论文获得过亚洲计算机视觉第一届国际会议优秀论文奖。在模式识别上他有创造性思维。他的知识面很广。”那一天,是大家接触封老师的开始,是大家寄托心中希望的开始,也是封老师为大家答卷的开始。 组建一只强有力的技术团队,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前提。封博士很快地与石青云院士的其他弟子陈益博士、林通博士等取得了联系,开始组建新技术团队的工作。 “那时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实验室工作。2002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封师兄的电话,他告诉我,北京指纹公司目前有些困难,他要我回国和他一道组建新的技术团队。这对我太突然了。当时我正准备去加拿大,研究人脑对音乐感知方面的课题。我已报了名,并缴了费用。”陈益,这位石青云院士的另一位多才多艺的弟子,在回忆他加盟北京指纹公司的情景时说:“封师兄当时对我说,公司目前有困难,希望你能回来和我一道完成石老师的事业。” “就是这句一道完成石老师的事业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不去加拿大了,回国加盟北京指纹公司。” 就这样,封举富和陈益,两名技术强将,携手共进,成为公司新的技术核心,与其他几位博士、硕士一起迅速组建起了北京指纹公司新的技术团队。封举富博士现任北京指纹公司技术副总裁、首席科学家,陈益博士现任北京指纹公司技术总监。 2002年6月,公司在云南昆明召开用户大会,200多名客户代表出席会议。在会上,人们注意到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梳着光溜溜的头发,身着笔挺蓝色西装,站在台上,清晰明了地介绍着指纹系统和模式识别。客户们惊讶:他就是封博士?封博士的风度、学识以及对客户问题的侃侃而谈,深深地征服了客户,博得大家的高度评价,扭转了大家对公司技术前景的担忧。很快,公司员工和客户都认可了以封博士为首的技术团队,大家对公司技术团队组建之快而感叹,对技术团队水平之高而感叹,甚至已离开公司的技术人员也感叹没想到新的技术团队这样强。 封老师在模式识别领域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但在学校做老师和在公司做首席科学家是有一定差别的。封老师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尽快熟悉公司情况,了解原有产品,积累实战经验,封老师很快主动和其他开发人员、销售人员、技术服务人员“亲密接触”,并经常到客户中了解情况。2002年10月,公司组织了一次技术研讨会。封老师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同与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十来位公安战线的专家们进行了交流,仔细地征询客户对北大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的意见和改进建议。我注意到,他十分认真地听取每一位专家的意见,作了详细的记录,并于会后组织公司技术人员进行讨论。之后对系统中许多地方都进行了改进。 封老师对北京指纹公司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来公司的时间虽然不长,只一年多的时间,但因他的威望,很快地组建了一支当今在指纹自动识别领域非常有成就的青年才俊队伍。在他的带领下,北大指纹自动识别系统3.2版本在广州完成。12月中旬,这个版本在公安部有关专家的主持下通过了专家验收。与公司合作多年的广州市公安局的专家说,封举富、陈益等新的技术团队与公司以前的技术人员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更注重实际,说得少,干得多,落实得快,解决问题的能力强,水平更高了。作为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封老师不但解决公司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有些算法自己亲自完成,还站在更高的角度,考虑如何整合技术方面的资源,将AFIS、MIS和其它相关技术相互融合,使之发挥更大功效。 封博士是言辞严谨、低调之人。在这个一些厂家为迎合客户心理,不断地推出“新理论”、“新方法”,并得出天文般数字的年代,封博士仍然保留着赤子般的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科学总是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并不断向前发展的。永远正确的那是神学”。对于没有严格理论依据、没有经过大量实践检验的比较“炫”的数字、比较“炫”的理论和概念,封博士总是很小心的使用,他严格辨别着各种概念,认真检验着各类数字,并勇敢的怀疑着一些理论。封博士非常强调测试工作,“对于产品的修改,尤其是算法,不能随随便便,不能靠感觉,一定要有大量的真实数据作为依托”。“用户不是试验田,我们必须建立大量真实、可靠、符合实际情况的测试用例,提供详实、精确的测试数据,检验算法的有效性,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封博士最不愿看的是“这样应该好一些”、“感觉上问题不大”。他对部下的报告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于有些人“怕”他。 其实封博士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和他接触时间长了,你就能感觉到,他挺愿意和大家聊聊天,喝喝酒,抽抽烟,打打球,逛逛商场。他酒量不大,但大多时候他都愿意喝一点,当然他也会要求你喝。如果你吸烟的话,没事的时候,你可以上他的房间,坐到他的对面,叼上一只烟,或者翻看一下他那几百页的英文书,或者摆弄一下他的七巧板,封老师不忙的时候,也可以问他一些问题,你一定会得到耐心而细致的解答的(我看我们公司有很多人借着问问题的名义,到他房间蹭烟抽)。休息日,如果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和封博士一起打打保龄,或台球、羽毛球,但不要去图书城,否则你就要陪他看几小时的满是公式的数学书。 封老师看问题很准确。这是封老师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地方。缘于何?2002年下半年,公司参加湖南省公安厅、海南省公安厅、宁夏自治区公安厅、陕西省公安厅等多家省厅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的招标工作,并开始制作规范本的标书。公司组织了由技术、销售、技术服务、宣传等部门组成的应标组,对应标书进行讨论。当时我们对罗昌英拿出的初稿逐段甚至逐句进行了仔细地分析。“这个提法是否准确?”“那样说是不是更好?”封老师的眼睛很“尖”,看出不少问题,经他提议改过的,大家又都觉得很好。 封老师知识很广博。除了生物特征识别外,他喜欢哲学、文学、物理等。今年2月,海南省公安厅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招标会上,我们公司的标书夺得海南7项标准的7个第一。作为公司各方负责人员:封举富、胡欣、赵峥、程卫杰、罗昌英、王刚等人欣喜之余,天南海北地开侃:“所谓无损压缩,实际是这样的……”封老师侃侃而谈。“噢,原来如此。这下我可以向姚科(浙江省厅姚跃武科长)吹牛了”胡欣语。回到北京后,我曾听过封老师的这段科学普及,讲得真是透彻、简明。大科学家往往是大科学普及家。可惜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否则,我们真应该割爱,让他写一些科学普及的文章,惠及更多的年轻人。 封老师热爱运动。说到封老师的运动,那也是公司里一流的:各种球类运动,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各种棋类运动,象棋、围棋等均样样出色。2002年9月,公司在北京九华山庄召开核心竞争力的研讨会。会余我曾欣赏过封老师和其他几位博士的台球对垒,可惜的是,当时封老师小输1分。10月,公司在密云开会时,封老师又与这几位博士相遇在台球场上。我因有事,没有看完这场龙虎大战。据说,封老师大胜。但封老师似有不甘:“可惜没有让她们看到,上次我小输时却被她们看到了”。 封老师的年龄并不大,他是1967年10月出生的,是“三北”(即大学、硕士、博士都在北大读的)。说起他考北大的经历,还真有些传奇色彩。如同其他小男孩一样,封老师小时候也绝顶淘气,打架、恶作剧、带领其他小朋友玩打仗游戏、在河里嬉戏,无所不做。但他也十分聪明,学习一直很好。在他10岁左右,上三四年级的时候,湖南省出了一位少年大学生,名叫谢彦波,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年龄与他相仿佛。此时正值1978年,改革开放的洪流激荡着人们的心田,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大地。少年大学生的出现,对当时的中国影响非常大。因为同是湖南人,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封举富。他的老师看透了他的心思。一天,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拿出一本书。“你看,这是什么书?”封举富拿起书来一看,是一本《算得快》。“能让我看看吗?”“就是准备送给你的。你算算看,看算得快不快?”从此,封举富就像着了魔似的,再也不把时间放在同小朋友的嬉戏上了。他从《算得快》开始,进入了书的世界。他每天捧着书,读了一本又一本。 书本将他的知识迅速地扩大着,知识让他的眼界开扩。他就读的学校不是重点学校,只是县里的一座普通中学。但在地区中有众多重点中学参加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中,他夺得第一名佳绩。不久,他又在全省中学生的竞赛中,获得一等奖。他的学校因他的出色成绩而辉煌,他的老师因他的出色成绩而自豪,他的父母也因他的成绩而欣喜。 很快就到了该考大学的时候了。考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呢?此时的封举富,心中没有任何“我考不上哪所大学的”顾虑,唯一要考虑的是哪所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呢?一天爸爸下班回家,给封举富带来几所大学的介绍和照片。有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的。看着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美丽风光,封举富决定了:考北京大学。 封举富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大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种知识。神秘的数学殿堂,精深的理论知识,使他的学习欲罢不能。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了石青云院士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石青云院士那里,他收获颇丰。石青云院士为人平和、待人真诚、做学问精益求精、有大局观。石青云院士做人、做事的大家风范,深深地影响着他。尤其在学术研究方面,石青云院士往往从实际问题出发,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特别注意从视觉与听觉信息处理中提出新的数学问题,并进一步发展用于信息处理的数学方法解决问题,如一般学工科的人研究小波,只是研究如何去用;而石老师研究小波,不光研究如何去用,还研究其理论,以便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石青云院士很早就研究指纹自动识别,攻克技术难关后,又做图像数据库,后又研究小波压缩,每个课题的选择,都非常具有前瞻性。石老师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和选题的高瞻远瞩,成为封举富的一个好榜样。在石老师带领下,他也很快地成长起来,不但自己学习好,在学术方面有建树,做事严谨有大局观,还协助石老师带学生,成为北大信息科学中心的栋梁之材。 公安部五局八处王瑛玮博士,是当今中国公安信息化建设年轻一代的英豪级人物,也是封举富的师弟。提起封举富博士,王瑛玮博士认为“在当今国内指纹自动识别系统这个领域,有几个领军人物,第一当属封举富……” 是的。封举富正以自己的英华之年,为公司、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知识财富。如今,人们的一句“封老师”,包含着的却是数不清的一种韵意。 数学,优美而简单 星河 不久前,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送我一本新版《算得快》,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们都知道科学史上“日心说”战胜“地心说”的著名故事,在故事里我们总是把哥白尼想象成推动历史前进的斗士而把托勒密想象成阻碍科学发展的骗子。事实上历史真相并不完全如此:托勒密也是在做了许多观察和计算之后才得出“地心说”这一结论的,他也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虽说很不幸,他的结论错了;而且更不幸的是,他的结论后来为他人所利用。而哥白尼在撰写他的名著《天体运行论》时,只是深信这样一个原则:自然界不会如托勒密描述的那般复杂———托勒密理论为解释那些天体运动,不惜设定了80个假想的“齿轮”;而哥白尼认为,假如把托勒密理论中的太阳与地球易位,甚至连一半“齿轮”都用不了!哥白尼坚信,自然界必定是优美和简单的。 在我看来,用来描述自然界的数学就具有这样一个显著的优点——优美而简单。 作为一名科幻作家,我与文艺界和科技界人士都有不少交往。但我发现,不要说在作家圈里,即便是许多出身理工者,对数学也并无兴趣。这让我非常失望,因为我对数学一直迷恋有加。高中时我曾整宿整宿地求解一些艰深的数学问题,其精力之旺盛甚至超过我现在通宵打电脑游戏的精神;而当那些难题的面纱云开雾散时,我的喜悦和兴奋真的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虽然我后来没能真的去搞数学专业,但还是阅读了大量专业和半专业数学书籍,每当我站在图书馆数学部分前,都会有一种抛弃现有的一切重新去学数学的冲动。 凡事都有源头,检点我的藏书,《算得快》几乎是我最早读到的数学科普之一。凭心而论,那时我还太小了,所以不敢说就是这本书让我走上了喜爱数学之路,因为我在阅读它时,学会的也许只是运算上的技巧;但这的确成为在我眼前打开数学之门的一把钥匙,我至今相信它对我后来数学情结的影响不可忽视。 让少年读者一开始能够迅速融入的自然是精彩的故事,但在阅读故事的同时,那些精湛的速算方法便被潜移默化地注入到我的脑海:在售货员的故事里我知道了在加法算式里可以有选择地先加某些数,在高斯的故事里我第一次了解到那个从1加到100的主人公原来就是这位数学家(这恐怕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外国数学家),在加工木板的故事里我明白了工程中应该严格遵循设计先于施工的道理,在古代人计算两位数乘法的故事里我惊奇地目睹了阿拉伯人的“铺地锦”和印度人的“交叉乘法”……,及至迅速通读完全书,那些速算方法便囫囵吞枣般地被塞进了脑子;但也有很多不明白、不清楚、不准确的地方,于是再读,再学,再算…… 速算的意义,在信息时代里,似乎显不出什么更多的作用。我们拥有众多的计算机器和记忆机器,我们借助各种装置来“照顾”我们的大脑;我快捷的运算能力和精湛的记忆能力,往往只能勉强与那些由电池供电的装置打个平手……有人曾对我说过:技术的进步往往会使一些原本属于人的本领丧失甚至变得无用——这一论述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目前我还算不错的速算本领,似乎大多用于在商店结账或者在餐厅买单时能很快地复核正误,尽管在这点上我仍会经常让朋友们惊讶。在这里我不想假设这样的情景:身陷深山,远离文明,手边没有计算器而急需获得某个数据……这种假设没有意义,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毕竟属于非常规情形。我们今天仍要学习速算,更重要的作用是为了理解这样一种思维方法,那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复杂的事情,并非不可以用更为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和完成。而正是《算得快》这本书,第一次向我展示出这样一个道理。 数学,优美而简单。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