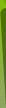鲁迅评议中的赛珍珠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4日11:03 光明日报 |
|
王卫林 在中美两国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赛珍珠(Pears.Buck,1892—1973)可说是事功累累,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作家、活动家。然而对赛珍珠而言,在新中国享有至高无尚地位的鲁迅的评语,也在长时间内,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成为决定她命运沉浮的标尺。 赛珍珠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写中国题材的作品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她8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大部分在中国度过,一直视中国为第二故乡(这点连鲁迅也认可)。直到晚年,她还向有关方面申请访华。当然,赛珍珠的热爱中国,与作为炎黄子孙的爱国情结,尤其与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存在很大差异。但赛珍珠身受中国儒学和西方基督教的双重文化熏陶,以仁义、博爱情怀,在行动上切身关注贫苦阶层的命运,在文化上致力于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这不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有其正向价值,就是对新中国以后乃至当今世纪之交的改革开放的中国而言,赛珍珠的工作业绩也仍可视为弥足挖掘、利用的文化资源。 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的视差,以及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赛珍珠的作品传入中国后,既受到某些相应的好评,也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尤其不被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鲁迅所看好。 作为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他关注的主流是民族存亡、国民性再造等深广博大的命题。同时,他也以“中国文化守夜人”(王富仁语)的自觉使命感,时时观察着中国文化界乃至世界文坛的动向。在赛珍珠的《大地》被译成中文不久的1933年,即该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五年,鲁迅就在致姚克的信中有所论及,在有所认可的前提下,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批评《大地》是“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至次年,鲁迅又对赛珍珠翻译《水浒》为英文时,改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事,提出非议。认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鲁迅这些评论,当然也和他谈论其他问题一样,极为深警精辟,非一般人所能及,不过也只是顺便提及,并非专论。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对赛珍珠的看法,似乎有所转变。他在1936年9月15日致日本友人增田涉信中,已考虑到对赛珍珠的评价中可能存在的不妥。只是由于鲁迅先生健康日下(写这封信后仅一个月,先生就去世了),已无时日和精力再顾及这一问题,从而使后人产生“鲁迅对赛珍珠其人其文均无好感”的简单印象。简单印象又被简单推定为结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人用以推波助澜,遂使赛珍珠及作品在解放后的中国长期遭到禁锢、抨击的命运。鲁迅对赛珍珠的并无恶意的微辞,自然也成为各类文章讨伐赛珍珠的利器。 平心而论,赛珍珠人文言行中的植根于基督教义的博爱,自然有诸多局限;她对中国的认识和反映,也不免如鲁迅所批评的肤浅。但若由此而将鲁迅对她的微辞无限上纲,把赛珍珠视为帝国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予以彻底否定,甚至将她妖魔化,则几乎是绝对的偏见。且不说赛珍珠的终生言行体现出的对世界(自然首先包括中国)弱势群体的真诚善意,即是对鲁迅本人,赛珍珠也始终怀着友好的感情和由衷的敬意。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到,就在鲁迅以不无轻蔑的语气评价赛珍珠之后的第三天(1933年11月18日),赛珍珠就向一位名叫章伯雨的来访青年问起鲁迅的情况,对鲁迅的学问、创作深表敬佩;对鲁迅的处境,表示由衷的关切和同情。1934年赛珍珠主编《亚洲》(Asia)杂志之后,又请斯诺撰写《鲁迅———白话大师》,发表于该杂志的1935年1—2月号上。1936年9月号上,该刊又登载了斯诺翻译鲁迅的小说《药》和散文《风筝》,这大概是鲁迅生前最后发表的作品译文。鲁迅逝世后二年,为鲁迅所不满的《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尽管鲁迅若在世,很可能对此仍不以为然(和鲁迅关系密切的巴金就说:以前他不看好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还是不喜欢她),但赛珍珠却在授奖仪式上讲演《中国小说》时,引用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许多资料。1954年,正当中国和苏联的文艺界齐声痛骂赛珍珠的言论是“猫头鹰式诅咒”时,赛珍珠却在《我的几个世界》中高度评价周树人“也许是第一个意识到:只要把自己的情感与自己的人民结合起来,就能摆脱简单模仿”。1972年,也即赛珍珠辞世前的一年,她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又一次提及:“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写有关农民题材的作品,鲁迅就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位”。当然,和赛珍珠对中国的了解一样,赛珍珠对鲁迅的了解和评价,和国内对鲁迅先生的认识评价,有着深度及高度上的明显差异,但在肯定、敬仰鲁迅的总体趋势上却并无二致。 其实,鲁迅对赛珍珠也并非完全否定,他也认可赛珍珠是爱中国的,承认她对中国有所了解,只是不如中国人自己了解得深刻。鲁迅对赛珍珠的微辞,也只是深刻而非对论敌式的尖刻。细读原话,可以发现鲁迅虽只是顺便提及,却仍是注意慎重立论,力求公允的。然而由于中美关系在50—70年代的严峻对立,两国文化关系的解读也被纳入政治渠道考虑。赛珍珠及其作品在解放前就受到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作家群的贬斥,解放后,赛氏的各类作品在中国长期被封杀,其人更受到中国及苏联文艺、思想界的敌视、诅咒。鲁迅对赛珍珠的真实态度,也在特定时代的政治气候笼罩下,被误解乃至曲解地利用。甚至在1975年批判水浒的政治闹剧中,赛珍珠也因为翻译《水浒》用名遭鲁迅非议的过节,被当作批判《水浒》的靶子之一,接受当时特定语言的抨击谩骂。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面的拨乱反正和冷静深入的文化反思,才使人们对赛珍珠及鲁迅相关评语的认识,终于回到正常文学评论的轨道。到新、旧世纪之交,对赛珍珠的研究更出现前所未有的热潮,不仅久遭禁锢的赛氏各类作品相继出版,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日趋深入,对作品分析更为细致,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以致学术界乐观地宣称:21世纪的赛珍珠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鲁迅的相关评价,也在这一热潮中被冷静客观而深入细致地体察领会,成为对赛珍珠及作品重新定位的重要参照。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