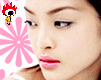申赋渔特稿:假如人生是一部默片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24日10:48 南京报业网 |
|
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是一部热闹曲折、有声有色的电影。 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向我走过来,沉默不语。 他在纸上写道:“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你老师的儿子,你初中的数学老师的儿子。” 我看着他,看着。 2005年3月11日,周五的下午,已经暖和了的南京忽然下起了大雪。 办公室的窗外黑下来,模糊了。时间倒了回去。 整整20年,我再没回到那个学校。 教室面前的走廊里铺着青砖,因为年代久远,许多块砖头已经松散开来。走在上面,铿铿直响。脚步声远远地从木柱长廊的另一端传过来,缓慢却方正。初一教室里的喧哗一下子停住。交头接耳的,站在课桌上大喊大叫的,立刻端端正正地坐好。围着讲台追打的,也飞一般蹿回各自的座位,屏声静气。 脚步声在教室的门口停住,看不到人,只有硕大的三角尺的尖端严肃地戳进门里,一动不动。 “起立。” “敬礼。” 班长喊。他走进来,在讲台前站定,朝下扫一眼,点点头。大家轰然坐下。 这是肖老师的数学课,也只有是肖老师,才会让教室在这一瞬间变得如此安静。他永远不苟言笑,严肃得让人害怕。然而课上得好,作业批改得也是极为认真。已经二十年没有再见到他。留在脑海中的永远是那样——右胳膊夹着大得吓人的三角尺,黄色的油漆已经剥落了许多。左手托着小小的木板钉成的粉笔盒,踱着方步,威严地向前。 在十二三岁的我的心中,如此严厉的肖老师是极为可怕的。即使是在下课的时候,看着他了,也是远远地避开。 那是个星期天的黄昏,因为什么我到学校去,现在已是完全想不起来。正在校园中央的林阴道上向前飞奔,忽然看到前面的人,像是肖老师。立即慢下来,不敢超过去。 他背着个六七岁的男孩,旁边走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 小男孩、小女孩我已经多次见过。小男孩大大的脑袋,两只大眼睛里满是顽皮和聪明。小女孩一头长发,白皙的瓜子脸,漂亮得让人吃惊。 这个黄昏的这一幕,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小女孩走在爸爸的旁边,两只手端着一搪瓷盆的粥,盆沿上横放着两根筷子,筷子上摆着两只馒头。小女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馒头,小心翼翼地走着。小男孩趴在爸爸的背上,两只手揪着爸爸的领口,他不停地跳跃着,骑马一般。忽然伸了脚去踢身旁那女孩,一脚踢翻粥盆,粥泼了一地,馒头远远滚出去。小女孩惊恐地站住,哭起来。 他放下那男孩,男孩笑着,又用脚去踢那搪瓷盆。他左手拉住这孩子,右手伸过去,用衣袖擦那女孩的眼泪。那男孩挣不脱他的手,兀自又用脚去踩地上流淌的粥。他仿佛毫不生气,一手一个,牵到一旁。又回了头,弓着腰,捡起那脏了的馒头,放进搪瓷盆。他一手端着盆子,一手牵着那男孩,像是什么也没发生,又朝前走去。小女孩用手背擦了擦眼泪,快步赶上去。 懵懵懂懂的我忽然一阵感动,这是最初的感动——时隔20年,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他那对可爱的儿女,听不见这世界,发不出脆脆的童音。那个踢他姐姐的小男孩,便是眼前这个高大而帅气的年轻小伙。 他在纸上告诉我,他叫肖华,今年大学毕业,找了许多家单位,可是没有人要。听说他父亲有个学生当记者,他只知道名字,就一家一家报社找过来。 他说他找了一天。我不知道他跑了多少地方,问了多少人。从偌大一个南京,茫茫人海中,他找到了我。他知道我不认得他。可是我是这个城市里唯一一个可能会记得他的人,能帮他的人。他是这样想的。他说他没办法,他跑了十多家单位,他跑了许多趟人才市场,他可能找不到工作了。 “没想到,真能找到你。”他在纸上写道,抬头朝着我笑着。头发上的水从他额头上滑下来,那是落在头上的雪融化了。窗子外面,雪越下越大。 我是知道的,这个叫肖华的小伙子对于他那个家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个我已经20年不通音讯的肖老师意味着什么。然而,我,一个不谙世故的记者,又能帮他什么呢?然而我不能说。我让他过两天再来。 他是学“计算机信息管理”的,我在报纸上细细地翻招聘启事,抄下一家一家公司的地址。 陪他去找工作是下午。只去了三家,天已经黑了。一家说负责人不在。一家让他试试电脑绘图,他试了。一家说跟聋哑人交流不是很方便。 我和他在他的宿舍坐着。宿舍7个人,都在。他们一个班18个人,6月就毕业了,听说只有两个人可能在家乡找到了工作。 肖华说他不想回老家,他已经习惯了南京,他已经在南京呆了9年。 “大街小巷都熟悉了,比老家还熟,就是不认识什么人。” “在南京9年,除了老师和同学,外面的人,我几乎一个不认得。”他在纸上写道。 现在,我是他认得的一个了。他像那个在寒冷中渴望哪怕一点温暖的孩子,在他的心中,我,也许就是一根可能擦亮的火柴。 “找到你,我最高兴了。”他写道。 然而,我能隐约感到肖华的失望。总是微笑着的肖华是聪明的。他从接待我们的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上,看到了我的无力。 “爸爸问我的工作。我说等大学毕业了,工作就不会有问题了。10岁的时候,爸爸把我送到扬州聋校,家乡没有我读书的地方。在扬州,我读了8年小学,然后来南京读中学。中学6年毕业了,又读大学。这么多年的书读下来,总算要毕业了,爸爸,全家的人,都松了口气。” “爸爸以为大学毕业,好歹就能找到工作了。” “爸爸只是寄钱给我,大学三年,从没来看过我。他说我大了,自己能照顾自己。是的。可我知道他也是为了省钱。我在这里上学一年,要花15000元。而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1000多块。全给我还不够。” “一家人的希望都在我身上呢。” “姐姐没读书。” “姐姐比我大3岁。我们一起在扬州读小学。别的小朋友欺负我了,姐姐帮我打。作业不会了,姐姐教我。好吃的,姐姐省给我吃。可是后来忽然不读书了,回家了,我跟爸爸闹,我要姐姐。有姐姐,我心里踏实。可是姐姐再也没来学校。爸爸只是让我好好用功。从家里再去上学的时候,姐姐躲在一边哭。我也哭。那年我是哭着上学的。我也是从那年才真正开始懂事。” “衣服再也没有姐姐帮我洗了。每年的冬天,姐姐总是一手的冻疮。我什么都不干,全是她洗。这年冬天,在冷水里洗衣服,我就总在想姐姐。姐姐十三岁就帮我洗衣服,洗了五年。好像她天生就会洗衣服,天生就是我姐姐一样。” “你姐姐是不是总帮你打手套?”我忽然问他。 他愕然地愣着,点点头,又点点头。 我记得那个小女孩。今年她已经30岁了,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她永远是那个小小的女孩,白皙瓜子脸的、长长头发的美丽的小姑娘。永远是那个粥盆被打翻而哭泣的女孩,那个埋着头,一言不发,笨拙地勾着毛线的小女孩。 那是个寒冷的冬天的早晨,天刚蒙蒙亮。 人群黑压压地站在落满了白霜的操场上,鸦雀无声。1000多人,人人仰着头,郑重地盯着高高的主席台。国歌声中,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国歌响起之前,我就把帽子拿在手上,立正站好,一动不动。每天的这个时刻,我都是十分的庄重。然而前面的两个同学却总是扭着身子说话。巡视的体育老师突然走过来。 然而体育老师直奔我而来,让我出列。 “我没有动。”我说。 “我看到你在讲话。” “我没有。” “明明看到你,你还抵赖?” “不是我。我没有。” “你抵赖,我让你抵赖!” 国歌已经奏完,然而体育老师生气了。他一把揪起我,朝主席台上拖过去。 我被拖到高高的主席台的上面,站在台角上。 1000多人看着我。喇叭里传来广播体操的音乐,人群拉开距离,开始做操。我站在主席台的台角上,梗着脖子,手里死死地攥着棉帽,眼泪不停地淌着。冷风吹着,耳朵、手、脚渐渐地冻僵。 人群散去,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开。第一节课开始了,操场上空无一人。我还站着,呆了一样。 下课了,拎了粉笔盒从操场边上走过的肖老师拐了个弯朝我走来。“怎么回事?”他问我。我不说话。他拖了我下来。我的眼泪“哗”一下又淌下来。肖老师领我去了他的宿舍。宿舍里生了火盆,很是暖和。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坐在火盆边上,笨拙地用毛线勾着一只手套。她让我坐在火盆边上,她用长长的竹筷,夹起火盆里的花生,一只一只,她把所有的花生都放在我坐着的板凳边上。她朝我笑笑,指指花生,又低下头,勾手里的手套。 其他一切都已模糊,只记得两只小小的生了冻疮的手,努力地勾着一只小小的手套,一针又一针,一针又一针,永无止尽。 “我刚到扬州的时候,姐姐一下课就跑来找我。有时候上课了,她也不走,握着我的手教我写字,总要被老师赶上几次了,她才走。” “可我到扬州没多长时间,她就回家了。” “她在家帮妈妈干地里的活,养鸡、养猪。” “我回去了,她特别高兴。一脸的笑,围着我忙这忙那。” “爸爸总问我学习上的事。爸爸问的时候,她就不知道跑到了哪里。” “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供我一个人读书。” “姐姐很迟才结婚。小孩刚刚满月,是个男孩。” “又健康又可爱。” “姐夫是木匠。” 我们在纸上一句一句地说话。他的句子很短,简单明了,然而却让我读出了很多伤感。大多的时候,我们就沉默着。在校园里散步、去他的教室或者没找到工作回来的路上,我们一句话不说。有时候想说什么了,我看看他,他也回头看看我,他微微笑着。那笑是透明的,像特别晴朗的大海上的天空。他像是已经知道了我的问话。 他不说话。他用眼睛说话。他的眼睛坦诚、温暖甚而灵动。可是谁能知道,他的死一般的沉寂是怎样一个深洞呢,谁能知道,那无声无息的深洞里有着怎样的孤独呢? “不好沟通。”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是这样拒绝他。小学8年,中学6年,大学3年,这17年,肖华最主要的精力其实都用在克服“沟通”这两个字上。他以为自己可以了。他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他能用字准确地表达出他的内心。常人也许完全没法去体会,对于永远生活在那个无声世界中的人来说,读懂一个字,写出一个字,理解一个字,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然而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攻克下来了,他们知道,这也许是通往正常世界的唯一途径,他们没有退路。 “优秀团干部”、“精神文明标兵”、“学习标兵”、“江苏省政府奖学金”……肖华拿出各种各样的证书,肖华给我看他的散文。肖华是班长,是学生会副主席。肖华选择了“计算机信息管理”的专业,他以为跟计算机打交道了,就能弥补一点“与人不好沟通”的缺陷。他说他是不会屈从的,他也不能屈从这命运。 “父亲,母亲还有姐姐,在看着我。” 肖华已经不能回家,因为他不能让家人知道,他的无奈他的悲伤。他会在这座城市苦苦支撑下去,只为了一家人能感到渺茫的希望。 “父亲已经老了,也不教学了。” “我跟他说,不工作了,就在家陪陪妈妈吧。多少年,妈妈一直是一个人在家。” “爸爸说,还可以再干干。好在你马上就毕业了,等你工作了,就回家。” 他父亲工作了几十年的那个学校,我曾经上过学的那个学校,已经关闭了。听家乡的人说,学校已改作工厂,校舍大部分拆了。大礼堂、有着一根根木柱的长廊、高高的主席台,甚至那林阴道,都已不复存在。 无学可教的肖老师去了县城,给一家小店看柜台。 肖华是不能说话,我是不爱说话,沉默,让我们感到放松,一种亲切感弥漫在我们之间。灯光,给肖华年轻的身影打上柔和的轮廓,他身后的一切隐在黑暗里。恍惚之间,肖华年迈的双亲、苍白的姐姐出现在背景里。于他们而言,肖华大学毕业时间的临近,便是他们艰辛劳作的收获季节了,命运就要改变了。这是他们将近30年的期望。 肖华,这个有着明朗笑容的小伙子,他能承受这生活的重压吗?我探寻地看看他,他看看我,眼睛明澈、坦荡,我想,有着这样眼神的他,应是无畏的。 南京日报记者申赋渔 实习生丁珊珊 (编辑 丹妮)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