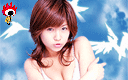“纯情者” 张国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钢铁教授”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07日10:44 河北日报 |
|
他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他最近的愿望是退休后写一本自传;他一生中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听从党组织的安排,但他干什么喜欢什么。 2月23日,记者再次采访“全国优秀教师”张国滨。在轻松的气氛中,记者和他聊起天来。平淡中,我们感受到了这位“钢铁教授”的真情人生。 人物档案 张国滨,男,一九五○年出生于哈尔滨市,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一九七四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四年九月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习,一九七七年毕业后到位于唐山的河北矿冶学院任教。现为河北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他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刻苦钻研,锐意进取,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他主讲的课程被评为河北省“精品课程”;撰写的论文,数量、质量在教师中名列前茅;其科研成果为国家创造了近二亿元的经济效益。在身患癌症后,他克服放疗、化疗的剧烈反应,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舍己忘我、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被人们誉为“钢铁教授”。二○○四年九月,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省委日前决定,授予张国滨“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听从组织安排成了我的人生惯性 新闻纵深:看到您精神状态很好,首先祝您早日康复。最近除了上课、治疗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打算或想法? 张国滨:最近常常想,退休后写一本自传,甚至构思可以分几个阶段。我的人生经历看起来很简单,但经历却很丰富。 回过头来想我的经历,感触最深的是我的一生处处都听党的话,好像人生的每一步都在服从组织安排,从没有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有时候心里有点想法,但组织既然安排了,我也就想,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的一生就是在这种“惯性”中走过的。 新闻纵深:为什么这样说呢? 张国滨:难道不是吗?1968年,我18岁。和几个同龄人响应毛主席屯垦戍边的号召,涌入上山下乡的大潮,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那时候最羡慕当兵的,一身戎装,闪闪的帽徽、红红的领章,很是潇洒。 后来领导让我当卫生员,我就去学医了。等兵团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时候,我又被推荐到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习轧钢,毕业分配时本来可以留校,但最终却听从组织安排来到地震后的唐山。1978年、1979年两次想报考研究生,但都因工作需要,最后听从组织安排而作罢。 新闻纵深:你感觉自己的想法和现实之间有矛盾和冲突吗? 张国滨:有过。在兵团当卫生员的时候,很喜欢学医,希望能上医科大学,而且上大学的冲动难以抑制。1972年,兵团派一些卫生员到大学学习,我也想去,可没敢说。实在憋不住,我就找指导员谈了自己上大学的想法。指导员问上大学想学什么,我就说学医。但最终却学起了轧钢。 新闻纵深: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遗憾吗? 张国滨:感到最遗憾的一次是,1985年我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东北工学院的“助教进修班”,并修满硕士研究生的全部课程,再有一年就能拿到硕士学位了,但领导不同意,说需要我回来上课,我就服从安排回来了。现在想起来还十分后悔。有时想,若当时不回来结果会怎么样呢?不过现在看起来虽然有遗憾,毕竟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并没有影响我搞科学研究。 其实干什么我都能钻进去 新闻纵深:每一次工作岗位调整后,你都干得有声有色,这种动力来自哪里? 张国滨:我干什么都能钻进去。你们不知练习,后来就在自己身上扎,慢慢就熟练了。在大学期间我给很多同学扎过针灸;成家后孩子、爱人感冒什么的,需要打针,有时我也给打。就连我输液,有时也自己扎呢。 之所以干什么学得较快,可能跟我自学能力较强有关吧。 当时学医也给我带来了好处,兵团在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时候,要在200多名知青里选3个,最后定下2个,比例很小。但因为我经常为大家看病,接触多,人缘儿比较好,投票选举结果是我的票最多。 新闻纵深:到兵团的时候你的文化程度是什么? 张国滨:初中毕业,我就读的哈尔滨八中是市重点中学,教学质量挺好的,从小就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到北大荒后,因为可以看的书少,我通读过毛泽东选集,还有马克思的一些著作,有些著作读起来比较难懂,我就到处查找参考资料,逐渐培养了一种自学习惯。对于我来说,自学是最好的老师。包括以后想上大学,我让父母找了很多高中的数理化课本,都是自学完成的。 新闻纵深:干什么喜欢什么是否跟你的性格有关? 张国滨:我这个人比较外向。年轻时在领导眼里属于比较机灵的,而且喜欢运动。有人说我干啥像啥,也有人说我是“多才多艺”。当时在兵团的同龄人里也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领导可能考虑,让这个小伙子学点什么东西吧!就给我安排了。初到兵团才3个月我就当上了副排长,说明领导可能觉得我还行吧。 我所在的连队很偏远,当卫生员给了我广泛接触人的机会。无论谁找我看病打针,也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我都是有求必应。记得有年冬天后半夜给一老乡家的孩子看病,回来时天黑漆漆的还刮着北风,一个人走在路上,心里直害怕,因北大荒野兽很多,比如狼、熊什么的。为了给自己壮胆儿,我就边走边大声唱歌,想起来很好笑。 研究钢铁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新闻纵深: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钢铁教授”,除了人们认为你意志坚强外,还因为你是研究钢铁的。当初得知被安排到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上大学时是什么感觉? 张国滨:1974年8月末,我接到一个大信封,一看是来自西安冶金建设学院的录取通知,再看是轧钢专业,自己压根儿就没听说过。除了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脑子里从没有过钢铁这根弦儿。原本跟指导员说希望自己能进哈尔滨医科大学,没想到最后竟然是学钢铁。而且,学校离家还那么远,这与当初的愿望相差太远了。 但这毕竟实现了我上大学的梦想,也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永远忘不了,1974年9月17日是我离开我为之奋斗了6年的兵团的日子,几乎全连的人包括男女老少都赶来给我送行,很多人都掉了泪,我也哭得一塌糊涂———难以割舍的北大荒啊! 新闻纵深:但你还是接受了这一现实。 张国滨:我记得很清楚,到学校后,教专业课的老师带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到陕西钢厂参观,当时轧钢的技术水平十分落后,生产环境很差,都是人工操作。心想学这个真不如学医。但老师告诉我们,钢铁是国家的基础工业,国防建设、盖楼建桥都需要钢铁,经济发展更离不开钢铁。正因为我们的钢铁产业落后,才需要你们来学习。听了这些话,我就想,钢铁这么重要!我就好好学吧!就开始了我认真钻研轧钢技术的生涯。 新闻纵深:面对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当时你有信心学好吗? 张国滨:我特别珍惜这次上大学的机会,可以说我是班上惟一一个每天晚上都到教室上自习的人,有时很晚了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就想起远在哈尔滨的父母,不知不觉眼里就溢出泪来。但强烈的求知欲望使我刻苦地学习专业知识。老师说学轧钢首先得学会绘图识图,说这就是工程师的语言,否则还搞什么设计,轧什么钢? 我没进过工厂,也没见过机器的零部件,所以学习机械制图时空间概念很差。但由于我离家远,又很穷,假期一般不能回家。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我把厚厚的一本“机械制图习题集”上的图几乎全画了,吃透了每一个绘图的环节,极大提高了我绘图识图的能力。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西安市钢铁厂搞加热炉的炉体设计,两个人一组合作分别设计并绘制一张零部件图。不到3天,我就做完了自己的“功课”。就又帮着其他同学设计、绘图。老师看到我设计的图纸说:“你干得好快啊,干脆总装配图也由你画吧。”装配图的绘制可比零件图复杂多了,但我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让老师也“刮目相看”了。 新闻纵深:但后来你所做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一个最费力的领域。 张国滨:搞理论方面的教学和研究的确比较费劲,但是可以让你将基础功底打得更深厚,知识面就会变得越来越宽,有时候一些课题研究甚至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理论知识才行。 当一些实验数据出来后,能跟我的理论研究结果相符,我会很激动。我睡觉有一个习惯,总在床头放上纸和笔,只要想到了一个课题研究的想法或撰写某一篇论文的思路,就马上记下来,不然怕到第二天“灵感”就没了。到现在我还这样呢。 只要爱情是真挚的,别的我都不在乎 新闻纵深:听说因为你学习好,人很聪明,很多同学都喜欢你。你和你爱人苏慧敏就是在大学期间认识的,你俩谁追的谁? 张国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有点儿近视了,但配不起眼镜,所以上课时总坐在第一排。我身后就是苏慧敏,她常用笔捅我,问学习上的问题。时间一长,我们之间的话就多了起来,说起来还应该是我追的她吧,毕竟她是我们全系很优秀的女孩儿。因我在上大学前就入了党,在班里很“光鲜”的,觉得比现在考上博士还光荣呢! (“这回总算不是组织安排的了。”提及这一情景,记者笑称。张国滨也笑了。) 新闻纵深:从学校毕业后你就到唐山工作了,你爱人也一起来了吗? 张国滨:没有。我先来唐山报到,她回到了甘肃嘉峪关父母身边。她家条件很优越,又是家里惟一的女孩,照现在看肯定成不了了,但那时我们心里的想法是:只要爱情是真挚的,其他的问题都无所谓。后来组织上很快就把她给调来了。 我记得,来唐山前我在她家呆了20多天,为她家挖了一个很“地道”的菜窖,她爸妈特高兴。 新闻纵深:当得知患癌症后,你是怎么想的? 张国滨:开始我爱人和医生都不想让我知道,但我是学过医的,一看检查结果写着“肝占位”就知道自己可能患癌症了。我主动要求不要瞒着我,让我了解病情,会更好地配合治疗,而且我也想知道具体的治疗方法。其实癌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你看我的病不是控制得很好吗? 就在我患病后,我爱人哭着说,“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救你”。有她这句话我就知足了。都这把年纪了,她不顾一切也要留住我。可能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感情基础吧。 即使得了病,我还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新闻纵深:面对很多媒体的采访,你是否感到了压力。 张国滨:我不喜欢张扬。我想给大家说的是,我喜欢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老老实实做学问,安安心心搞研究。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跟学校里的其他老师没什么不同。若说有区别的话,可能是我更“较真儿”吧,在别人看起来有些怪,有点呆。 很多次爱人打电话让我中午早点回家将饭做上,结果在研究室一呆就忘了时间。说起来可能人家都不信,当我投入在科研领域时,就是外边打雷下雨都浑然不觉,特别容易将注意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一个“点”上。 现在大学里的老师都挺辛苦的,我们学校就有病倒的老师,而我是幸运的,得到了社会上这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 如今我得病了,人们都来宣传我,宣传我取得的成绩。其实应当看到,即使我不得病,那些所谓的成绩不都还在吗? 其实那些都不算什么,自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所做的工作都是一个大学老师应该做的小事。很多课题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哪一个项目不是一个“团队”共同艰苦努力的结果呢,将其说成我个人的成绩不合适,这让我很不安。 新闻纵深:即使在得病的情况下,你还把自己看作是幸运的? 张国滨:是的。我有时候想起当年一道上山下乡的同伴们,他们在北大荒有的呆了8年、10年后才回家的。我曾回哈尔滨看过,当年一起到北大荒的同伴,如今很多人都下岗了。我一个从小要好的伙伴,现在要靠在路边修自行车为生。跟他们比起来,我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归宿,自己的奋斗目标。很知足了。 [记者旁白:干净、整洁、利索,病中的张国滨依然保持着以往的形象。仍然不停顿地进行着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透露,在今年河北理工大学的教职工运动会上仍报名要参加两个项目的比赛。一向酷爱运动的他曾在校运动会参加过多项比赛,得过400米的第一。 张国滨,时刻流露着平凡人生中的“纯情”。]本报记者 汤润清 张许峰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