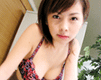我的母亲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09日13:24 人民网 |
|
一 我的母亲是位医生。1963年,母亲二十四岁时生我,所以,我与母亲属相相同,都是兔子。早前,听父亲说起,母亲怀我那阵,她在哈尔滨铁路总医院工作;大冬天里,母亲下班回家,时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研究生的父亲,在去接她的路上,经常看到母亲,挺着个大肚子,独自在雪地上行走,一不小心便象个圆皮球,滑倒在路旁。或许,这正是母亲早产生我的原因。 降生这个世界四十天,我被母亲用衣褥千包万裹着,从天寒地冻的松花江岸,送到黄浦江畔祖母家赡养。当母亲怀抱我,经过三天四夜火车的长途跋涉,抵达祖母家居的弄堂,由于南北方温差,天气转暖的缘故,包裹我的衣褥,已与我的皮肤紧紧粘在一起。第一次看到她的长孙,老祖母又惊又喜,再瞧见我衣褥连体的景况,当下就呆住了;立在一旁的母亲,顿然也手足无措。老祖母不敢亲手剥脱,浆糊一样贴着我肌体的衣褥,生怕撕伤我的皮肤,还是邻里的姑嫂们,把我合衣浸泡在温水盆中,一点一点地将衣布同我的肌肤分开。直到我一身清净,最终躺进老祖母怀俯,迈动一双三寸小脚的老祖母,接过养育我的责任,老祖母的庭院,成为我的家园。此后,我的童年早期,似乎再无与母亲同处的印记,自幼也没喝过母乳;唯一的印象,是母亲每月都会邮寄养我的钱,春节回上海过年,还要从哈尔滨,背来一大面袋白糖,留给我食用。 我六岁那年,母亲随父从大东北,调到大西北一家军用飞机研究所工作。母亲前往新单位报道前,先回上海探亲,并接了我,和她同去那个深藏陕北山沟的新工作地,一住就是大半年。其时,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先行报到的父亲,已去了山东农场锻炼,母亲被分在研究所医院工作。不知怎么,新工作刚开始,母亲就站错了队,她所属的一派,成为挨整一方;这期间,母亲每天都要开会,回家既晚,心情又不好。当然,对那段生活记忆最鲜活的,莫过于观赏母亲参与的医院舞蹈队,大跳忠字舞,以及全体医院职员,配乐合唱电影《英雄儿女》插曲。我很喜欢电影《英雄儿女》,觉得母亲她们的表演,实如电影一样情真意切,十分壮烈。 母亲秉性刚烈,本人是个相当能干的医生。当时,研究所条件简朴,我同母亲,先是住在一座土窑洞里,后来才搬至一间砖瓦平房。那阵子,我与母亲关系很生疏,从不叫她“妈妈”,有事则以“哎”称呼。还有,因为母亲是外婆的独女,自幼由两个奶妈伺候,不懂做家务,更不会烧饭。到了那个一贫如洗的偏僻山沟,父亲又不在,母亲别无它法,唯有从生火学起。记得母亲首次学习生火,还是带了一个笔记本,将别人教她的生炉子注意事项,从开始至末尾,逐项记录,回家后再照猫画虎。不管怎么讲,那个年岁的生活很简单,母亲能做给我吃的,只有大米稀饭炒鸡蛋,再就是藕粉。好在这些也是我素喜进餐的食物,加之,偶尔我会潜进邻居叔叔阿姨家,分享一些人家的菜馔,日子过得倒也逍遥自在。 和母亲共同生活的日子,我和她极少啰嗦,最不爱听她教训,但又有点怕她,便采取逃避策略,尽量把时间消磨户外,回家只是吃饭睡觉。即使人在家室,我也不言不语,她问一句,我答一句,她不言语,我连屁也没有一个,乐得清闲。 不过,那一年的生活,至今忘不了的事情,是母亲决定我提前进小学。入学考试很简单,要求孩子书写自己和家人名字之类;未曾想我考试没通过,小学没念成,这可让生性好强的母亲脸面无光。母亲痛打我一顿,之后又强迫我,每日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背不出还得挨打。那阵,我将母亲恨之入骨,及至翌年,我将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母亲方才满心欢喜地通过关系,把我直接插入二年级就读,使得我无缘学习汉语拼音。补上汉语拼音课,还是后来妹妹上小学一年级时,在家教会我的。 童年时代,我与母亲相处很不正常,母亲教子太严,我在感情上,和她过分疏远。我不认她的帐,她除了责骂我,也很少温馨,母子之间的沟痕非常明显。 在陕北山沟居住不久,父母又调迁位于西安远郊终南山脚,该家军机研究所的分部工作,总算离城市近了一些,母亲的情绪有所进步。然而,母亲于此年间,接连生养了妹妹和弟弟,自是乏力额外关照我,我则思念老祖母,于是,父母将我送返上海,再同老祖母相守,安度童年。 二 重见母亲,我已步入少年。十一岁那年,我在上海念完小学,由于户口不在当地,无法读中学,只能回到父母居住地,继续求学。临行前,老祖母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记住了,见到你母亲,一定要叫妈。我答道:记得了。 和老祖母道别,千折百回,不必尽述。但再见母亲,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八月正午。记得从上海坐火车,抵达西安那天,内心颇为激动,又有些忐忑不安。在西安火车站,被母亲的同事接上,搭乘一辆父母单位的小车,离城南行三十八公里,到达父母工作的研究所住地大院。从车上下来,顺着一道石阶上坡,行至家居的那座三层高砖砌的家属楼,走进家门时,身穿一件白衬衣的母亲,正给一位登门就诊的病人看病,“王大夫,你儿子回来了”,听闻邻居的话声,母亲放下手中的听诊器,转身面朝我,一脸笑容,“妈”,我尽量大声地叫道。 从这天起,直到中学毕业,母亲的家,成了我的家。父母工作的研究所住地,依山傍水兴建,面朝关中平原,研究所院墙外,皆是乡村农田。研究所里的数百名员工,分别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又以知识分子为主,文革前后毕业的大学生,占了职员人数的一半以上。研究所占地面积不大,院子里的孩子却不少,但与我年龄相仿的大孩子,则屈指可数。我来到的那年,研究所已开办所内幼儿园,不过尚无自己的学校。为此,母亲只能送我,去到附近一家兵器工业部工厂子弟中学借读。这家兵工厂,坐落在研究所住地隔邻的山粱里,每日上学下学,单程步行大约三十分钟。 正象我抵家之日,父亲在外地出差搞科研,我对中学年代的印记,仍以读书为主。那个地方,虽说交通闭塞,每天只有两趟进城的公共汽车,加之人烟稀少,周边全无商业,然而,那里却是一片山明水秀的乡野,滋养我易梦善感的少年心灵。居家四年中,父亲似乎永远都在出差,母亲则永远都在户外奔忙。母亲本行内科,为人治病不分昼夜,作为研究所唯一一位专业医生,她接生、打针、门诊、临床,五花八门什么都做。 母亲精力旺盛,在研究所内大名鼎鼎,她又是个极尽职责的医生,时常被人半夜唤醒,为病人看诊。印象中,母亲一般不吃早饭,夜眠往往仅有数小时,整个研究所里,她是第一号女强人。尽管如此,纵然母亲业务能力极强,自身表现积极向上,却永远入不了党,个中原因在于母亲脾性耿直,自认对的轻易不转弯,跟所长、政委都敢顶撞。母亲入党成真,还是八十年代中期,举家搬迁广东之时,面对自己将要被迫改行的工作前景,临别那个生活十六年的航空研究所,母亲毫不含糊地要求所领导给一张党票,作为她倾心贡献一生最珍贵岁月的补偿。母亲的坚定不移,最终令她跨进她那代人,孜孜以求半辈子的共产党门槛。想起母亲的苦斗精神,我常为她感惜。 少年时代里,我同母亲单独相处的时间极少,母子俩的关系不尽和谐。一方面,母亲热衷在外夸赞我,使我被邻居树为教育子女的楷模;另一方面,母亲却很少在家与我欢笑。母亲望子成龙心切,觉得我必须随时前进,她的职责,就是督促严教,如此,忽略了母子之间,正常的亲情与温暖。在这方面,母亲一点也不聪明,虽然她给了我,物质上她能给予的,比如每趟进城,母亲都会带我上馆子开洋荤,所有好的衣服什物,她也凭力充分供应,但是,母亲过多付诸事业工作,不自觉地漠视了,孩子对母爱的正常需求。 还记得,母亲一直希望返乡上海,但十数年无法全梦。母亲是个医生,天性中秉存艺术禀赋,母亲还是个理想主义者,却因性格自强,在政治上履遭冲击。对自己的命运无力左右,母亲唯将深心希望,加倍寄托儿女身上,对这一点,我充分理解。母亲很象她那代人的缩影,付出太多,酬报太少,加之她们的生命,耗损地无昼无夜,青春的岁月不曾美好,人到中年季节,甚至没有伤心和悲哀的时间。 我极少看到母亲哭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1年夏季,母亲敬爱的生母在上海病逝,对于身为家中独女的母亲而言,这是继年前外祖父死后的又一重大打击。当时,母亲渴望去上海给外祖母送葬,但她的这一央求,却被研究所领导,以政治理由拒绝。那是我唯一一次,亲眼目睹母亲,在大庭广众下嚎啕痛哭,那种撕心裂肺的悲音,我永难忘记。 正是那个年代的严酷,冰结了母亲真诚的平和天性,并使母亲的善良,变得凉瑟,除去自己的儿女,漫漫国土上,咸有值得信赖的人。 三 中学毕业后,我考上大学,又与母亲千里相隔。正真亲近母亲,还是当我长大成人,也缘于时事境迁,母子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正常。其实,母亲十分疼爱我;而且,母亲还有许多出众的优点,象对子女的个人事宜,母亲表现得相当民主,一般不轻易干涉。 第三次同母亲生活一处,是在深圳的四年。1985年,当全家搬往深圳时,我已大学毕业,分配在秦岭山川,一家大型军工厂工作,不能随父母南迁。为此,母亲初到深圳新地,即刻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为我的调动操碎了心。时值广东夏天,岭南酷暑让人生畏,但年近半百的母亲,却不屈不挠;为了我的户口指标,能于我的工作单位,同意放我前,继续保留深圳人事局,母亲时常在下班后,踏着自行车,从城的这头,骑到城的那头,利用她的针灸绝技,上门给当权者家人义务看病。直到翌年,我所在工厂终于放人,亲眼见到我在身边,母亲才松下一口气。 人在广东年间,一如我的习惯,室外疯狂的时辰,远较居家为多。经常母亲见我回家,都当我困难的日子,或是弹尽粮绝了,或是生不如意了。母亲一般不刨根究底,也不大责难我的是非,而是见到我就很开心。其实,母亲对我的行踪,颇为了如指掌,缘于我的周围同事,随时向她通风报信。针对母亲的认识,一个显著特征,即是母亲给予子女足够空间,她的评判准则很简洁,物尽人事,心随灵意,只要我没有危险便可以。 在母亲不刻意地监护下,我十分自由,更感亲近母亲,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母子俩,喜欢坐下来,做点家常琐事,再就海阔天空地闲聊。生活境遇的好转,无疑从根本上,恢复了母亲天性中,悠然自得的一面。 对待子女个人生活,母亲历来宽容有加,但对子女前程,母亲则重之慎之,从不丝毫懈待;对我人生重大选择,母亲都会严肃把关,并全力扶持。1990年春天,我到澳洲留学,不想一去无返。出国之际,父亲的要求很简单,在外混不下去就回家;但母亲对我充满热望,离境的前夜,母亲将我单独叫去,一片语重心长的话谈,还把她经年积蓄的一笔私房钱给我,叮嘱我人要勇敢,遇到困难不气馁。去香港那天中午,母亲要了单位的面包车,往罗湖桥海关送我。为免母亲流泪,父亲只让母亲送我下楼上车,从车窗口向母亲告别,内心充满不舍的依恋。 刚到雪梨的日子,我人生地疏,又无英语能力,在英语学院和歌剧院餐厅勤工俭学,生活很清苦。不顺心的时候,也给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的母亲,都会鼓舞我: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经年既逝,妹弟业已人当三十,母亲退休也逾十载。母亲年纪与日俱增,面容逐渐显现老态,但对人生热情无改。诚如她的同辈,母亲退休后,似乎比工作之年更繁忙。母亲性格乐观开朗,离开工作环境,为使自己不脱离社会,她就一个缝纫班,一个烹饪班地不停学习,还将自己注册成人学院,修读法律经济。母亲拿回家的各类文凭枚不胜举,比全家人文凭总和还多,为此,老少家人常会笑话她,数落她不先把家里收拾整洁,反而化钱买废纸,带回家更多垃圾。对众人的声言,母亲听后也不反驳,只是笑得象个未出阁的大姑娘,依旧我行我素。 母亲是个天塌下来,也不怕的骄傲女人,对子女的教养,有自己一套独特逻辑。母亲亦是家里的顶粱柱,在我们三个子女心目中,母亲一若钢筋铁骨打造,从无任何闪失。然而,2005年春天,母亲不慎跌倒,摔折了腰骨。一直将治病救人作己任的母亲,这回可轮到了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重伤,静卧床榻一百天,被人全日制料理。 母亲住院期间,在电话上念叨,她人困病床,无法用电脑上网,即时了解股市行情;其次,就是每回越洋通话,母亲都要主动向同在澳洲的妹妹与我,详叙她的病况,并同康复进展,以使我们安然生活,莫要为她担忧。 我知道,母亲心怀里,负荷最重的部分,仍是对子女的思虑和寄望,母亲对子女的关爱无边。正如母亲生龙活虎之日,我们眼中的母亲很平凡,但当母亲突然倒下,面对应声倾斜的家庭中轴,身为子女的我们,才皤然悟觉母亲的伟大。我与母亲之间的故事,母子亲情的深厚,于时光的延续里淀积,回顾既往岁月,想起一首我早年撰写的诗歌:《给母亲的歌》,诗的结尾唱道: “母亲的油灯不熄呵――― 你正是火苗,擦燃记忆” 在此,将这首诗歌,献给我的母亲。(伊名)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