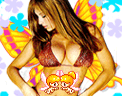秋菊的秩序世界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2日08:20 法制日报 |
|
文化随笔 刘楠 秩序的决定者或许是国家或社会,但对秩序的感觉,却属于这个国家或社会的个人。 从秋菊看到同是自己冤家和恩人的村长被警车带走时那迷惘的眼神里,人们或看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或看到了旧秩序的衰退,新秩序的阵痛;或看到了无奈和尴尬。显然,秋菊对两种制度和秩序带来的结果都是失望的,村长没有道歉,她也不希望村长被抓。那条延伸向天边的乡间小路,给了我们无穷的想象与暗示,不断激发人们去诠释秋菊“说法”的意义。是她对尊严、平等的追求?是利用现有制度资源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是某种捉摸不透的自然法?有一点可以肯定,秋菊的“说法”,显然既不属于“集体所有制”的习俗或民间法———上访本身就是对村子自然秩序的反叛,也不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法———秋菊触摸到了又害怕地缩回了手。那些普遍性的规则都暂时在秋菊那里失效了,发生作用的,是秋菊“个体所有制”的秩序感,是她的“可以打但不能打那”的权衡,是仅仅属于秋菊在特定的时空和语境下的秩序世界。 贡布里希在其名著《秩序感》中认为,秩序感既来源于心理需求,同时也是作为高级生物的人类的一种美感。秩序感首先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决定,但亦有自身的独立性。因此一种秩序的尺度可能影响主体的判断,但不必然符合主体的秩序感。我们在说秩序世界本身是客观存在的时候,而秩序感却是主观的,是人各不同的。当我们看到百万红卫兵齐聚天安门时,排山倒海的口号让我们看到另类秩序的美感,当我们看到几千年的“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男耕女织的生活场景时,我们也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秩序美感。在美学领域,有人认为人天生就有“补白”的冲动,对已经存在的画面的不满意,表明了主观的秩序感与现实存在的距离和裂缝。对现实秩序世界的“补白”是绵延历史长河的延续,而不是彻底颠覆,否则我们会更加焦虑和不安。漂泊感常常唤起我们去讴歌旧世界中令人怀念的东西,混沌中我们对寻找新秩序迫不及待,想要一个心甘情愿归顺的家。 寻找家园的,不仅有精英们,也有秋菊式的大众。电影有意识地时光倒错展示给我们的正是几千年波澜壮阔的寻找家园的画面。从乡野那条延伸到城镇和都市的小路,从步行、人力车、畜力车到汽车,从自然经济到现代化,从传统到“西洋镜”,秋菊恍惚在跨越着时空讨“说法”。精英的参与创造秩序也许更能借助于知识,但秋菊们“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智慧和勇气也同样值得尊重。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秩序世界,他也试图通过自己主观的秩序感改变着现实的秩序世界。秋菊村子里也是如此,例如村长骂他老婆“你懂个屁”,表明了他强烈的关于权力的秩序感,风雪之夜送秋菊上医院是村长的关于义务的秩序感,“送她上医院与打官司是两码事”表明他的秩序感由于体制内的教育与信息让他也在被现实世界决定着。假如上访的是冬梅而不是秋菊,难说她不会把村长给的钱从地上拣起,难说她不会对村长被抓而拍手称快,这是和现实秩序世界的妥协,是秩序世界的重合,或者是某种生存智慧。在大多数时候,村子里的人们的秩序感是同向的,是一种共识,是历史形成的默契,人们因而对行为和事件都有稳定的预期,而叛逆者、破坏者一般都会受到唾弃、责难。但当有人完全无视有关生存的功利去追求自己的秩序世界时,我们就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了。 这让人想起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废奴主义者的罗伯特·哈代。哈代是个技艺娴熟的箍桶匠,他孑然一身,少言寡语,逆来顺受,似乎甘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他耽于幻想,酷爱读书,神情独异,因此不被人接受。有一天,哈代突然毫不掩饰地宣布自己是个废奴主义者,人们大吃一惊,感到他大逆不道,纷纷要求用私刑把他处死,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说了一番富有情理的话,才使他免招一劫。牧师说:“哈代精神失常了,不能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因为主张废奴是一桩滔天大罪,精神健全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们相信了牧师的话,从此总是把哈代的话当成胡言乱语和笑料,尽管哈代难以忍受,恳求人们相信他是诚心主张废奴的。人们对他的恳求置若罔闻,以更为顽劣的心态忽略他。直到有一天他帮助一名黑奴逃向自由而杀死抓他的警察,人们相信了他真实的信仰。在对哈代的审判中,无人为他作证,除了他自己证明自己有罪。但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在心中逐渐认为哈代是英雄。 当秋菊拒绝将村长扔在地上的钱拣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秋菊上访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决定她的现实秩序世界,她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与村长的苟同、不是为了获得任何机会主义的利益。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在被历史决定、型构或格式化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地经由自己的秩序感对现实世界进行着想象与重构,只不过人们通常都会选择作机会主义的奴隶。机会主义在这里是个中性概念,很难说可耻,正如墨子所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这是人们自身的秩序感在发生作用。但我们在对机会主义者保持宽容的同时,可怜的秋菊难道真的只能回到那个她并不喜欢的秩序世界中去吗? 人们就在这种秩序感的重合与冲突中随历史前进。一种秩序感可能首先属于某个人,甚至某个小人物,然后唤起一个时代的共鸣,因为那时历史已经走到容易引起共鸣的地方了,正如哈代们、秋菊们,乃至孙志刚们。在许多场合,更多的人的秩序感是不为人注意的,就如雪地鸿爪,但他们的确来过了这个世界。秩序感的重合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就像基督徒齐唱赞美诗。但当一个不和谐音出现时,假如她的声音很动听,人们会和着她,假如她的声音太难听,不用担心,她自然会回到人们的和声中,而差异和多样并非必然是和谐的敌人。 “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树叶在枝头颤动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那儿了。”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博士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