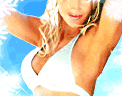刀耕火种竟成为人类新文明的星星火种?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5日14:12 人民网 |
|
半年前,在一场关于“金光集团毁林事件”而起的争论中,一位专业是社会学、对人类学也有所研究的朋友举出云南大学教授尹绍亭所者的《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一书(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下简称尹书),说它充分地论证了刀耕火种也是一种先进的、合乎生态学的生产方式,借此反对在云南用种植桉树的办法使当地居民致富。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在伪环保人士创办的“情系怒江”网站上,又看到了田松的《稻香园随笔之二十二——刀耕火种的生存智慧》,里面也提到了尹书,田松并以此为据 ,说什么“中国依然拥有传统尚存的地区,是中国的幸运。……当日疯一日的工业文明体系崩溃的时候,那里才是人类文明最为可能的方舟,也最有可能成为人类新文明的星星火种。”这更使我想看看尹书究竟是何方圣经,到底是怎么替刀耕火种“翻案”的。看过之后,我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刀耕火种确实是一种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这是怎么也翻不了案的;由于作者对现代科学的不了解,以及其所持的弱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对于刀耕火种不免有过分拔高之嫌。第二,尽管如此,作者本人对于刀耕火种的叙述和评论,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客观平实的,而且坚持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所以极端文化相对主义和极端环保人士对于这本书的吹捧,如果不是出于误读,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具体来说,由于尹绍亭教授是人类学家,尹书又是在所谓“生态人类学”的视野下写成的,所以书中不可避免地洋溢着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氛围。在全书终章“文化、自然与发展”中,作者称:“事实说明,文化是多元的,是相对的,每一种文化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绝对先进、优秀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因而文化的取代就是不科学和不可取的了。”(348页)这是典型的文化相对主义论述。 但是,正如上面提到的,作者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是一种弱文化相对主义,从而有别于田松的强文化相对主义,也即极端文化相对主义。强文化相对主义不仅否认不同文化之间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别,而且否认文化是进化的,或只承认文化的分异,不承认文化的趋同,认为文化的趋同一定是强势文化的进攻造成的弱势文化的灭绝,从而激烈反对一切对“弱势”文化的影响和改造;弱文化相对主义则承认文化是进化的,并且承认尽管各种异质的文化同时保存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如果现实条件不允许这样做,则有可能通过对弱势文化的温和的影响和改造,在尽可能保护其独特内容的同时,使之与强势文化趋同。 文化的进化,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著名生物学家、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就提到了文化进化的问题,并把文化进化中类似于基因的最小单位称为meme;方舟子在一系列文章中进一步指出,文化进化遵循的是拉马克式进化,而不是达尔文式进化。但是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最大不同,在于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属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因此具有内在价值,也就可以进行道德评判。方舟子曾指出,生物进化是没有目的性的“一次次试错”,而文化进化则是有目的性的自我改造,其动机是人类希望保障社会存在和发展、增进每个人利益的欲望,这是所有人类文化共同的,尽管对于不同的文化,这个欲望的具体表现形式也不同。 正因为如此,所以文化之间是必然可以分出高下的。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文化相对主义逻辑的内在矛盾》的文章,驳斥的是田松的另一篇文章《稻香园随笔之二十一——要年薪多少才能日日欢歌?》。文章的观点就是说,既然所有人类文化都有相同的对过更好生活的期望,显然,越符合这个期望的文化,就越先进,反之就越落后(也就是说,田松以为是强势文化强加给弱势文化的“冥尺”,其实正是客观存在的),这样,对于落后的文化,尊重其过更好生活的期望和拒绝先进的工业文明的影响、渗透,就成了一对矛盾。基于这个观点,我一向反对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对于否认文化进化的极端文化相对主义,更是嗤之以鼻。 好在尹绍亭教授是个弱文化相对主义者。在尹书第三章中,作者称:“文化传统、文化特质和民族特性是不可以强行改变的,然而这并非是说它们是不可改变的。任何文化都不是静止、僵化的,而是动态的、演变的。”(287页)这显然是承认了文化进化,而且和水博在《怒江水电开发中的民族文化保护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没有静止的民族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终章”中,作者又称:“如果抓好混林农业和水田农业,那么就可能完全解决山地民族的粮食问题,刀耕火种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大部分轮歇地就可以退耕还林,云南山地的生态面貌就将大为改观。”这不仅是同意对刀耕火种这种弱势文化的影响和改造,而且还指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这种弱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显然和田松的“人民有愚昧的自由”的极端文化相对主义截然不同。 但是,弱文化相对主义毕竟也是文化相对主义。尹绍亭在书中矫枉过正地反对把刀耕火种称为是“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在尹书绪论中,作者称:“本研究将摆脱传统观点的束缚,跳出‘原始’的视野,摒弃‘落后’的偏见,从人与自然、人与森林相互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审视刀耕火种,同时运用‘生态人类系统’的概念进行分析和整合,并探讨研究系统中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及其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从而达到揭示人与自然、人与森林和谐相处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规律的目的。”(14页)实际上,作者反对的是“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傲慢粗暴的态度”(375页),以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实施的“完全排斥民族传统文化、脱离当地的自然条件等实际情况”(351页)的发展思路和规划目标,这当然是对的,但并不能就证明刀耕火种不是“原始”、“落后”的。 什么是原始?从字面上讲,原始就是较早出现的意思,一种“原始”的劳动技术,必然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发明的劳动技术;以后,它可能会被较进步的技术取代,但也可能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原来技术的本质特征不变(虽然在细节上可以有很多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始”一词并无贬义,也就是说,“原始”的并不一定就是落后的。比如人类至今仍然需要通过吃其他的生物获取代谢所需的物质和能量,而不能像叶永烈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那样,从无机质大量合成淀粉、蛋白质和脂肪,代替对植物的栽培和对动物的饲养获得食物;那么比起这种幻想的获得食物的技术,现在的农业就显得十分“原始”。 尹绍亭辩白说:“如果把云南的刀耕火种说成是农业史上原始阶段的刀耕,那就错了。”(247页)经过他的考察,我们知道,云南的刀耕火种确实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耕作方式,远非远古人类的刀耕火种可以相比,但是单就“刀耕火种”这种技术来说,它确实比锄耕、犁耕更原始,又是经考古学证明了的毋庸置疑的事实。尽管云南的刀耕火种和中原王朝核心地区的农业技术是从远古的刀耕火种的根基上各自独立进化的两支,但它保留了远古的刀耕火种技术较多的内容,又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生物学家常说“细菌比动植物更原始”一样,其实是说比起动植物来,细菌的结构、形态和生活史更接近于地球上全部生物的共同祖先,而不是说细菌和这个共同祖先就完全一样。所以,说云南的刀耕火种比较“原始”,又有何不妥? 至于说刀耕火种是“落后”的,也有依据。整本尹书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论述刀耕火种不落后,作者甚至几次说什么:“通过对轮歇类型的考察,我们看到了生态环境是怎样从广袤、茂密的森林逐渐变成荒凉、贫瘠的草地,也看到了刀耕火种民族是怎样从富饶、优裕走向贫困和危机。”(235页)“就当代所发生的刀耕向锄耕、犁耕演变的情况来看,与其说是进化倒不如说退化更为合适。因为这种演变并不是从技术的角度进行选择的结果,即并不是高水平技术对低水平技术的取代的淘汰,而是生态破坏后的被迫选择,是生存危机的无奈。”(247页)然而,我从书中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刀耕火种惊人的落后一面。 比如,刀耕火种农业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即使它一时能保持生态平衡,在人口增长之后还能不能继续保持?对此问题,作者无法回避,只好承认:“无轮作轮歇类型的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假设人均拥有土地面积下降到25亩甚至20亩以下时,……就将陷于崩溃。”(213-214页)既然如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放弃刀耕火种这种方式,采取更先进、更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而且从作者给出的人口普查资料,有的少数民族的人口其实增加得很有限。比如景颇族,1953年是102811人,1995年不过是121900人,增加不到五分之一;佤族,1953年是286161人,1995年也只增加到360200人,增加了四分之一强,均远远低于同自治州其他各少数民族以及总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可是,在景颇族聚居的盈江县卡场乡,变得“土地抛荒之后没有足够的休闲期,变成杂草地,地力恢复不了,再次耕种产出减少,陷于恶性循环的状态之中”(234页),西盟佤族“由于人口的增长,村民仅靠砍种麻卡地已不足维持生计,所以在打洛以至整个西盟地区,又普遍实行着短期轮作耕种方式,在此基础上,还发展了少量的水田和台地。”(139-140页),我实在不解,像这样脆弱的“人类生态系统”,连如此轻微的人口增长压力都承受不了,究竟“先进”在哪里?而且上文已述,作者明确指出,混林农业和水田农业是可以代替刀耕火种的,而且混林农业“并不是现在的发明和创造,而是一些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的传统经典技术”(353页),水田农业“较之刀耕火种,具有不必轮歇,节约土地,不消耗森林资源,耕作省力,粮食产量高等优点”(355页),难道这也是“走向贫困和危机”,也是“退化”?特别是水田的耕作不可避免地要用锄、用犁,按作者的观点,这不正是“退化”吗?这样一来,尹书本身前后就出现了矛盾,这个矛盾正是文化相对主义因不承认文化高下之别而造成的逻辑内在矛盾的又一种具体表现。 再来看尹书中的几个个例分析。书的第二章,题为“传统刀耕火种志”,由盈江卡场景颇族、勐海布朗族、西盟佤族、勐腊基诺山基诺族、贡山独龙族五个刀耕火种田野调查报告组成。作者对盈江卡场景颇族的无轮作轮歇、造林休闲的定居型刀耕火种赞赏有加: 人类早期的原始农业,似乎多采取多种作物混种的形式,而景颇族的百宝地却 非盲目无知、随心所欲地混种。它有地类作物、早熟作物和晚熟作物合理配置的经 验,有防灾保收的目的,还有改善地力,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功效。……实行多种 作物间种、套种,具有几下几个显著的优点。第一,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和阳光。 ……第二,可以提高土地肥力并充分利用地力。……第三,可以抗灾保收。……第 四,可以满足人们生活的多种需求。……第五,可以节省劳力。……第六,单位面 积的作物产量比较高。……这种貌似粗放的栽培技术,就是与当代化学农业相比, 其一些显著的优点也是不言而喻的。令人遗憾的是,景颇族代代相传的“百宝地” 种植技艺以及粮林轮作的优良传统,竟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合作化运动中毫无道 理地被当做“原始残余”而被取缔了。(86-95页)如此说来,景颇族的刀耕火种在栽培技术上简直可以和“当代化学农业”媲美了。然而仔细想想,就能发现至少两个问题: 第一,所谓“单位面积的作物产量比较高”是基于错误计算而造成的假象。作者引用了几份当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所作的粮食生产情况报告,其中一份称:“……在2.25亩的旱地内,收获……共458公斤,还有其他蔬菜瓜果,平均亩产值90多元人民币,等于3.5亩水田的收入。”(93页)作者因此说:“百宝地的作物亩产量,就是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也是十分可观的”(94页)。然而,要知道这样高的亩产量,是以撂荒了八倍、九倍于当年耕种地面积的土地为代价的,换句话说,为了要获得这样高的亩产量,就不得不有八倍、九倍面积的土地白白搁置,得不到直接利用(充其量是像作者下文说的,可以提供些薪材、食用菌之类的副产品)。这样的话,要计算亩产量就必须把撂荒地的面积也考虑在内,方才合理。这样一来,实际上的亩产量自然就要大大下降,不但比不上水田,连半亩水田的收入都不及。这样低的产量,还能算是“显著的优点”吗? 第二,其他“显著的优点”,也并不是景颇族的刀耕火种所独有的,而且完全都可以用现代生态学来解释。比如“可以提高土地肥力并充分利用地力”,指的是景颇族栽种豆科农作物和水冬瓜树能够使土地变得肥沃。作者自己已经指出,“那是因为它们的根部具有可以固定氮素的根瘤菌的缘故”,这正是生态学的常识,而不是什么不能被认识的神秘现象。我不明白一种连现象的本质都不理解的文化,比起能够理解现象的本质的文化,究竟“先进”在哪里?又如,多种作物的混种制不光是景颇族在采用,汉族劳动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采用了,而且到了6世纪30年代竟然出现了在5亩“灼然良沃”的土地内穿插种植了瓜、萝卜、茄子、葱、葵、莴苣、蔓菁、芥、白豆、小豆等10种作物的实况(见《中国植物学史》29页,中国植物学会编,科学出版社,1994年),而且还是在轮作、施肥的情况下完成的。相比之下,我实在看不出景颇族的这种无轮作的混种有什么“显著的优点”,更不用说和现代生态学理论指导下的热带生态农业[比如中美洲的荫生咖啡(shadecoffee)种植]相比了。 后面勐海布朗族、西盟佤族、勐腊基诺山基诺族、贡山独龙族四个田野考察报告显示出来的,不仅不再有什么“显著的优点”,反而有不少可以充分论证刀耕火种落后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如勐海布朗族,作者说:“因垦殖过度,不少地方植被退化为稀树灌木林和稀树草地。”(100页)而且勐海布朗族和西盟佤族都曾经以栽种罂粟为主要的经济作物,西盟甚至到上世纪60年代初才彻底根除了罂粟种植,这样的刀耕火种,“优点”何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西盟佤族的“猎头祭谷”的习俗,充分暴露了基于一个落后的耕作方式的落后文化的残酷一面: 如在埋伏时,见有单身过客或少数商队,即静伏不动,待其走近巫师所撒米、 盐、姜的范围内,即先发一箭或一梭标,过客被射倒地,伏者一冲而出,争砍人 头,砍得人头者,即张口饮血,弃其尸身于路旁。用草或树叶,将人头包扎,放在 一竹篮或背袋内,由得头者背之星夜驰归,沿途欢呼跳跃,并鸣放火枪。……人头 在木头上祭供三日;祭期已过,巫师用竹竿一根,长约两公尺,一端劈破成数条, 撑开如一罩,作头骨架子,将人头嵌置其中,外以稻草包扎之,插植在鼓亭之旁。 人头在骨头架上,日晒雨淋,经若干时日,逐渐腐烂而有雨水下滴于地。时至旱谷 苗长尺余,巫师挖取头骨架下泥土,分成若干小块,分送寨中每家一块,各家收到 血土再和以泥土,洒在自家旱谷地内,据说一经洒上血土,谷苗即欣欣向荣。 (146-148页,引自凌纯声《云南卡瓦与台湾高山族的猎首祭》,载台湾大学《考 古人类学刊》,1953(2))如果按照作者的系统论逻辑,这样的残酷文化,既然是处在“刀耕火种文化系统树”中的,而且“如果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那么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子系统甚至整个系统失去平衡”(14页),那么我们就应该保留这样的残酷文化了吗?好在作者基于弱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在上面这段话之后紧接着说:“而当系统陷于紊乱状态时,系统可以依赖自身的调节机制的调适,使其恢复平衡,从而达到新的良性循环的状态。”算是避免了一个可怕的悖论的出现,但是这样的可怕悖论,在田松式的极端文化相对主义那里,简直是一定要出现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想云南的刀耕火种是不是一种“原始”、“落后”的农业技术,已经昭然若揭了,而田松对尹书断章取义的解读,实在令人不齿。最后要说明的,是尹绍亭在全书中自始至终都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他对于“环保专家”十分不满,这在“终章”的一开始的一段话中表现得很明显: 而且,当生态环境保护成为热点之后,有的学者马上又成了“环保专家”,恨 不得把山区的农地全变为森林,巴不得漫山遍野都是大象,而忘了森林中的民族也 是要吃饭、要生存的,忘了一头大象一餐会吃掉几亩庄稼,还会把人抛到天上然后 再用脚踩死。诚然,生态环境以及动植物资源都必须保护和珍爱,然而山地民族的 生存和发展也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337页)我由此奉劝那些信奉形形色色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家和极端环保人士们:如果你们用尹绍亭教授的这本书去证明自己的观点,将不仅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是对尹教授的侮辱!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