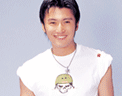友情老而弥笃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15日03:47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 ||
|
我父亲邓广铭和臧克家是70多年的老友。他二人自1923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时就是同班同学。此后多年,一直来往不断。用臧伯伯的话说,他们“七十多年来互通心声、互诉衷情”。季羡林也是山东人,20世纪30年代就和父亲相识。后来季远去德国留学,1946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如此,这三位智者、学者、诗人又相聚在北京,使他们能 密切交往,友谊历久而弥深。洋溢着诗情和热情的信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行动还自如的时候,父亲和季羡林伯伯定期或不定期地到臧家小聚。臧伯伯重感情,诗兴浓,下笔又快,往往在小聚之后的当天就写封信寄来。到了80年代后期以至90年代,老人们行动不便,就主要靠信件和电话来互通信息了。1998年初父亲病逝之后,妹妹小南从他的遗物中找出近20年来臧伯伯的80多封来信,封封洋溢着炽热的友情和诗情。下面摘录几封。 1975年4月14日的一封长达3页的信,最后说: “读这样信,老友一定不嫌罗嗦反觉如饮醇醪吧?我书此,用的不是蓝墨水而是红色的诗情也,以为然乎? “每次看到古人集中与友人书(如陈亮……),觉大好,吸引人,无他,情真意切故也。” 有时,信中也流露出感伤的情怀,如:1990年6月27日信中说:“最近一个时期,老想给你写信,上了年纪,容易怀旧;同时,故人凋零,生者也多在病痛之中(唐弢、沙汀均入院);人心不‘古’,真正的朋友越来越少,所以时常想念到你!同时,也忆往昔。” 父亲写给臧伯伯的信,因不在我们手中,所以无法引用。数量肯定也不少,但会比来信少一些。一个重要原因是,父亲晚年写字时手有些颤抖。对此,臧伯伯也很理解,还曾于1991年6月写一条幅:“一纸书来动我情,少年伴侣两衰翁。交深五纪如兄弟,入目心伤字失形。”后面又写:“得来书,述生平,诉苦情,手颤字为之失形,我心绪久久不宁,赋此以赠恭三老友(恭三是父亲的字)。” 我常去赵堂子胡同15号臧伯伯家。1995年7月初,父亲来电话说,最近臧伯伯身体不好,让我替他去看望看望。我去了。臧伯伯见了我很高兴,他说主要是心脏房颤,血压不稳,但不至有什么大问题。他说:现在身体最怕两条,一怕激动,二怕伤心,听说有的老朋友去世,不免伤心。他引了宋代陈与义的一首《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尽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他特别把“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用笔圈起来,前后各画“!”号,反复念诵着“此身虽在堪惊”。 说起给父亲写信,他幽默地比喻说:“我和他好像谈恋爱,我追求他追得多,他追我追得少。”直到我和他握手告别时,他又把这话重复了一遍。我替父亲解释说,他写字手发抖,所以不常写信,不像臧伯伯一挥而就。(其实臧伯伯并非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我把他的比喻告诉父亲,父亲笑了,也幽默地说:“我写一封等于他写十封。” 一段文坛佳话 二位老友,不论谁发表、出版了什么著作,都要互赠互贺,互读互评。《文史哲》杂志1982年第一期刊登了父亲的文章《再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对否认岳飞为《满江红》作者的论点进行了辩驳。臧伯伯看后,很赞成这观点,但他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解释有不同意见。对此句,过去一般的解释为岳飞对功名的鄙视,把它视如尘土。父亲也沿袭了这种解释。臧伯伯则认为“尘与土———风尘奔波之谓,非视功名如尘土也。”“‘三十功名’是纵写,‘八千里路’是横写也。”父亲很快回信说:“你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解释,确实是至当不易之论。是你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得来,不但发前人之所未发,也将是后来人所无法摇撼的。” 不久,《文史哲》又发表了二人的上述通信。臧伯伯读后给父亲写信说:“今上午收到《文史哲》,我们辨难的信,一气读了两遍,快慰心情,不待言了。 “我们的信中,充满了激情、真情与友情,也洋溢着为真理而探讨的精神。 “窃慕曹丕与吴质、元与白、李与杜,他们的‘书’意与诗情,使我觉得友谊之可贵;他们彼此关怀尊重之意气,动人。而今,同行相妒,派系成风,扬自己抑人,不顾事实,为此,心常常为之‘痛’,胸时时为之‘寒’。” 这可称为一段文坛佳话。 朗润园内时往还 那些年,父亲和季羡林同在北大,工作上、学术上的交往自然很多。他们又同住朗润园公寓,更便于时相往还。他俩常常在湖边相遇,坐在石凳上畅谈。每年春天,妹妹可蕴给父亲送去上等龙井茶,父亲都要分给季先生一两盒品尝。 1994年,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一书出版,父亲读后,立即写了一篇《向文科研究生推荐一本必读书》(发表于《光明日报》)说:读了这本书,“如获至宝一般”。文中对书作者的治学和为人都作了很高的评价。 90年代中,北大四院老同学编印了一本诗集《不褪色的青春》,我们几个发起人商量,最好能请季先生为诗集写“序”。当我去找他时,他正在楼前湖边散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问他:“需要多长时间?一个星期行吗?”他说:“灵感来了,很快就能写出来。”果然,不到一周,我就收到了一篇充满感情、文采斐然的“序”。这篇“序”真为诗集增色。 1994年10月11日,父亲和季羡林一同乘车到北京图书馆参加“臧克家文学创作生涯65年展览”,为诗人祝贺。在展前的会议中,三位老友并肩站在主席台上。摄影师的闪光灯一闪一闪,留下了这难忘的一刻。没想到,这竟是三位老友的最后一张合影了。 老友情深 1998年1月,父亲因病逝世,二位老友痛在心中,都写文章表达了深沉的思念与哀伤。次年3月6日,北大历史系、中古史研究中心、中国宋史研究会共同举办“邓广铭先生纪念会”,会上季羡林首先发言,心情沉痛地缅怀老友。(那天,我带了一本季羡林著的《牛棚杂忆》,请他给签个名。他在扉页上写了一首诗:“杨花飘零满春城,新荷尖尖水溶溶。世间多少伤心事,到处听人说牛棚。”)几天后,我去看望臧克家伯伯。他正因病卧 床,听说我去了,他让保姆搀扶着来到客厅。虽然重病在身,他仍像往常一样滔滔不绝地和我谈。他说,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简直承受不了。当纪念父亲的文集出版后,他看到扉页上父亲的照片就难过得受不了,让家人赶快收到书柜里。 谈起往事,他越说越兴奋。我和郑曼阿姨怕他太累,就劝他回卧室休息了。 没想到,2004年2月,臧伯伯也离开了我们。在悼念他时,我又想起老人们七十多年来“老而弥笃”的友情,正如他在信中所说:“似此情况者,试看天下有几人?” 如今,季先生也住在医院养病,我谨在此祝愿他尽快康复。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2月15日第七版)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