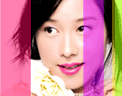雪与快乐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16日03:46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
|
每一朵雪花,其实都是洁白的蝴蝶,从那么高的空中飞下来,好像除了它们身上的那种白是正宗的,别的白,都有假冒的可能。对一朵雪花来说,我最想给它念的,是瑞典大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一句诗:“冰雪闪耀,负担减轻———一公斤只有七两。”想想那个银装素裹的世界,一切都在减轻,比轻还轻,像叹息,一声两声三声……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先生的这首诗特 有意境:烧个小炭炉子(请注意,炉子是用红泥攒的),上面温着酒,天色已晚,欲雪,此时最渴望的就是与知己对饮了,呵呵,太小资了。现代小资如果下雪天喝酒,估计不会围着红泥小火炉,最有可能一拨儿哥儿们姐儿们开会一般,在火锅边坐成一团涮羊肉。最不济也要找上二三知交去水煮那个鱼。醉眼迷蒙地看着雪,在窗子外面,飘啊飘的,像被谁撕碎的一封信———有可能是一封情书———会不会是上帝失恋了?如果一场雪就算一封被撕得粉身碎骨的情书的话,那,上帝也够累的。这却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上帝和我们一样,亦有七情六欲:会流泪———那是雨水;会悲伤———那是乌云;会发怒———那是雷霆;会痛哭———那是狂风;会发火———那是闪电;会失恋———比如外面这场正被越撕越碎的“雪花情书”。童年的种种快乐,堆雪人算一个。你简直不能想象一场雪怎么会给一个孩子带来那么大的快乐。一朵又一朵雪花,只要一落到地面,就会团结在一起。雪人可由你任意地堆,堆的过程中,你感到雪的无限可能。给一个雪人戴上草帽,再找几粒黑黑的钮扣做她的眼睛,我认为最有意思的,是拿两粒枣核般干硬的山羊粪球,做雪人之眸———那种一丝不苟的黑,在白雪的反衬下,甚至会黑出一种光芒。 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肯定会在不同的年龄段遇到不同的大雪,但,惟有童年的雪才叫雪,换句话就是,一场雪,只有下在童年,才叫真正的雪———那是纯洁与纯洁握手,无邪与无邪拥抱,天真与天真相逢。每一场童年的雪,都会像一笔存款,多年之后,你还会因为回忆而快乐———这是它的利息。现在,我还常常想到雪落屋顶的光景。那些雪,可以说是个头儿最小的白鸽子,一夜之间,把我家屋顶弄成白茫茫一片。远处,田野里、草垛、树梢,大毛家的牛棚、狗剩家的鸡圈,以及三丫家西厢房的房顶,都白得不能再白。太阳出来了,雪开始化,一滴滴水,顺着屋檐往下跳。到了夜晚,没来得及跳的水,就拥抱在一起,抱成了冰挂———水晶一般透明的冰挂,像萝卜,咬一口,凉、脆、爽……硌牙。 昨夜又下了一场雪,现在已是午后,阳光灿烂,尽管许多雪化了,但,还是有一些雪,不愿意撤退,正蹲在我的窗台上,伸手可及。看着这雪虽说也有快乐,可是,年龄一长,这雪带给我的快乐至少打了三折。既没有吃冰挂的心情,也没有堆雪人的雅兴。此刻坐在电脑前码字,这场雪还是撩拨了我,真想现在就出发,去滑雪———滑天下之大雪。这么多年来,每一场雪,其实还是童年的那种雪,只不过,我不再童年而已,怪不得雪。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应该像个孩子似地,去雪中重找儿时的快乐。或许,回到一场雪中,才有可能重新找回久违的童心。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童话般洁白的滑雪场里,我最想穿的,是一套红色的滑雪服,脚踩红色滑雪板,连袜子都是红的。像一团火焰,从雪野飘过,如果你把我当成火狐,我会更加乐不可支。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01月16日第七版)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6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