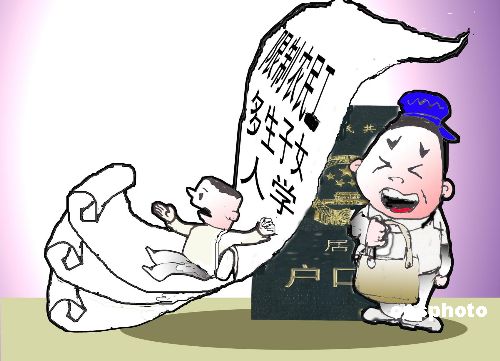|
|
|
公办学校瞧不起农民工子女 平等上学路在何方?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05日09:20 中国新闻网
漫画: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难中新社发 李忠 摄 版权声明:凡标注有“cnsphoto”字样的图片版权均属中国新闻网,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使用。 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话题。去年以来,一些城市纷纷对农民工子女敞开了公办学校的大门,但是,还是有很多农民工子女没有选择到公办学校就读。今天,本报与中青在线、新浪网联合邀请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代表、江西省赣州市滨江第二小学校长刘艳琼代表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二年级学生宋霞,一同探讨农民工子女就学之路到底在何方。 小平平破灭的公办学校梦 访谈一开始,宋霞同学就向两位代表讲了一个名叫平平的农民工子弟上学的故事。宋霞参加了学校的“农民之子”社团,这个成立了六七年的学生社团,一直坚持免费为农民工子女授课。 平平老家是河北,但从小在北京长大,目前正在北京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读五年级。妈妈和她都不喜欢这所学校:学校三天两头换老师,而且一个老师兼任好几门课程。平平和妈妈都很向往公办学校,但是家里无力承担这笔费用。 去年7月中旬,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各公办中小学要继续挖掘潜力,扩大招生规模,将在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就读的儿童少年分流到公办学校和已批准的民办学校就读。” 8月17日,宋霞第一次见到平平和她的妈妈。详细咨询了政府的政策和就读程序后,兴奋的平平妈妈第二天就来到附近一个公办学校询问情况。值班的老师回复,“你过几天再来吧。”不死心的平平妈妈第二天又来到这所学校,另一位值班老师告诉她:要办全“五证”,8月末再报名。 “8月末就一定能报名吗?”平平妈妈问。这位老师说,也不一定,到时候还要看接收的人数能不能容纳下,然后才能确定能不能报名。抱着一线希望的平平妈妈还是去办了“五证”。这五证办得并不容易:办房屋租赁证需要租赁合同,但是他们的房东没有正规的租赁合同。 在等待中,公办学校还是没有答复,平平妈妈也不知道孩子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是否在关闭范围内。 9月初,平平妈妈还是把学费交到原来的打工子弟学校。平平妈妈实在没有信心再等下去了。打工子弟学校已经开学了,如果再不交学费,平平会落课。 在宋霞和她同学们的调查中,这个区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在新政策出台后,能够进入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弟寥寥无几,更多的还是回到原来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有许多实际困难。比如说,办“五证”,有的打工子弟学校不愿意生源流失,不把这个信息告诉学生和家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办学校对接收农民工子弟入学这件事情,看起来不是非常热情。 公办学校瞧不起农民工子女? 有一年,在一所城市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所在当地还算有些名气的公办小学对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结果,家长们在校门口前抗议,理由是担心农民工子女成绩不好,会影响到自己的孩子。 在宋霞和同伴的调查中也有类似的例子:一些家长带上已办好的“五证”、借读证明及打工子弟学校的取缔告知书前往公办小学报名,却屡屡碰了软钉子。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公办学校在这件事情上很不痛快,是不是瞧不起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刘艳琼代表是江西赣州一所公办小学的校长。她所在的小学就有不少农民工子弟。“一方面在考虑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时候,大家也要反过来考虑公办学校在收这个孩子的时候,实际上有自己的困难。”她说。 第一个困难就是,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但是各个地方的义务教育学校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城市的生源也没有严重的萎缩,像赣州这样的中小城市也不是学校的人数越来越少。实际上,很多学校单单是接收城区管辖片内的学生就已经趋于饱和。 第二个困难就是老师,高校扩招后中小学的师资力量比以前有所增强,但是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宽裕。中小学本身也在扩张,老师的数量显得不够充足。 以赣州为例,打工子弟的聚集量没有大城市那么多,问题也相对简单一些。随着赣州这个城市的改造,城区南迁,赣州就把两所相对生源略少的公办学校就作为农民工子弟特例的学校,农民工子女可以很畅通地进入这两所学校。 大城市的问题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案。周洪宇代表曾经担任过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他说,武汉总人口870多万,流动人口的子女在16万左右。1998年以前,与全国其他省市一样,武汉的公办学校和教育部门基本没有考虑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最近几年,武汉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发生变化。武汉市李宪生市长有一句名言:与其将来去建一所监狱,不如现在多建几所学校。 周洪宇代表说,武汉是逐步打开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大门。一开始放开了100多所,到2003年左右,放开的学校达到300多所。当时,武汉的学校总数是1000多所。 公办学校当时不愿意无偿承担这个责任。周洪宇代表说,当时也有学校提出希望适当收取借读费,否则就要政府补贴。武汉市政府的态度很强硬,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不许公办学校收取农民工子女的借读费,如果不执行行政命令校长就要被撤职。 如今,武汉市基本达到这样一个状况:有农民工居住的地方,就会有一到两所公办学校向其开放。 不能仅靠政府的一句话 尽管武汉市农民工子女到公办学校读书的问题解决得不错,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农民工子女入学人数越来越多,行政命令不能解决最致命的问题:经费问题。没有充足的经费,师资、教学环境和办学设施的改善都会受到制约。这也是困扰很多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的问题。 刘艳琼代表深有感慨: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不是政府的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中间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落实。 “如果从全局来讲,农民工子女入学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部门认识上的不统一,执行部门具体操作的不统一,现有的政策法律不配套。”周洪宇代表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农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对农民工贡献的认识就不统一。很多流出地政府都有这样的看法:农民工到流入地做事,为当地创收,流入地有责任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而有的流入地政府的看法则完全不一样:农民工在流入地创造的税收很少,基本上等于农民工自己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消耗,这就等于他们对流入地基本没有创造什么税收。 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而言,流入地与流出地就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流入地主要承担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周洪宇代表建议,考虑权利与义务平等的原则,流出地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你是国家级贫困地区拿到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资金时要转到流入地。简单地说,就是如果流出地政府拿到一个学生500元的补助,就不能扣住这500块钱,应该相应转到流入地。 周洪宇代表说,现在有这样一个情况特别值得注意:极个别流出地的县政府,不但不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钱转过去,甚至还要收流出地的学生的学籍贷款费。他说你高中还要到我这儿考,你的学籍还在我这儿,我不怕你不回来。按照现行的教育体制,高中阶段没有放开,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结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后,必须回到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流出地收费的想法很简单:你在城市读书,已经接受了比你在同等城市下同时间学校的更高教育质量的教育,你回来考试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会增加这个地方的升学压力。 政府承担适龄儿童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义务,需要统一认识,层层落实责任。比如说,政府的服务意识,群众意识的建立。周洪宇代表建议,政府首先要对整个城市教育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一个最切实可行的事情就是把城市适龄儿童,也包括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状况一起作规划。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流动人口子女信息的监测体系。农民工本身处在一个流动的状态,或者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或者从一个城区流动到另一个城区,如果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政府清楚农民工的流动状态,也就清楚了农民工子女的状况。其次,对所有规划一定要有经费预算,把农民工子女的费用也一并算在内,并对市本级财政和区一级的财政有一个合理的分担。 宋霞同学有一个疑问:什么时候,整个城市才会真正把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放在一个城市建设者的平等的地位来看? 周洪宇代表说,这不可能一步到位。从实际而言,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尽量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这个教育质量与城市孩子相比,可能要低一些,但是会高于他在家乡所接受的教育。“改革是循序渐进的,所有的改革包括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都要兼顾各方,要考虑改革的目标,更要考虑改革的承受力。”(原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