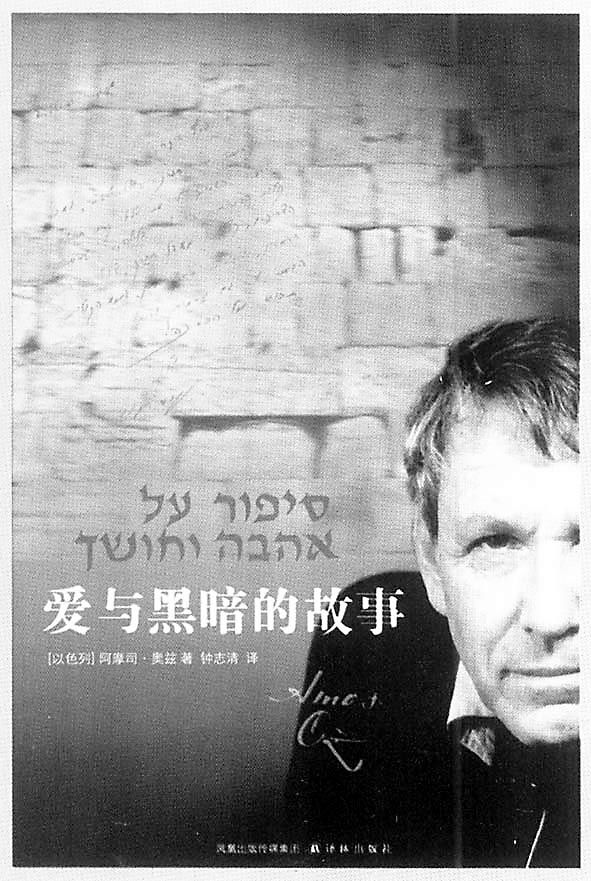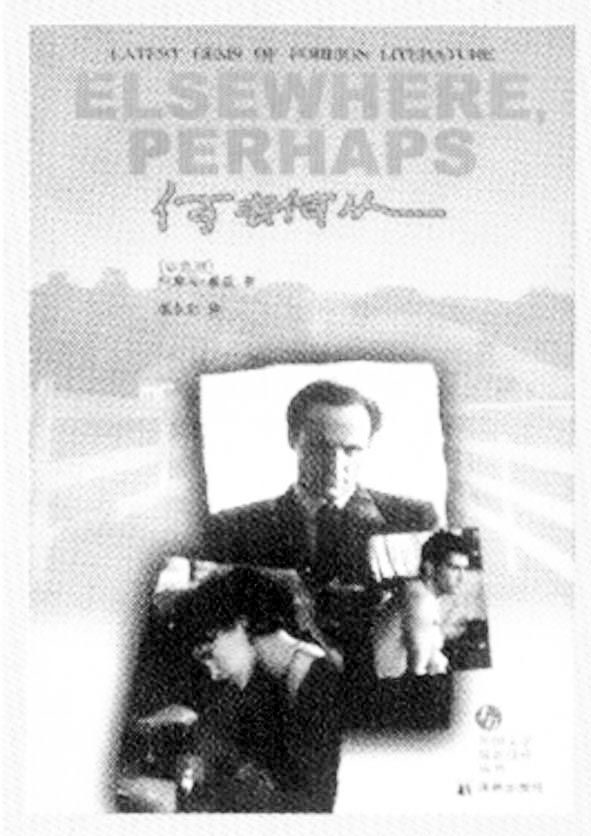|
|
|
世界上的事并非全部黑白分明———奥兹与莫言对话录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07日00:20 正义网-检察日报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邀请,当代以色列杰出作家阿摩司·奥兹于8月26日至9月9日访问中国。8月31日,奥兹在国子监街留贤馆会晤了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 把长辈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写 奥兹:读了您的《天堂蒜薹之歌》后,我仿佛真的到了中国农村,到那里生活。 莫言:一个人不可能去许多地方,但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却可以到达世界每个角落。我尽管没有去过以色列,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但是读过您的作品之后,我仿佛成了一个土生土长的耶路撒冷人。 奥兹:您在从事创作的时候一定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 莫言:我做了一些关于地方历史的调查工作。研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阅读关于地方历史的书籍,另一部分就是倾听老人们的口头讲述。我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老人们口头传说的历史故事更有意义。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您讲述了祖父、祖母家族在敖德萨的故事,讲述了外祖父、外祖母一家在波兰的故事。这些遥远的故事和资料我想您也是通过老人们的口头讲述而获得的。 奥兹:我二人拥有一个共同之处:把死者请到家中,来理解他们。 莫言:您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您说自己在作品中写到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等长辈时,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写。小说中描写长辈青年时期的生活,他们那时的年龄,比我们现在的年龄小。把自己的长辈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写,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年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一个艺术问题,一个道德问题,这对于作家是很有意义的。 奥兹:我在读《红高粱家族》时,也意识到,您在写“我爷爷”、“我奶奶”、“我爹”等几代人的时候也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写。 莫言:有时我把他们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但我更多的时候是把他们当成我自己来写。 奥兹:读了您的两部作品之后,确实感到老一代人已经复活了。 莫言:是用文学的方式使他们复活。从作家个人的体验来说,他们既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又是我们自己;但是从文学角度来说,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艺术中的典型。 奥兹:我特别欣赏您笔下的自然风光、农村风情,令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莫言:因为我从小在那片土地上出生长大,对那个地方的一草一木都有一种很深厚的感情。其实,我从来没有有意识地进行风景描写,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纯粹的风景描写是不应该存在的。 奥兹:对此我非常赞同。 莫言:小说里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景物描写应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读过您的许多作品后,我逐渐感觉到,耶路撒冷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耶路撒冷是个有生命有情感的人物,耶路撒冷的每座建筑物就像人的一个器官,每一条街道就像人的一根血管。所以整体上说她是有生命的。 我只能写过去的战争 莫言:我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看到你们一家人穿过整个耶路撒冷前去看望你的伯祖父约瑟夫·克劳斯纳,整个过程像一个非常长的电影镜头,我在阅读时的真正感受是跟随在你们一家人的背后走过了整个旅程。 奥兹:谢谢您恰到好处的描述。我在读您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时也产生了类似的感受,当时我正坐在书房里,我仿佛亲自来到了你笔下的小村庄,闻到了那个村庄的气味,目睹了那个村庄的风情。我的书房里仿佛飘起了蒜香。 莫言:在《爱与黑暗的故事》接近结尾之处,您描写了母亲两次雨中漫步。这也是非常优美的电影长镜头。这段景物描写与前面一家人前去探访亲友时的情感氛围截然不同,前者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后者充满了沉重忧郁的气氛。 奥兹:您非常敏感,细腻。我在创作《爱与黑暗的故事》时有一种感觉,就像在创作音乐乐章,有时是合奏,有时是双人演奏,有时是独奏。 莫言:对,而且里面有高潮。中间的一个高潮就是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公布阿以分治协议表决结果前的那个夜晚。几乎耶路撒冷的所有犹太人都走上了街头,仿佛一个乐队的全部乐器同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 奥兹:这一场景并非我想象,而是确有其事。尽管过去了六十年,那一切依然在脑海里历历在目。在以色列的一家读者俱乐部,我曾经向大家读过这段文字,许多人热泪盈眶。而在读您的《天堂蒜薹之歌》时,有时也让我感动得落泪。当农民们在店铺前排起长队,等待店铺收蒜,而忽然得知店铺关门的消息失望至极时,我不禁百感交集。 莫言:从小说创作的意义上说,我从您这本书里学到了很多。我在写《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时,以及我以前的一些创作中,描写了悲剧和战争,不过,我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剑拔弩张,慷慨激昂。您在创作时也处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采用的则是一种非常宽容舒缓的笔调,我觉得您这种手法比我要高明,所以我说您是我的老师。 奥兹:我们都从对方那里学到了东西。我们的创作技巧不尽相同,但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我的创作手法就比您的高明。我在阅读您的作品时,有一点感触很深,即使您在描写特别残酷、特别血淋淋的场景时,依然透露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把怜悯与残酷结合在一起的描写手法,从创作角度来说,也是很高明的。 莫言:既要描写残酷场景,揭示人物的悲惨命运,又要充满悲悯的情怀,把握这个分寸很难。 奥兹:我们都曾经是军人,但是时至今日,我从来也没有一部作品描写战争,描写军旅生涯。而您却成功地描写了军旅生活,这一点确实令人羡慕。 莫言:实际上我也没有描写自己的军营生活。我从军22年,但在军队里主要从事文职工作。我没有上过战场,我打靶时从来没有打中过靶子,投弹时却击落过班长的门牙。我不是个好兵,所以我写战争,只能写过去的战争,写想象中的战争。 奥兹:我虽然上过战场,但是我从来写不出战争。我也不是个好兵。在战场上诚惶诚恐。 莫言:我想,很难将一个作家同一个好兵联系在一起。托尔斯泰尽管写了《战争与和平》,可他要是当兵也不会是个好兵。威廉·福克纳也不是个好兵。海明威是不是个好兵我不知道,估计也不会是个好兵。 奥兹:区别就是他们目睹了战事。 我不能用某种黑白分明的方式来描写阿以关系 莫言:尽管我不是一个好兵,但我对中东战争颇为关注。我没有去过以色列,也没有去过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但是感情上却站在阿拉伯一边。仔细想想可能和中国当时的宣传有关。当时我们认为中国、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当时即便一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人,在思想感情上也是天然地偏向阿拉伯一方。 到80年代中期,我听一个中东问题专家讲了两堂课,改变了我的观点。这个专家讲述了犹太人数千年来的悲惨遭遇。他们数千年来流亡异乡,没有安身立命之处。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屠杀他们,斯大林也屠杀他们,因此他们逃往当时的巴勒斯坦这小片土地上。我想犹太人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希望有自己的祖国,是非常正义和正当的要求。奥兹先生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关于联合国表决之夜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描写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在于写出了历史的真实和犹太人的真实心境。 但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阿拉伯国家也很有道理。去年我看到一个电视场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时,轰炸刚刚结束,一个满身尘土的阿拉伯老太太就搬着纸箱出来卖蔬菜。面对着摄影机镜头,阿拉伯老太太庄严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谁也不能把我们赶走。我们即便吃这里的沙土,也能活下去。 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都是受害者,都有自己正当的理由,难以简单作出究竟谁对谁错的判断。因此我尤为钦佩奥兹先生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描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时,能够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尤其是描写你跟随着红脸膛的格里塔大妈到服装店,掉进了贮藏室,是一个棕色脸膛的有两个大眼袋的阿拉伯大叔把你救了出来;你也描写了和阿拉伯小姑娘阿爱莎的交往。多年来您一直对他们念念不忘,担心着他们的命运,您发自内心地希望他们幸福。所以,从总体上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似乎是势不两立的,是仇人;但是具体到每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可以成为朋友。 我说这么多就是要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我特别敬佩奥兹先生不是站在犹太人立场上来进行民族主义的描写,而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站在了全人类的高度上,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关系进行了包容性的、人性化的描写。因此,我认为不仅犹太人要读一下奥兹先生这本书,阿拉伯人也要读,尤其是各个国家的政治家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 奥兹:非常感谢您刚才说过的话。我不能用某种黑白分明的方式来描写阿以关系,也希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要以某种黑白分明的方式来对待对方。每场悲剧基本上都是正确者与正确者之间的冲突。许多人把以色列当成第一世界,把阿拉伯国家当成第三世界,这种观点有偏颇之处。称其偏颇,主要是因为居住在以色列的许多犹太人以前都曾经是被逐出欧洲的难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列也应该属于第三世界。 莫言:您的作品没有特别描写政治,但处处充满了政治;没有刻意直面描写宗教,但却处处洋溢着宗教气氛。这也是一种以小见大的艺术表现方式。就像少年奥兹和阿爱莎一样,虽然说的是两个小孩子的小故事,但却表现出一种广大的背景。阿爱莎背后站的是阿拉伯民族,奥兹后面站的是犹太民族。历史、现实、友谊、仇恨、理解、误解、痛苦、负疚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我认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能用一个很小的细节,表现出非常重大的问题。 奥兹:谢谢。我相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将来能够解决。希望巴勒斯坦建国,两个民族在一片土地上和平共处。 莫言: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就像中国一则童话中描写的两只黑山羊,试图跨越一个山涧。山涧上横着一座独木桥,两只羊就站在独木桥之间,顶住了,谁也不肯退后一步。 奥兹:二者都可以跨过山涧,但不能同时通过。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一种妥协,但是狂热主义者们总是想把这种冲突转化为宗教战争。其实,应该把这片领土一分为二,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有自己的居住地。 莫言:这种理想的模式听来简单,但要执行起来就困难了。 奥兹:我想给您讲一个故事。三年前,一个名叫乔治·胡里的阿拉伯小伙子在耶路撒冷郊外开车,被恐怖分子当成犹太人,头上中弹身亡。小伙子的父母在他死后,决定出资把《爱与黑暗的故事》翻译成阿拉伯文,以纪念他们被恐怖分子杀害的儿子。小说的阿拉伯文版献词上会写道:“谨以此书纪念乔治·胡里,一个阿拉伯年轻人,被阿拉伯恐怖分子当成犹太人而遭到误杀。希望以此增进阿以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 莫言:可见在阿拉伯世界里,也有很多理智的人。但这理智,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换取。您的小说中描写过类似的故事。我感觉《爱与黑暗的故事》的任何一个译本,都不如阿拉伯文译本重要。 奥兹:我非常赞同。某和平运动机构的主席决定购买1800册阿拉伯文《爱与黑暗的故事》,捐给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读者。希望以这种方式增进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 莫言:相信它会发挥很好的作用。因为文学所起的作用不是强制的,但一旦发挥作用,就是持久的。 奥兹:我非常喜欢和您之间的这场谈话,分分秒秒都令我感到愉悦。等您有机会来以色列,欢迎您到我家里做客。 莫言:好,请您一定要把我带到您生活过的基布兹看看,我在您的小说《何去何从》、《沙海无澜》中已经很熟悉这个地方。尽管我不是一个好兵,但从事农业生产,也许勉强及格。 翻译整理/钟志清 摄影/郑键 阿摩司·奥兹作品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既述说了一个不幸家庭的故事,又讲述了一个民族诞生的历史。
《何去何从》的故事发生在靠近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一个基布兹农庄里。主人公在爱、恨及冲突矛盾中难以取舍。在他觉得自己已被生活、婚姻所禁锢时,他遇到了渴求爱情的她。
《沙海无澜》展示个人与社会问题、男女关系、对以往社会价值观的留恋和在变化无常现实中的挣扎。 钟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