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完酒离去朋友醉死,谁有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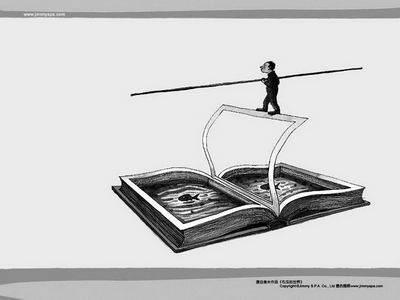 |
几迷 漫画
记者 徐林武
通讯员 李克梅 赖华平
两人相约到酒吧喝酒,一人醉酒后另一人离去,结果醉酒者猝死,离去的同伴是否有扶助义务?朋友相约出海钓鱼,开车走高速发生车祸驾车者死亡,同伴是否有提醒义务? 前天下午,思明区法院学术报告厅济济一堂,这些思明区法院审判过的案例引发了道德与法律、同舟共济与自担风险的理论探讨,思想火花在第二期“思法论坛”上再次擦亮。
前天下午,全国法理界的“大腕”张文显、葛洪义、宋方青等出席第二期“思法论坛”,与实务界的法官们、法学理论点的博士们一起探讨“生活中的法和案件中的理”。
思明区法院洪志坚院长介绍说,“思法论坛”由思明区法院和厦门大学法学理论博士点联手打造,是目前全国首个由法院和法学院联合开办的法律论坛,2009年4月份首度开讲。
全国法理学泰斗级人物——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文显再次肯定“思法论坛”以案说法的方式非常好,思明区法院选择的案件很有代表性,探讨侵权责任领域中有待完善的注意义务问题,具有前沿性。张文显透露说,目前进入第三稿审议阶段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已经就注意义务作出规定。
论坛同时也吸引了上级法院的关注,厦门市中级法院副院长黄小民、厦门市中级法院研究室主任张如曦、厦门市中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刘友国等出席论坛。共青团思明区委副书记王一青率思明区“青年学习沙龙”成员也应邀参加了论坛活动。
举 案
一起去玩 朋友意外死亡要负责
2004年10月2日凌晨,谢先生与朋友相约到酒吧喝酒,准备离开时,谢先生因饮酒过度摔倒在地,随后他提出留宿酒吧,朋友没说什么就离他而去。第二天上午,酒吧服务员发现谢先生醉酒后猝死。谢先生的家属随后将酒吧和朋友告上思明区法院,索赔损失。法院认为朋友的不作为与死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3%的赔偿责任。
2007年11月4日凌晨,郑先生与苏先生相约从厦门开车前往福州出海钓鱼,当晚两人开车从高速公路回厦门,苏先生开车,郑先生则在副驾驶座上睡觉休息。次日上午7时许,两人乘坐的轿车与重型车追尾,苏先生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定苏先生负事故全责。之后,苏先生的家属到思明区法院状告郑先生,提出索赔诉求。法院认为郑先生没有尽到提醒义务,应承担15%赔偿责任。
两起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均服一审判决,没有提出上诉。
民 议
多数市民认同合理分摊责任
就这类案件的责任分担问题,昨天下午,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
“朋友醉了怎么能一走了之?这也太不够意思了,怎么也要送他回去,至少也要跟他的家人打个电话。”小许觉得谢先生的朋友做人太差。但她认为真要从法律责任上说,似乎也于法无据。不然以后谁也不敢跟朋友一起出去喝酒了。
对于第二起案例,市民宁先生说:“一人做事一人当,都是成年人,有没有疲劳驾驶自己应当知道,但如果死掉的那个人是酒后驾车,同伴明明知道他酒后开车而没劝阻,这时候出了事就有责任了。”
“我认为出了事同伴得承担一定的责任。”市民陈先生说,喝酒时劝酒是常有的事,自己喝醉的很少,大多是被灌醉的,把人家灌醉还一走了之,这当然要承担责任。如果法律确认同伴有责任,对形成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本身也是有益的。
虽然市民们意见不一,但是对法院的判决大多能够接受,因为法院认定同伴负有责任,然而并非全责,而是在一定范围限度内的责任。
辩 法
同舟共济应上升为法律义务
宋尧玺博士用社群主义理论解读说,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不可能脱离群体而获得正常生存,在这个群体中,每个成员共享共同利益,相应也应当共同承担风险。
他引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说,法律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和纽带,法律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团结共存,从而提升社会的公共道德伦理与积极互助、同舟共济的公民意识。因此,无论是情理上还是法律上,同舟都必须共济。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胡成蹊博士一开场就朗诵起李白的《将进酒》,他说在古代社会,友人间对酒当歌发生意外,或许一哭一碑一祭文也就罢了。然而在基本人权被空前尊重的现代社会,这样的问题值得上升到法律层面探讨。
胡博士解析说,相约出游意味着同伴们面临着共同风险,在这些风险面前,同伴们的生命健康等权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体的而非完全独立的。提醒注意义务基于人类最基本的自然目的和自然事实而产生,属于“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的规则,所以它应当得到法律强制力的保护。
自担风险是理性人的责任原则
朱志昊博士用“我的青春我做主”概括他的观点。他认为具有理性能力的人必须自我选择、自我决定、自我发展,并最终对自我事务负责。法律规定年满十八岁、身心健全的成年人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因此,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要承担因自己行为而造成的任何后果,这本身就是对作为理性主体的人的尊重。法律不是万能的,生活有自身标准。友情、相互扶助等都是生活的概念,它们本身所具有含混不清的性质是法律无能为力的。因此,法律就应当在此止步,让日常生活准则来处理。
“前面是红灯要小心,方向盘打直,赶快靠边,提起精神……副驾驶座的乘客确实尽到了注意义务,一直提醒,但是我想司机一定会感觉受到干扰,甚至火大,结果本来没事都会弄出事来。”来自宝岛台湾的董瑞国博士出言惹得听众会心一笑。
董博士发言的题目是“死者虽不幸,生者尤其苦”,他认为注意义务难以界定,一旦强行规定,会加重注意义务方的负担,从而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反应。董博士以台湾“邱小妹妹人球案”为例,指出因为台湾地区的医院责任条款规定过重,造成各家医院害怕承担责任而拒绝收治受伤小朋友。因此,“注意义务”不需上升为法律规范。
道德于司法者而言不仅仅是资料
郑金雄博士同时也是厦门市中级法院的法官。他说,现实中,法律有时是默不作声、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的,这种含糊不清派生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就是法律和道德发生联系的场合。思明区法院的两个判决确认同伴负有注意义务,在一定程度符合了共同体的道德情感要求。
他赞成“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也应进行处罚”。他说,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主观上应该知道司机酒驾是违法行为,乘客看到违法行为可能引起社会危害,应该进行劝说、制止。同车乘客如果默认、放任这种潜在的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发生,这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义务的问题。法律不能防止人们不出任何偏差,却能够阻止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最轻微的责任也能够给社会以某种有用的警告,使其意识到自己的不行为所带来危险。
另一位法官李缘缘则梳理了现行法律及法典草案中有关注意义务的条款,认为注意义务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系统化的规定,而且除了上述注意义务,法律对于其他活动中“同伴”间产生的关系就没有再做规定了。
法官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借助法政策、道德准则、交易惯例、以及对公平正义的考量,来决定同伴注意义务的有无。
【点睛】
 |
◆“法律无权宣布什么是道德,只能判断哪一种情况合法,哪一种情况违法,诠释道德有很大的风险。”
——葛洪义(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葛洪义说,这两起案件的审判说明思明区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重视法律方法,道德与审判本身就不能牵扯,因为法律无权宣布什么是道德,只能判断哪一种情况合法,哪一种情况违法,诠释道德有很大的风险。
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是否产生注意义务?法官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转换成其他语境来处理。很多情况都是利益在起作用,道德在多数情况下只是提供一个理由,掩盖不想说的东西,因此不要笼统地说道德。
 |
◆“一言以蔽之,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宋方青(厦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宋方青说,很多道德的义务已经转化为法律义务,这点在我们民法通则里关于法律原则的规定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上有密切联系,在概念上没有关系,一言以蔽之,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怎么办?从法律渊源方面考量,应当从道德规则中寻找法律渊源,以此为依据转化为法律原则,进而做出司法判决。
 |
◆“当同伴无法证明尽到第一性注意义务时,就应当承担第二性的侵权责任。”
——张文显(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张文显说,法律上有第一性义务与第二性义务,《侵权责任法》草案已经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当同伴无法证明尽到第一性注意义务时,就应当承担第二性的侵权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