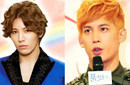留守农村的46年(图)
1974年,戈卫(左二)和父亲戈治理(右四)和公社社员合影
10月19日,在码头村村委会的宿舍里,戈卫站在刻意铺的碎花地毯上 本报记者 张宏伟 摄
建于1969年,戈卫曾经住的“知青”房,4年前才拆除(资料图片)10月28日注定是戈卫人生中重要的节点。
1966年10月28日,21岁的西安青年戈卫来到宝鸡西部山区码头村,开始了他的知青生涯;1975年10月28日,他和另外11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一起,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46载蹉跎岁月过后,当年一同向毛主席表决心的大多数都已返城,而花甲之年的戈卫始终留在码头村。“叶落归根?我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在这里,这里就是我的根。”65岁的戈卫说,他扎根农村,并不是要把自己变成普通农民,“我在农民中生活,更知道农民需要什么。”
人物语录:
谈下乡——
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所展示西汉时期的生产工具相比,码头村当年就是多了个架子车,而且一个生产队只有两辆。
谈返城——
我所受的是传统教育,讲奉献、讲社会责任,还有理想主义色彩,我之所以能留下来,是来了之后看到中国很落后,农民的生活很艰难。
谈农村——
中国不能搞土地私有化,很多农民会出卖土地应急,失去生活保障,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没有涵盖到这些人,以后他们的生活怎么办?
谈幸福——
什么是幸福?能做想做的事就是幸福,如果连想做的事都做不到,能说是幸福吗?
出西安市向西,沿西安至天水的高速公路行驶约200公里,驶过宝鸡市从坪头出口下高速,拐上310国道继续向西2公里,再右拐进一条乡村公路,过了横架在陇海铁路的小桥,再经过一个天主教堂,就到了码头村村委会。
65岁的戈卫打开房门,穿着红色衬衣的他更像一位退休干部。寒暄两句后,他弯腰递过来一双拖鞋,然后转身走到卧室门口,脱鞋,走进铺着碎花地毯的卧室。
当农村城镇化潮流带着农民涌进城的时候,戈卫却依旧住在山村。
文革初期,出身于三代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的戈卫,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来到陕西省宝鸡县坪头公社码头大队,从此成为家族中惟一的一个农民。
这一去就是46年。
>>废除高考 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戈卫,1947年7月出生于西安。父亲戈治理是原西安医学院教授,也是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者之一,母亲李维清曾担任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专家。父辈10个兄弟姐妹中,有9个受过高等教育,叔父戈治均从西安交通大学水利系毕业后,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改行做了演员,曾获得2001年度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此时的戈卫是陕西师范大学附中应届毕业生,正准备参加高考。
6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遭废除。戈卫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转折。
按照通知要求,“凡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尚未结束的,可以由学校妥善安排时间和住地,继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在本校文化革命运动已结束,而高等学校尚未招生时,可以由学校组织他们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
戈卫至今记得第一次离家时的情景:西安火车站到处红旗飘扬,南来北往的学生涌进站台,挤进各式各样的车皮车厢里。他下午终于登上西行的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天亮时才到达宝鸡。就这样,他从四川到贵州,又经云南终于到达北京。
当时,戈卫的父母不但没有反对儿子参加大串联,还为戈卫带了200元路费。在那个工人月工资不到20元的年代,元钱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当戈卫走完大半个中国回家时,口袋里还剩100多元。
>>“留下来养好猪”
“我的家庭都是知识分子,起初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体力劳动者。”戈卫说,刚下乡并没有长期打算,后来慢慢建立了感情,觉得自己有责任留下来做点事,改变贫困的状态和面貌。
1968年10月27日,戈卫和同伴们离开西安,先坐火车到达坪头,在小车站停了半夜,天亮后步行穿过两个隧道,然后坐木船渡过渭河,对岸已有码头大队的社员迎接。分配到码头大队的共27人,戈卫等5男4女被分配到第三生产队,包括小他4岁的弟弟戈健,还有曾是他妻子的一位女知青。
码头大队条件极为落后,戈卫到达最初一年还没有通电。用戈卫的话说,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所展示西汉时期的生产工具相比,码头村当年就多了个架子车,而且一个生产队只有两辆。那时根本没有农闲季节,地里没活的时候,生产队就发动社员进山开荒。那时地里种的只有小麦和玉米,社员辛苦干一年下来,连基本口粮都拿不回来。
好在知青点9个人都来自知识分子或者干部家庭,家里不缺粮食也不缺钱,分的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就从家里带粮票去镇上粮店买。
1969年秋季开始,知青陆续被招工回城。到1971年初,码头大队知青点的27名知青只剩下戈卫一人。
对于当初自愿留在码头大队,戈卫否认有任何个人功利主义目的,他强调自己1970年就给公社写信表明不打算回城。而他入党则是在1974年,之前连共青团员都不是。“不是别人把我逼上去,我也并不是学毛选积极分子”。
戈卫解释自己留在农村的初衷是:“我所受的是传统教育,讲奉献、讲社会责任,还有理想主义色彩,我之所以留下来,就是来了之后,才真正看到中国很落后,农民的生活很艰难。”
记者查阅有关报道发现,戈卫在1975年4月召开的宝鸡县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这样表述自己当时的最终抉择的:“考虑到自己下乡才一年,对农村情况才入门,和贫下中农的感情刚融洽,确实留恋不舍。当时我正在大队养猪场劳动,和社员一起试制黑曲霉醣化饲料。我想我自己走了,(这件事)当然还会有别人来干。可又一想,这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关于‘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指示的大问题,要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留下来养好猪正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具体行动……”之后的40多年里,戈卫一直住在知青点的老房子里,直到四年前被拆除。这个老房子一度被网友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知青点”。
>>改变山区面貌 不只是豪言壮语
10月19日,在码头村村口,70岁的村民王宝旭谈及戈卫时说:“他把机会错过了,有一年省上让他去当团委书记,他没有去,要不现在也当了大官。”
王宝旭说戈卫“犟”,而码头村支书魏文杰则说戈卫“执著”。魏文杰在大跃进时曾在城里做过几年工人。戈卫下乡的46年中,两人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至今戈卫吃住在魏家,连工资卡也由魏文杰保管,戈卫出门从不带钱。
戈卫坦承,早年间组织部门曾经找他谈话,准备提议他担任宝鸡市团委书记,但被他婉言谢绝。
戈卫曾经的仕途最高官位是乡党委副书记,那是1986年。而在他曾经“大红大紫”的文革时期,他的最高职务仅仅是码头大队的支部书记。
戈卫说,当初他留下来时,码头大队广种薄收,到处挖地,牛上不去的地方,人都去开荒。
戈卫认为,改变低产面貌的途径首先是在粮食品种上下工夫。1971年,他从河南博爱农场和西北农学院引进良种。1972年,他又主持繁育了“陕玉六六一”、“晋杂五号”。上世纪80年代初,在粮食生产面积因为发展林果而减少到1600亩的情况下,总产一举突破百万斤大关。
“当年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那封信,我不光是豪言壮语,我确实这样做了,从当年粮食总产30多万斤提高到110万斤,我落实了。”戈卫至今仍感到欣慰和自豪。
他所提及的那封信,就是1975年在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与天津邢燕子等12名知识青年代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来邢燕子一度担任了天津市委书记,而戈卫始终在农村基层担任大队支书,直到1986年,才被提拔为乡党委副书记。
魏文杰说,码头大队文革期间曾经也曾出一个高中毕业生,但很快当了教师脱了“农”,包产到户前10年,戈卫是大队学历最高的社员。也因为有戈卫这样有文化的知青,当年码头大队建水电站、科学养猪和杂交玉米推广总是走在别的大队前面。
>>不提倡年轻人留在农村
对于仕途,戈卫并不愿多提,但他仍强调说,即使担任乡党委副书记时期,仍旧没有离开码头村,至今户口依然在码头村。但当谈论起“三农”话题时,他的话匣子打开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像普通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戈卫说,中国有8亿农民,不缺我这一个,缺的是对农民有责任感、对农村事业有推动的人。
对于近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有关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戈卫表达了作为基层“农民”独到的见解:土地私有化?中国不能搞土地私有化,很多农民会出卖自己的土地应急,从而会失去生活保障,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没有涵盖到这些人,以后他们的生活怎么办?
戈卫认为,在很多国家,土地是作为纯粹的生产资料。而在我国,土地主要承担的是社会保障功能,其次才是生产资料功能。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现状是,即使有一半农民进城,还有一半农民在农村,农民在外打工,土地是最后的保险。
戈卫很推崇很多地方已开展的土地流转政策。他认为,在确定农民的承包权的物权之后,应当鼓励流动,让有条件放弃的部分农民的土地进入市场,通过有偿的流动,让他们逐渐脱离这样的社会保障,作为生产资料变为纯粹的生产要素。
戈卫认为,中国农村发展应注重三个方面:一个是要稳定;二是要改革开放;第三要教育,他引用毛泽东“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他解释说,当年毛泽东的说法着重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而目前所谓的“教育”就是技能教育、文化教育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没有科学文化,没有技能,你农民进城去干什么?真正要在城市扎根,不能仅仅是进城卖苦力!”戈卫说,我现在不提倡年轻人留在农村,我鼓励孩子们走出农村。
对于他之所以留下来,他的解释是,在他那个时代留下来有意义,那是自己选择的路,适合他。他希望成为中国农村的见证人。
戈卫:“能做想做的事就是幸福”
没有什么遗憾,我想做的都做了
记者:您如何看那场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
戈卫:总体来说,大多数知青是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想在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对这一代人来说,他们一下子深入到中国最基层,最了解中国,所以后来出现很优秀的人物。
记者:过去46年,农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戈卫:物质上比较丰富了,人的观念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农民思路更开阔。
记者:留在农村有什么遗憾吗?
戈卫:没有什么遗憾,我想做的都做了,一辈子一个人也不可能做太多事,当然是不是完全就达到理想或者愿望?可能是没有实现。
记者:您以前的愿望是什么?
戈卫:改变码头村的条件,而且要在社会或者经济发展中起到示范作用。但目前还远到不了我的理想状态。
记者:是不是当官,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想法?戈卫:性格决定命运吧。在政治上我没有那个野心,范围越小,越容易实现自己的想法。别人说如果去了更高的职位,就可能做出更大的事情,“可能”的事情终归不是现实。
要改变农村也包括生活习惯
记者:你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什么?
戈卫:善于思考,那年代提倡个人想大事,想国家大事。
记者:你觉得你的人生完善吗?
戈卫:我的个人生活还是很失败。我30岁才结婚,妻子当年也是这里的知青,后来那个家庭持续了不到10年,问题在于我没有想到回城。
记者:你会参加高中同学或者知青聚会吗?
戈卫:他们有过聚会,但我没参加,他们都成了爷爷奶奶,和我的想法有距离,没有共同话题。记者:你和村里其他农民的区别在哪里?
戈卫:我刻意铺地毯,以前在旧房子也铺,这是一个示范,要改变农村也包括生活习惯。
钱这东西,只要能保证基本生活就成
记者:套用央视记者的问题:“您幸福么?”
戈卫:我觉得很幸福吧。什么是幸福?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幸福,如果连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到,能说是幸福吗?
记者:您怎么看待金钱?
戈卫:我的钱都在老魏(村支书)那,我在他家吃饭不用花钱。钱这东西,只要能保证我的基本生活,不为生活发愁就成。
记者:您对家里老人也有责任感吗?
戈卫:确实有愧疚。我父亲90多岁身体不好,国庆节我回家就没有出门,基本就是陪老人。
(原标题:留守农村的46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