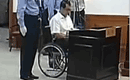字典里的邂逅
人们最早知道托尔金,并不是因为《哈比人》或者《指环王》,而是缘于《牛津英语词典》。
博德利安图书馆保存的活页笔记本上,有托尔金清晰整齐的字体——W词语可能被采用的定义,以及复杂的词源说明。这是一个有趣的字母,没有任何希腊语或拉丁语的衍生词以W开头,托尔金的工作,就是弄清楚这个“奇怪”的字母部落的一些难字——它们的定义、用法和词源。
那是1919年。与后来问世的两部魔幻作品截然不同,字典的编纂工作,容不得任何的天马行空,甚至有些乏味和枯燥。小说家孜孜以求的灵感无足轻重,除了学识才华,持久恒定的毅力、体力、精力才是关键。
幸好,托尔金很快就不再“咬文嚼字”,他带着由此获得的良好声誉开始学术和写作生涯。如若一直身陷其间,“哈比人”肯定没有机会从浩如烟海、错综复杂的“词汇森林”里现身。
人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这项工程,它绝非想象中那般简单。即便是内行——最初提出编纂建议的“语文学会”的学者,早期的主编们,承印字典的牛津大学出版社,还有众多参与工作的志愿者,都不曾料到它的繁复浩大、艰苦卓绝。他们原先估计,最多10年,字典就能面世。出版社据此签订了“误差巨大”的合同,总页数不超过7000页,预算成本9000英镑——其最终花费高达30万英镑。
1928年,《牛津英语词典》(简称OED)完工时,距离起点(1860年5月12日)已有68年零三个星期。从编纂方案的确定,到排印好的清印送至主编默里手里,就相隔了22年。“充满着犹豫不定,怒气爆发,恼人的争吵,放弃的威胁”,让词典工程一度摇摇欲坠。
其间,27岁的首任主编赫伯特(诗人柯勒律治的孙子,学识丰富却体质衰弱),在将词典样张送印时受冻感冒,不幸离世。继任者弗尼瓦尔除了热爱英语之外,还热衷于同漂亮女子做伴儿和水上赛艇运动。相比于细致严谨的词典编纂工作,他似乎更擅长后者。这位冲动任性的主编几乎让OED早夭,好在他最终找到了“把词典工程从悬崖边拉回来,并引向最后成功的人”——默里,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出身贫寒,靠自学跻身学术界,为词典工程奉献一生的默里,差点儿与OED失之交臂。编纂出版一部严谨权威的英语词典的愿望,让他披荆斩棘,在字纸堆里呕心沥血。默里要阅读志愿者提供的引语字条,逐字逐句琢磨它们,然后为一个词写下定义,总结它的用法,弄清它的词源……工作条件一度很糟糕,为了御寒,他和助手们不得不将脚埋进字条堆里取暖。引语条源源不断地寄来,足以将所有编纂者淹没。
差不多70年的艰苦劳作,迎来了OED的诞生。12册形如石碑的巨著,构成了当时世人所知的“英语整体”,“所有的词条都经过充分而适当的释义;每个词不同的拼法,过时的和正确可取的拼法都列举出来;词源学的发展都记录在案,各种规定、要求或建议的发音都加以注明。”
看一下这些数字,大约能窥见它的“非同寻常”——将近1.6万页,41万多词条,180多万条引语(从几千名志愿者所提供的500万条引语中挑选出来,它们表明每个词的意义,使用方法,出现方式和时间)。它不仅是主编们才华和毅力的见证,也是一项恢弘的“民众工程”——志愿者们成就了OED这部鸿篇巨制。
他们的名字,以特殊的小型字体排印在每册词典的卷首词之后。当我们翻阅一本词典之时,或许不曾想到那一个个字词背后,藏着怎样的人和事。
隐士霍尔,因学术之争身败名裂,隐居偏僻山村的茅屋里,悄无声息地为词典干活儿,寄来引语,校阅样张;杀人凶手迈纳,在精神病院里不知疲倦地为词典辛勤工作了20多年; 学徒工斯威特曼,17岁时到缮写室工作,“一辈子当词语的奴隶”,看着词典完工,又继续为增补卷工作……
在一本关于词典编纂技术的严肃著作中,英国传记作家西蒙·温切斯特看到了一个简短的小故事:一个深秋的下午,《牛津英语词典》的主编默里博士坐火车去会见一个名叫迈纳医生的神秘人物。他为词典提供了大量至关重要的引语,近20年来,双方书信不断,探讨英语词典编纂学中复杂而细致的问题,却从未谋面……
西蒙立刻被它所吸引,于是追根究底,写出了《教授与疯子》。原本是要讲迈纳医生辛酸而充满人情味儿的故事,却附带着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英语词典的编纂历程。这一“附带”随之又引出了一本真正的《牛津英语词典》史——《OED的故事》,既然原先的故事“只是历史的一个注脚,为什么不写历史本身呢?”
历史总是没完没了,词典的编纂也一样。严格意义上讲,OED一直处于未完成阶段,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它就要进行修订,补充进新的词汇。不然的话,托尔金教授发明的hobbit(哈比人)一词,也不会列身其间。
(原标题:字典里的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