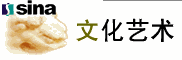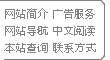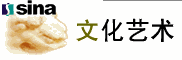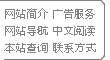张洁是一个善于在创作风格的不断突破与变化中,获
得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家。她早期的作品以表现纯情的女性
之爱和人间真善美见长,曾经轰动文坛的《爱,是不能忘
记的》和《祖母绿》,使她被评论界认为是一个崇尚爱情
至上的“痛苦思想主义者”,就书写情怀而言,我以为,
此时并不年轻的张洁仿佛处在“文学的少女时代”。以后,
她便逐渐走出了这种少女般的纯情与理想,可以作为女性
主义小说名篇的《方舟》,以及贴近改革现实的长篇力作
《沉重的翅膀》等,又使张洁成为新时期以来擅长以中性
和女性两种眼光,探索和表现风云变幻社会现实的重要作
家,从“文学年龄”来看,这个时期更像是张洁的“文学
成年阶段”。八十年代后期,以《他有什么病》为鲜明标
志,张洁的创作风格发生了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大幅
度陡转,《鱼饵》、《横过马路》、《只有一个太阳》等,
使曾经十分纯情又极其正统的张洁,变成了一个执著于内
心的宣泄,喜欢以变形的文学眼光和荒诞型式把握社会人
生的狂人式的女小说家,我曾把这个阶段看作是张洁创作
的“文学更年期”;进入九十年代后,张洁的这种女狂人
式的文学经营,因着母亲的溘然辞世而迅速消褪,《红蘑
菇》、《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等,越来越显露出她
观照女性人生时所持的无奈、悲哀与失望的情绪绝境,特
别是为母亲的去世所撰写的长篇纪实作品《世界上最疼我
的那个人去了》,标志着张洁的创作将由此而转入平实深
沉的人生反省阶段,从以往愤世嫉俗的入世,走向出世(
宿命与宗教),并且走向文学的唯美。
这样一个清晰的创作风格演变过程,恰恰体现在《张
洁文集》的精心编排中。有意思的是,四个卷本的书名均
是张洁不同类型的小说或散文(随笔)题目的“拼盘儿”,
比如《方舟日子只有一个太阳上火》,就是中篇小说《方
舟》、《日子》、《上火》和长篇小说《只有一个太阳》
的“拼盘儿”。由于这种独具特色的拼合,准确地把握并
强调了张洁不同“世界感”的变化,因而使这位作家(不
同于生理年龄的)从文学的“少女时代”——文学的“成
年阶段”——文学的“更年期”——文学的“老年时期”
的创作风貌,得以集中而全面地展示。
《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有勇气吗》,集中收录了张洁有
关理想主义与爱情的小说与散文,其中,无论是属于张洁
“文学少女时代”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未了录》,
还是她于“文学成年阶段”创作并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
沉重的翅膀》,以及与张洁个人爱情生活相关的散文如《
人家说我嫁了个特权》、《吾爱吾夫》等,都可以使我们
阅读到张洁特有的那份纯情与浪漫,挚爱与深沉,应该说,
这个卷本里的许多篇什都系结着张洁本人曾经“不能忘记
的”爱,可算作她的“爱之卷”。《方舟日子只有一个太
阳上火》则与这个“爱之卷”构成鲜明对比,收录的大都
是张洁进入“文学更年期”后的审丑之作,“上火”(泄
愤)之作。在其中的一个长篇、五个中篇和一个短篇中,
不仅能真切感受到张洁寓于《祖母绿》、《红蘑菇》中对
爱情的绝望与悲剧感,更能在另外的篇什中深切体会到她
面对人间假恶丑的怒不可遏。这时的张洁,显然已经跳出
了美的圈定,恶狠狠地为自己挑选了一副审丑的文学滤镜,
不遗余力地试图以恶作剧式的以毒攻毒,以恶抗恶——甚
至张牙舞爪,达成对残缺现实的批判,并且将(出现于这
个卷本的)几乎所有的男人,都置于她的审丑的滤镜下加
以无情的透视。《如果你娶了一个作家串行儿》可视为这
一“恶之卷”的姊妹卷,它集中收录了张洁以超现实主义
的笔墨创作的变形之作,以及她以轻松巧智之笔书写的随
笔与散文,这是最能展示张洁文学智慧的一卷,不仅提供
了张洁有资格作为一个幽默作家的范本,而且使人看到她
成为一个超现实小说家的全部可能性。《世界上最疼我的
那个人去了》可能是张洁最为珍惜的一个卷本。其中收入
了她几乎所有的与母亲相关的创作。我们从中读到了与母
亲结下生死之交和生死之恋的张洁,因着特殊的人生经历
而对母亲的“共生固恋”:当最深的爱恋——母爱,因着
母亲的辞世而永远地失去;当一生追寻的摆脱苦海的“方
舟”,因着母亲永远的离去再也无处找寻;当曾以为是“
不能忘记的”的爱情,因着母亲的痛失,而加重了它已经
被忘记的绝望与孤独;张洁郁结在内心的那许多许多恨怒
与厌恶均被丧母的巨痛吞噬了,这意味着她已经走到了自
己人生情感的极致大限。大限之后的情景犹如绚烂之极必
归于平淡,因而,这个卷本不仅仅是张洁用文字为母亲竖
起的一座纪念碑,也可当作标志张洁进入新的创作阶段的
里程碑吧。
在这个里程碑后(也就是在这套《张洁文集》之后),
张洁向人们奉献出的忏悔录式的长卷——《无字》,正是
她集聚于以上四个卷本中艺术能量的总爆发,从此,她的
创作又跃上一个值得探究的新高度。
就像这部长卷的题目那样,张洁以“无字”进入她“
文学老年时期”的创作,这或许意味着一种对于“大音希
声,大象无形”境界的思想与艺术拘执?
然而,这淡到极处的“无字”也是浓到极处的。这部
长卷完全可以看作是张洁多年思想和艺术积累的一次能量
的总爆发,也是张洁以纯然的写作、纯粹的文学方式对人
生的反省、忏悔和还债。从世纪初的东北老林到世纪末的
京华古都,从国民党张作霖、张学良将军的旧部,到共产
党内部的“抢救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及改革开放……
笔势之厉,使得世纪性的生命史诗不能不断裂成零碎的诗
语或警句,汇入小说背景。这部小说更以精致的散点透视
结构为骨架,以精美的诗语为血肉,使精细的情节故事和
精敏的思想参悟得以生动呈示,让人深感张洁在艺术上对
自己近乎苛求的精益求精。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如果作为
忏悔录来读的话,便应该是大忏悔,因为:在个人忏悔的
背景上,同时涂抹上的是浓重的历史无法偿还的欠债;如
果作为反省作品来读的话,那也一定是大反省——因为需
要反省的不仅仅是小说中为张洁代言的吴为,而是被政治、
历史、文化、命运所异化所限定的几代男人和女人,或者
说是存在于自身有限性中的叫作人类的大群;如果作为隐
私作品来读的话呢,自然也是一个大隐私——在作品中,
个人的隐私不过是从历史的隐私、文化的隐私、政治的隐
私、社会的隐私中甩出来的一种副产品罢了。可以说,正
是在这样的大忏悔、大反省、大隐私的观照之下,张洁才
可能那么小心翼翼地追求叙述态度的沉实、冷静与客观,
唯恐一不小心,自己笔锋的锐利会划破她以悲天悯人之心
书写的每一个人物。
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张洁留在字
里行间的与母亲共生的固恋,因而,大凡涉及吴为的母亲
叶莲子(秀春)或其母系的故事,便也是张洁这部小说最
精彩和动人的部分。这说明,张洁除了以“无字”来命名
这部专门“献给我的母亲张珊枝”的长卷,也确实没有再
好的题目来安置自己那一片曾经苦到极处、也爱到极处、
也悲到极处、也痛到极处的心了。这样,“无字”便有了
含不尽之意于言(字)外的寓旨。 王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