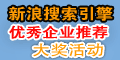| 记者涉险金三角 探秘“毒影第一现场”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22日06:52 新华网 | ||
|
毒品已成为世界头等公害。从毒品诞生之时,人类就与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1989年6月12日至26日,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了有138个国家和地区约3000多名代表参加的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部长级会议,提出了“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6月26日“国际禁毒日”由此诞生。记者进入“金三角”,对毒源地进行了一次零距离接触和调查。 提起金三角,人们就会想起罗星汉、昆沙,漫山遍野的罂粟花、海洛因、丛林、没完 孤身出境艰难从勐拉开始 经过长达3天紧张的准备和一路狂奔,4月1日晚7时,AF3记者和云南某报记者小杨终于抵达边陲小镇打洛。数公里外就是缅甸掸帮东部第四特区的首府勐拉。站在中缅一条街眺望缅甸,重重叠叠的山梁下就是那片危机四伏的土地———金三角。紧张的气息从夜风中扑面而来,只身闯毒源第一现场,我心里没底。 出境前,云南边防武警多次告诫记者,金三角地区情况复杂,各种武装不计其数,特别是大宗毒品加工、贩运都被地方武装直接控制。流血事件经常发生。缅甸各特区政府公开宣称禁止毒品交易,缅甸掸帮东部第四特区早在1995年就对外宣布全面禁绝鸦片种植与加工,但距离第四特区首府不到100公里的地方,就是缅北重要的罂粟种植区。 4月2日早上8时,验证、盖章、放行。走出检查站10米远,小杨回头望着国门沉默良久:“希望我们能安全回来。” 穿过几百米长的缓冲区,一个持枪的缅甸掸帮东部第四特区警察拦住我们,金三角之行从这里开始。刚进勐拉市区,满眼都是金碧辉煌的娱乐公司(赌场)和豪华酒店。一辆辆豪华本田轿车在街上候客。楠马河穿城而过。不足6万人的缅北边境小镇在赌博业的支撑下,奇怪地繁华着。 按计划,我们住进某大赌场属下的新宝大酒店。正当我们试图全面收集金三角鸦片情况的时候,小杨得到一个重要信息,被西方国家定性为亚洲最大贩毒武装集团———佤联军,与当地毒品加工厂的武装正在进行一场战斗,有几名贩毒武装人员被打死,171部队也有伤员,战斗激烈而残酷。几天后,一个熟知详情的军人将返回佤帮中央所在地,这是金三角送给我的第一份见面礼,但我必须穿越被不同武装所控制的200公里高原地带、进入佤帮才能与他见面。 记者和杨然立即进行了简单分工。我拍摄当地赌场和地方武装,杨然则与他在金三角地区几个有限的“熟人”联系,试图与从缅北罂粟种植区进入帮康、并与从南部军区回来的知情人汇合,为穿越罂粟种植区域捕捉毒源地“毒品第一现场”的终极目标打下基础。事后证明,这是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 “寻毒”受挫勐拉没有“毒影” 2日下午2时,风云突变。杨然不仅没能找到一个熟人,而且因为种种原因,他还必须立即回国。从现在起,我只能孤独地去完成探秘“毒品第一现场”的任务。 据悉,金三角的军人对毒品有最权威的发言权,找到军队就成功了一半。但在勐拉街头闲逛了1天,我不但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罂粟的影子,还根本无法接近当地驻军。好不容易在勐拉市场内找到一个年轻的重庆籍民兵,但这个士兵除了拉几句家常,说说重庆旧事外,对一切有关军队和毒品的情况都闭口不谈。而我想和其他士兵套话时,这个重庆籍士兵立即阻止了他们。而当地居民透露的零星线索显示,只有进入佤帮才能“方便”地发现罂粟种植区以及鸦片的交易情况。我必须穿越罂粟种植区,惟一有效和安全的路径就是依靠军队搭桥。 3日上午,掸东同盟军士兵军校的训练结束前,我就早早地守候在阅兵场外,想法接近一个“警惕性”不高的士兵。10时许,士兵们高呼口号离开阅兵场,一个年近50岁的老兵引起我的注意。他没有许多年轻移民士兵(近年从外地移居勐拉的第二代人)的那种骄横之气。他沉默着,但对身边一切显得十分好奇。记者试探着迎上去,打着手势向他“问路”。这个哈尼族老兵会一点简单的汉语,他热情地为记者指路。从简单的交流中,我知道他是一个班长,有20多年的兵龄,参加过多次战斗。 为报答他的热情,我邀请他一起吃中午饭。他犹豫一下答应了。像他这样的老兵每月的工资只有60元人民币。在纸醉金迷的勐拉,这点钱只够上一次饭馆。 在勐拉市场里的饭馆坐定,老兵说,他20岁当兵,有28年的兵龄,打了15年的仗。他都不清楚到底和哪些人打仗,只知道连长喊打谁他们就打谁。30岁的时候有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在与另一支地方武装作战的过程中,他和一个同伴与部队失散了,东躲西藏中同伴被地雷炸死,他在山里钻了两天终于跑了回来。老兵说:“缅泰边境丛林里地雷那个多啊,一脚踩下去,说不定自己就飞上了天。”战争给他留下两处伤疤,一处在手上,一处在肩头。好在打中肩头的子弹只是撕开了一块肉。 老兵说,以前行军打仗的时候,因骡马数量不足,他们除了要带枪支弹药外,每人还要背几公斤黄砒(鸦片初加工产品)到指定的地方。常年打仗、他错过了娶老婆的最佳年龄。今年已经48岁的老兵最大的心愿就是讨一个老婆,但他说:“没希望,因为没钱。”随后,他长时间地沉默着。 让人失望的是,老兵证实,现在在勐拉基本看不见鸦片当街交易的场面,勐拉附近也没有种植区。要看鸦片必须进山。记者提出到军营里看看。他同意了。 独闯军营辟“寻毒”路径 擦着勐拉小城的边缘,我们沿一条新修的土路向山顶爬去。山路越走越高,绕过两道弯,一个突兀而起的土包出现在眼前,老兵说:“军营到了”。从四周看,军营藏在山坳里,隐蔽在树林中,从勐拉市区很难发现它的存在,而站在军营的空地上,脚下的城市一览无遗。 老兵直接把我带进连长的房间,连长与他来自同一个寨子。掸东同盟军已经有13年的和平时光,在这支部队里,像他们这样经过战争的人并不是很多。在新兵面前,这个老兵有绝对的权威,就是连长也会给他一些面子。连长,一个全身黝黑40岁出头的中年男子,穿着筒裙躺在床上惊愕地看着我的出现。 按“交朋友”的程序先发烟。但掏出烟盒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烟盒空了。 连长笑了,一声吆喝,一个12岁的小兵飞快地从门外跑进来,立正。连长命令:“去买烟。”小兵怯生生地接过我的钱,飞快地向山下跑去。10分钟不到,小兵又一路小跑从山下回来,立正等候下一个命令。连长一挥手,小兵悄然退出门去。 连长告诉记者,他9岁当兵,13年前,这支部队属于缅北原著名的八一五军区。他现在每个月工资90元人民币,家里有4个孩子。他抽烟最多只能抽3元一包的春城。平时基本是以烟叶代替。尽管已经是管着30多人的连长,但城里的赌场、红灯区他没有跨进过一步,一年也不会去一次饭馆。 连长说,由于新兵太多,第四特区连续13年没有战争,掸东同盟军的枪支弹药不必像原来一样经常放在身边。但军官还是随身携带着枪。连长说着,一支枪出现在手中。连长退下满满的弹夹,将空枪交给我。 人熟了,连长也就无话不说。他说,现在佤帮多罂粟,那里是佤联军控制的地盘。首府是帮桑(已改名为帮康),从勐拉到帮康最安全的路线是从打洛进入中国,然后经中国境内的勐海、澜沧、孟连、最后从孟啊口岸出境到达帮康。南线则直接从缅甸境内穿越南佤卡山,经勐片、勐波、霍岛直接到帮康。南线是佤帮重要的罂粟种植区,一条土路穿越高山河谷地带,路况恶劣、车祸事件经常发生。即使乘坐皮卡越野也需要9个小时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经南线进入帮康需要经过数个由掸东同盟军与佤联军武装守卫的关卡,南线每天有一趟发往帮康的中巴车。但沿途的关卡肯定会将我拦截下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找佤帮驻勐拉办事处。13年前,他们与佤帮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可以帮忙联络。一条穿越缅北高原罂粟种植区的道路就这样渐渐明晰起来。 离开军营时,我把一盒价值25元的香烟留给连长。老兵十分眼馋,他比划着说:“我买烟,送你下山。”为了不让他失望,记者提出为他付账。他犹豫好半天,只挑选了5包单价为3元的“春城”…… 枪口在上扣开佤帮之门 据有关报道显示,2002年,缅甸佤联军控制着缅甸主要鸦片和海洛因种植及交易,同时控制着缅甸大约80%的苯甲基安非他明片的高额贸易。 勐拉街头却很少有人知道帮康。经连长牵线搭桥,记者很快找到佤帮驻勐拉办事处寻求援助。佤帮驻勐拉办事处是一栋漂亮的5层大楼。后面山坡上还有一片平房。但奇怪的是,装饰漂亮的大楼里所有大门都紧闭着,平房内两个皮肤黝黑的年轻小伙子无所事事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光脚一直跷到窗台上。 其中一个小伙子叫岩宝,19岁就有十多次战斗经历。岩宝说,佤族在战斗中无所畏惧,伤亡惊人,但他们从不惧怕。调到办事处最直接的好处是工资从每月40元涨到了300元人民币。但钱不够用。 上午11时,一辆越野车风驰电掣地冲进办事处大院,一个戴墨镜的中年妇女跳下车。后院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惊慌地跑进来向岩宝嘀咕着,岩宝突然跳起来。中年妇女已经坐在了会客室。岩宝和他的同事们紧张地站着,手拿抹布却不知所措。据介绍,这个妇女是佤帮某领导的家属。 经过几个小时的沟通和一条春城烟的代价,岩宝终于同意为我拦截过境回帮康的车,但我需要向驾驶员支付费用。为了不暴露自己携带现金的情况,车费只能让办事处工作人员代为转交。4日早上7时,一辆来自佤帮的越野车从勐拉返回帮康,他同意只收取700元,条件是此事需要保密。原来,在金三角地区“假公济私”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4日早上7时,记者背着背包随岩宝赶到办事处,一辆皮卡越野车正在街边等我。年轻的驾驶员曼瓦漠然地看了我一眼:“上车。” 曼瓦只有18岁,但已经有5年驾龄。10岁当兵,一直在帮康做事务性的工作。连接勐拉与帮康的公路在缅北的崇山峻岭间逶迤而出。土路上黄土灰尘遮天蔽日。 曼瓦将车开得飞快。越野车在悬崖、河谷边一路狂奔。上午10时许,记者在对未知的恐惧中抵达掸东同盟军第一个武装检查站。 栏杆孤零零地横在公路下坡转弯处,但四周不见士兵的影子。我正在纳闷,一个士兵飞快地从左边陡坡上滑下来。顺着他的来路望去,10米外的高坡上一支黑洞洞的枪口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们的脑袋……曼瓦说,这个武装哨所上面是悬崖峭壁,左右是绝路,可以防止偷袭。哨所高居突出的山头,左右两边公路50米内都处在火力封锁范围。位于坡度较大的转弯处,车辆必须减速。一旦有人要强行冲关,驾驶员首先会被这些身经百战的士兵射杀。多年的战争让这些战士都成了军事地形学专家。在战事频繁的丛林里你看不到士兵,但他们无处不在。第一道关卡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但后面还有5道越来越严厉的哨所在等着我们。 一波三折逃单“寻毒”路 连续闯过两道关卡后,中午12时许,经过4个小时的狂奔,我们来到掸东同盟军与佤联军的联合检查站。长长的车队在这里等待办手续过境。按规定,记者必须在这里办理前往佤帮的手续。但曼瓦的车不能搭乘游客和商人。记者黝黑的皮肤与当地人近似,据说只要不开口说话,可望不办理任何手续闯两关一路混到帮康。最坏的结果是,记者被抓住后,曼瓦出面讲情,并缴纳罚款。从这里开始,记者闯进了佤联军控制的范围。 刚进入佤帮,路边目光所及的山头就是大片的罂粟种植地,罂粟已经收割完毕,光秃秃的山坡上只留下部分残留的罂粟苗。 路边的武装士兵多了起来。有的士兵甚至招手要搭车。这时,曼瓦总是一踩油门冲过去。从进入佤联军控制区域后,检查明显严格起来,武装士兵一丝不苟地将车辆的发动机号拓片与车本身进行核对,一切准确无误后才能过关。并不允许拍摄军队。 在抵达勐片某检查站时,曼瓦小声警告我:“别拍照。”随士兵进检查站后,一个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在20米外严密地关注着我的举动。高原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我“闭目养神”,汗水却从额头渗了出来…… 一个军官突然走来拉开了我们的车门,一句记者无法听懂的话随即抛过来…… 初闯帮康错过“第一现场” 关键词:山民拿出了一张纱布,上面的鸦片膏黑点清晰可见…… 曼瓦还没有出来,我艰难地指了指喉咙,装聋卖傻地摇摇头。他又问了句什么,我紧张起来。这时,曼瓦出来了:“他要搭车回帮康。” 光秃秃的山头继续在两边连绵不断地起伏着,曼瓦说:“早一点来,到处是罂粟花”。 我们的车在勐片修补轮胎时,我走进了附近的村子与一个18岁的佤族女孩交谈,想寻找关于勐片鸦片交易的细节。但谈话才刚刚开始,这个女孩的丈夫就追了过来。驾驶员曼瓦在听完对方的话后,坚决拒绝充当我的翻译。甩开曼瓦后,从这个男子有限的汉语词汇中,我听出了鸦片、赌场筹码在当地可以像现金一样使用。但这个男人没有给我看他的鸦片。 驶过勐片,越野车进入了南卡佤山系深处。高原上到处是一片片烧荒后的痕迹。佤族军官说:“放一把火,有的大火要烧上几天。七八月间把罂粟种子撒下去,一直到收割季节。” 在霍岛街边,一群衣衫褴褛的山民将大包小包的货物扔在路边休息。曼瓦停车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一个山民说:寨子里没有公路,从这里走回扎朗寨子还需要6个小时。一个穿军装的山民掏出一张包裹鸦片的布,上面零星的黑点依稀可见。“山货(鸦片)刚卖掉,帮康城里的烟会已经散了。” 曼瓦说:“这布裹烟抽着很香,不会上瘾。”曼瓦扯下一块滤布点燃,这股怪怪的清香让我毛骨悚然。帮康烟会刚散的消息让我十分沮丧———我只抓住了一次鸦片交易的“尾巴”…… 暗夜“接头”“谜底”扑朔迷离 关键词:一阵敲门声将我惊醒。打开门,一个满脸倦容的军官出现在门边…… 4月4日下午5时,皮卡车越过南卡佤山口。山下,一个小镇出现在眼前。曼瓦说:“帮康到了。”方圆不足5公里的小镇,绿树掩映的别墅与小铁皮房、小竹楼、低矮的平房以及高大的赌场奇妙地混杂着。这就是有名的帮康? 佤帮第二特区海关检查站外,一个武装哨兵雕塑一般站在哨位上。几个军官和一名女海关人员拦住了我们的车。另一个军官闲得无聊,把手枪的扳机推得咔咔作响。车里的空气紧张得快要凝固了。 发动机号,大梁号。几个海关人员和士兵板着面孔一丝不苟地执行核对任务。没人问我。大约过了5分钟,军官扬起了手——我踏进了帮康。 (旁白)根据事先的约定,下午6点,一个神秘客人将会为我送来部队6天前剿灭海洛因加工厂的图片和资料。 帮康街头无法与勐拉的繁华相提并论。没有出租车,破旧的火三轮在街头无精打采地揽客。唯一的亮点是满街奔跑着昂贵的皮卡越野车。在当地有一种说法,在贫困的佤帮地区,皮卡车背后都有一个无法公开的秘密。许多10多岁的年轻人的背后都插着一把手枪。曼瓦说,那可是真家伙。 我让曼瓦在城里绕了一圈,但烟会早在几小时以前就散了,鸦片的踪影全无。 曼瓦火速将我送到帮康最好的美心宾馆。但我惊讶地发现,号称帮康第一宾馆的美心客房里一片凄凉,我的房间连床都没有铺。服务员告诫:“不要让陌生人进来,晚上别去城里偏僻的角落。这里经常有人被打死。” 服务员出去后,我飞快地对宾馆的床垫、枕头、被子、沙发甚至卫生间都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生怕自己不小心中了“暗算”。根据曼瓦传授的经验,在毒源地,宾馆或者招待所有可能遗留下吸、贩毒人员的工具或者是赃物,一旦被误打误中就有口难辩了。一些吸毒人员有携带爱滋病毒的可能,要是被遗留的针头扎上一针,那可就“中大彩”了。 在缅北高原担惊受怕地奔波了一天,我倒在椅子上就疲惫地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敲门声将我惊醒。打开门,一个满脸倦容的军官出现在门边…… 丛林枪声禁毒战斗惨烈 关键词:海洛因工厂用先进的M15冲锋枪开枪还击,战斗十分惨烈…… 来人是给记者送资料照片来的。他打开了一个包裹,一叠照片露了出来:一个新开挖的掩体,一个当地人血淋淋的尸体;一群全副武装的佤联军士兵在打扫战场;一个年轻的佤族人被击毙在大树后面;另一个人倒毙在铺满落叶的丛林里…… 来人说:“2003年2月份,在佤联军南部军区控制区发现一个海洛因加工厂正在大规模加工毒品。这个毒品工厂就在扎努村。”来人向记者讲述了缅甸佤联军缉毒小分队围剿海洛因工厂的故事—— 2003年1月初,缅甸佤联军南部军区调集精锐分队悄然进驻扎努村丛林。但部队的逐渐靠近还是引起了海洛因工厂的重视,3月下旬,该海洛因工厂的武装人员在附近挖起了战壕和掩体。3月30日上午9时,小分队乘坐两辆皮卡车刚刚接近扎努村,突然发现一百米外一支火箭筒从掩体里伸了出来,瞄准了皮卡车。“有情况。”车上的士兵一声警报,数十名战士飞快地跳下车,一个士兵立即举枪点射,火箭筒手应声栽倒在战壕里。 战斗突然打响,训练有素的小分队战士立即变成散兵队型,并不顾地雷的威胁从四面向海洛因工厂发起了冲锋。海洛因工厂用先进的M15冲锋枪开枪还击,战斗十分惨烈。战斗在10多分钟后结束。9名顽抗的武装人员被当场击毙,数十人被抓获。事后打扫战场时,在工厂里发现了毒品400多公斤,同时还发现包括火箭筒、M15冲锋枪、地雷、炸药等在内的大量军火。一个缉毒战士受伤。据工厂的制毒工具的磨损程度显示,该毒品加工厂已经存在了3年。 中巴车上与毒贩面对面 关键词:高个子毒贩转过头来,我惊呆了,在孟啊口岸,我与这个面色黝黑而表情本分的人擦肩而过…… 帮康是一个奇怪的城市,豪华的赌场里,贵宾室里拥挤着一掷万金的富豪,赌场大厅门口,满脸菜色的山民如饥似渴地玩小押宝。作为烟会的主要地点,帮康的新农贸市场冷冷清清。(旁白)我寻找毒品交易第一现场的努力再次受挫。尽管已经进入了金三角毒源的核心地带,我发现自己寻找鸦片交易第一现场的“终极目标”始终没有浮出水面。我决定趁等待烟会的时间随人流过境,对毒品向中国境内走私的路线进行实地追踪。 5日中午11时,在佤帮第二特区旅游局工作人员李兴的帮助下,我顺利地跨上了界河南卡江大桥。在中国边防武警的特许和严格的行李检查后,终于站在了祖国的土地上。 界河南卡江蜿蜒南去。行人从各处钻出来聚集在口岸附近,准备乘车前往中国内地。这里有毒贩吗?一个皮肤黝黑的高个子在等车的人群中十分显眼。他木讷的表情和简单的行李首先让我放弃了对他的关注。(旁白)事后证明,这是我一个致命的“失误”。 从帮康进入中国,第一个县城就是孟连。中午12时,我混在大批从缅甸过来的人群中,登上了第二辆前往孟连的中巴,其中,几个携带大量包裹和皮箱的人让我“特别感兴趣”。 中午1时50分,在距离中国孟连县城约10公里的地方,中巴停了下来。一个武警上车———中国孟连公安局缉毒大队查禁毒品。好戏开场了,我习惯性地冲下车,前面的中巴已经被拦停,(旁白)首个关于查禁金三角海洛因贩运的“第一现场”就这样一头撞进了我的镜头。 (现场特写)一辆警车停在路边,警察们如临大敌。一个面目黝黑的高个子戴着手铐被推上了警车,身边是他红色的手提袋。缉毒警官提起手提袋告诉记者:“刚刚从车上查获来自帮康的海洛因,可能有一公斤。”高个子毒贩转过头来,我惊呆了,在孟啊口岸,我与这个面色黝黑而表情本分的人擦肩而过。据悉,几天前他越过南卡江进入帮康,今天早上携带毒品从南卡江上涉水绕过检查站入境,乘上了前往孟连的中巴…… (贩运内幕)在帮康时,有当地资深人士向记者讲述了毒品运送的内幕:从帮康买到的是纯度为99.9%的海洛因,运到昆明后,二道贩子在其中加入同等质量的砂糖和奎宁,再加价20%卖给了第三道贩子。第三道贩子又在每公斤海洛因中加入600克砂糖和奎宁并分装卖出,最后的小毒贩再次加入砂糖和奎宁或头痛粉分装成更小的包装……经过中间毒贩的层层加价和混装,最后到达吸毒人员的手中。这样,在帮康每公斤售价为1万元、纯度为99.9%的海洛因,到达成都吸毒者手中的时候,同等纯度海洛因每公斤的实际售价就高得惊人了。 为了斩断这条向北的毒品流通渠道,中国缉毒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 再访帮康直击鸦片交易 关键词:几个满脸尘垢的山民剥开用菜叶包裹的鸦片,贩子用刀切开沥青一般的烟膏,再放到鼻子上闻一闻…… 5日完成从帮康到我国澜沧的全程追踪后,我就地休整。7日重回帮康,并一路北上到120公里外的小集镇岩城,据说那里的鸦片交易十分频繁。(旁白)从帮康启程时,来自云南临沧的服务员警告记者,独自在缅北的大山里游荡是不明智的举动。 经过6个小时的颠簸,下午2点,我抵达岩城镇以北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寨子。躲在高脚屋下的孩子们半裸着身子,因为营养不良肚子肿胀着。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悄悄看着我。 寨子外,一片还挂着果实的罂粟残苗显得十分扎眼。附近有军人在游荡,我没有冒失地走近去看个究竟。 借着喝水的名义,我走进了寨子里桑龙的家。除了几个 锅碗瓢盆和火塘上的铁三角,没有一样像样的用具。但他说,家里现在有3口人,在寨子里还算“过得去”。 桑龙说,在这里,烧出一片荒地就可以种罂粟。今年佤帮境内的鸦片膏黑市价每公斤大约1000—2500元人民币,而贩毒集团强行收购价格仅仅为800元人民币左右。一个人为了维持基本生存,需种“半驾犁”(约1亩)的罂粟。他每年可以从鸦片上挣到1500元左右,只够买米、盐巴。桑龙可能永远也没有想过,他种植了一辈子的鸦片,到头来还是在贫穷与饥饿的边缘挣扎。而经他亲手刮下来的鸦片又让更多的人徘徊在穷困潦倒和死亡的边缘。 据称,佤联军绝对禁止山民们吸毒。桑龙说:“如果他们抓到你在吸毒,就会把你关到土洞里。”在地上挖一个三米深、两米宽的洞。毒瘾发作的人只能在里面干熬直到断瘾。复吸的代价是可能被枪毙。 在岩城街边,我前后追逐上千公里寻找的毒品交易“第一现场”终于出现了。 (现场特写)几个满脸尘垢的山民剥开用菜叶包裹的鸦片,贩子用刀切开沥青一般的烟膏,再放到鼻子上闻一闻,用我无法听懂的语言讨价还价后,放到一个手工做的天平里。天平里一边是大烟膏,一边是银币代替的砝码。 我第一个动作就是掏摄像机。但附近根本没有容我从容安装偷拍设备的地方。当我飞快地跑到附近连接好拍摄线返回时,大烟早已不翼而飞。连收购大烟的人和出售大烟的山民也都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简易天平和做砝码计量的银币还在原地诉说着一个刚刚发生的秘密。 (旁白)由于面临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即使在这里,毒品交易也属“非法”,只能半公开地进行。 当地居民对我的“少见多怪”不以为然。他说:“只要你有时间,这种买卖场面在任何一个烟会上都可以看到。”我还要继续追问,他对我的好奇心产生了怀疑,很快就消失了。他的突然消失只有两种结果,回避或者告密。我不加思索地快速离开,在街边租车回撤到30公里外的营盘。 7日下午4时许,在向帮康旅游局“请求继续旅行”时,对方告诉我:“我们无法给予你任何安全上的承诺。”他们要求我必须返回。 从营盘到帮康每天只有一班对开的中巴车。一辆辆皮卡车对我的招呼置之不理,我锲而不舍地坚持着,一个小时之后,一辆皮卡车终于停了下来:“400元回帮康。” 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敲诈,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记者龙灿)
两性学堂--掀起夏日阳光中的爱欲狂潮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2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