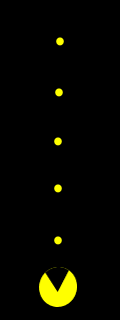| 新民周刊:“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的无奈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10日00:10 新民周刊 | ||
|
高耀洁:欲罢不能 撰稿/李清川(记者)摄影/钱东升(记者) 她坚持不说假话,但她阻止不了别人说假话;
她是艾滋病患者最亲近的人,但她也阻止不了艾滋病人“扎针”报复无辜者的行为; 她是第一个将“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观点进行到底的人,并为此深入乡村走访调查; 她被称作“民间防艾第一人”,古稀之年仍在密切关注着传染病疫情的发展;对我们而言,她是一面镜子 高耀洁有两副款式、颜色相同的老花镜:一副在家看书,一副出门认人,两副花镜的度数差别并不大,却绝不混淆。但有时,高耀洁还是无法清楚判断出哪些人真正需要她的帮助,哪些人只是欺骗她的善良。 尽管可能被假话欺骗,77岁的高耀洁坚持一点:不说假话。 在由她编写、免费赠阅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的印刷品中,高耀洁用发生在上蔡、项城、鄢陵等地的实例不断佐证着自己的观点: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因为采血感染的。但,接受此观点的人并不多。 “有时讲真话的结果并不好,但我已经欲罢不能。”说这话时,高耀洁正端坐在6月14日正午太阳的黄晕中,洋溢着笑容,面前的墙上挂着两幅立轴,“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另一幅字上是旁人的评价:她有太浓的爱太软的心。这间位于郑州红旗路某小区内的“新房”是儿子借给老两口暂住的,老家具样式陈旧但质地结实,几堵书整齐地码放在墙边。唯一透露些现代气息的,是清华大学学生3年前捐赠的电脑。 高耀洁记忆力惊人,她不仅能脱口而出每一个被问及的与她相关事件的准确日期,还能整段整段背出在私塾中学来的四书典籍,如果不是目睹了她爬楼梯时的蹒跚,我们对她已过古稀的年龄一直存有错觉。 倒了两杯水,没有寒暄,高耀洁便开始她的故事,开始流泪,沉重的话题几乎每隔20分钟就会被刺耳的电话响铃打断。 退休医生走上防治艾滋病的宣传路 作为医生,高耀洁很关心非典疫情,“与非典很高的治愈率相比较,艾滋病更加可怕,但在初始阶段,它们都没引起足够重视,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回顾自己的防艾之路,高耀洁也感偶然性很大:1990年8月,时任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的高耀洁去检查冤假错案情况,在新乡监狱,一名叫张雪玲的女犯引起了她的注意。女犯年纪不大,因为卖淫染上了梅毒、淋病、尖锐湿疣3种性病。“为啥偏要干这一行?”“挣钱呗!俺家盖房子全靠我挣钱!”“就不怕染上性病、艾滋病?”“只要有钱就可以治。”女犯轻描淡写的回答令高耀洁触动很大。为此,她对全省监狱1185名在押女犯进行性病调查,结果让人震惊:这些女犯中92%的人患有性病,有的人已感染艾滋病病毒。 结果令妇科专家高耀洁很有些自责。但真正让她步入防治性病、艾滋病之路的却是另一件事:1996年4月7日,河南某医院接诊了一位42岁的疑难女患者,邀请高教授前去会诊。最后查明,这是一位艾滋病患者,因子宫肌瘤手术输血而感染病毒,21天后,患者撒手西去。临终前,她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高教授说:“高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怎么就没治呢?……”她输的是血库中的血,高耀洁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有人到河南省偏远贫穷的农村地区收购廉价血浆,用来制药。当时血站的做法是,从血液中提取血浆,然后把剩下的红血球分开,再输入卖血人体内。因为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400毫升不会有明显虚弱和委靡不振。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中降临了。事后的研究发现,多个环节被认为存在着致命漏洞:首先是抽完血后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钳,这两个器械都与抽出来的全血接触;然后是离心机,当时普遍采用的离心机里面被分成12个小锅,每个小锅里放两袋血,很容易出现血袋被甩破的情况,如果血站分离员不严格操作,未将破损的血袋扔掉,沾有别人血液的红细胞会被回输。 这样一来,只要一个卖血人体内带有艾滋病毒,就会迅速蔓延开来。 在最鼎盛时期,整个河南的血站有230多家,直到1995年3月,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发布通知,已经泛滥成灾的血站被大规模取缔,最后一批非法血站也在1997年遭到严厉打击而销声匿迹。 艾滋病大规模血液传播的蔓延之势被掐止了,但悲剧已经上演。高耀洁做了一个决定:谢绝给病人看病,走上防艾之路。她希望全社会能够了解艾滋病,关注艾滋病,最终远离艾滋病。那时,高耀洁“并没有想到这条路如此难走”。 起先,高耀洁背着筹资印出的宣传防治艾滋病、性病的资料,来到人口流动大的火车站、汽车站去散发,不少人避之不及地将资料扔在地上。慢慢地,情况好起来,愿意义务帮助她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但资料的最大市场还是那些艾滋病患者集中的贫困地区。与来自艾滋病患者和家属的热情相比,某些专家的冷漠令高耀洁很不满意,“就前两天,我曾经把材料邮寄给中科院的一位知名院士,没几天,材料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地方政府、民间和专家对艾滋病防治态度的差异,使高耀洁感觉如鲠在喉。 她更大的焦虑是,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已经进入死亡的高发期,“有一次家里来了12个艾滋病人,今年春节再给他们汇款时被退回了4份,他们都已经死了。” 7928封来信和一张收支表 高耀洁的卧室墙壁立着一排大柜子,里面装的是她收到的全部信件,所有的信件她都会登记在册,便于查找。从1999年8月15日到2003年6月14日,她登记的信件为7928封,平均每天6封。在这些信件中,有十分之一是“卖药的”,“每个人都说自己掌握了治疗艾滋病的秘方,如果我帮助推荐可以利润分成,我很难过,竟然骗到这些最可怜的艾滋病患者身上。” 高耀洁退休后的工资是2100多元,他的老伴郭明久退休时是内科主任医师,每月收入2000多元,在中原腹地的郑州,绝不算低。孩子们都已有了自己的事业,不需要老两口资助,他们的日子看起来还是太过简单。 我问她,你有存款吗?高耀洁说,以前没有,现在有。79岁的老伴郭明久因我是老乡,话格外多。他说,“2000年开始,家里的账由我来管,那之前高耀洁管钱的时候,把钱都给了那些艾滋病患者和家属,我们没有一分钱存款。” 高耀洁和老伴两人的花销不大,每月200元的菜钱是最大支出。说起来,高耀洁很有些骄傲,“我从不买衣服、药品和鸡蛋,这些都是别人送的。”和这个年纪的老太不一样,除了一只手表,她的身上没有一件饰品,包括戒指。高耀洁说,“我自己没买过戒指,别人曾送过我一个,我把它送人了。”戒送给了郭明久与前妻的儿媳。而对于尚存的耳洞,她的解释是:在我们那样的家庭里,女孩从小就要留下耳洞。 现在,高耀洁的工资由老伴掌管,每个月可以领到700元钱,但她外出讲课的收入和稿费的支配不受影响。2002年,高耀洁给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讲课,获6000元报酬,不久前,她去巩义讲授计划生育,有800元进账。这些钱很快就被她少至50元多至500元地转给了那些艾滋病患者和孤儿。去年,她的支出是3万多元。而在2001年,由于有奖金收入,她用了28万元付掉了《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的印刷费用,这本书的印数已经超过30万册。 由高耀洁主办编写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的小报已经出了15期,总印数达到了53万份,费用是由她和各界捐助者承担的,“余维红女士1660元,《三月风》杂志编辑部1000元,上海纪秀梅女士2000元……”每笔捐款,高耀洁都清楚地印在了醒目位置上。尽管第16期的2000元印刷费还没有着落,高耀洁仍然拿不准接受捐助是否合适。 “收钱不好处理,两百、三百的邮票好一些。”为此,她退回了浙江一位老板5000元的捐赠。 从高耀洁手里放出的钱并没有全部如她所愿发挥作用,去年,她曾给一个父母都因感染艾滋病去世的孩子寄去500元钱,后来得知,孩子的奶奶在收到钱后只给了孙子30元钱,连学费都不够,当年7月30日,原本还要寄钱的高耀洁把孩子的名字划掉了。不久,孩子经高耀洁联系,在山东有了新家。 “民间防艾第一人”的无奈 高耀洁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在我们与她接触的两天时间里,经常因为她泪水沾襟而无措。她自己说,“我已经不知道为了艾滋病患者流了多少眼泪,也不知道陪着他们流了多少眼泪。”而那一次流泪,她永生难忘,“2001年3月31日,42岁的艾滋病患者王有志给我写信,希望我和他见一面,我赶到村子时,村子里正在出殡,走到棺材前,我才知道死的人正是王有志,我嚎啕大哭。” 还有一次,高耀洁到豫南的一个村子里,透过一扇没有合上的大门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一个女人上吊了,一个两岁模样的男孩正抱着妈妈的脚后跟,边啃边喊,“娘,你下来啊,你下来啊。”别人说,孩子的爸爸16岁时开始卖血,因为感染艾滋病已经死了。高耀洁的眼泪立刻流下来了。也就是从这时起,她改变了一贯的方式,花更多的时间去关心那些艾滋病患者的遗孤。 高耀洁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那些孩子,说到底是为了我们整个民族,我去村子里,一个小孩对我说,将来要杀人,要杀把艾滋病传染给他爸妈的人。事实上,这样的复仇情绪在不少地区是普遍存在的。从高耀洁提供的一张照片,我们认识了一位叫做张夏的男孩。一家有5人因为感染艾滋病辞世,2002年夏天,读小学五年级的张夏辍学了,他在砖厂打工每天只挣10元钱维持生活。心事重重的他一次在父母坟前痛哭后,在左臂上刻下了“忍”、“仇”、“杀”等字。 高耀洁很揪心,但与需要帮助的孩子数量相比,她明显力薄。 在客厅墙上,挂着她与艾滋病孤儿的15张合影,孤儿中有人已经有了新家,但绝大多数仍在艰难生活,她在照片上写了一段话,“请正视、善待、关心、同情艾滋病人,救助艾滋病人遗孤。” “不会做人”的善良老人 在今年6月1日印出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中,高耀洁把萨迪的话印在了报眉: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你就不配称为人。这样的选编其实是她一贯的风骨,也让不少人胸闷。高耀洁的老伴也很为她担心,“她这样做得罪的人太多。” 高耀洁无动于衷。 因为高耀洁是专家,医院很想她能回到医院上班,并且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你只要来,几分钟都行。”她还是回绝得一点余地也没留,“我就是不去,不能让他们借着我的名字赚钱。”她对有误导可能的种种做法深恶痛绝。 2001年,高耀洁用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1万美元赠款,加印了《艾滋病性病的防治》。她想把这些书全部发给最需要的人。为此,每来一次记者,她都会把“书讯”送出一份。因为“邮费负担过重”,她不得不说明,“请在信中付邮票作为寄书的邮挂费(无邮票者恕不赠送)”。她收取的邮票费用和印刷成本无关,1本3元,2本3元2角,3本3元5角,4本4元,……30本16元,如果大量需要,有单位介绍信,费用全免。 此外,她还把书送到有关机构委托发放,她出示的一份单据是去年8月的发放记录:省卫生防疫站21000本,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3150本,宋庆龄基金会525本,省图书馆5075本。因为省图书馆有134个市县图书馆和800个服务站,高耀洁还准备多送一些给他们。她最大的担心是这些书被堆在仓库里或被当废品卖掉。 “我与众不同的是在别人说好的时候总说不好。”1998年1月23日,高耀洁参加河南文史馆的春节茶话会,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省长马忠臣征求意见时,她出了道难题,“很多游医给人看病,不是性病也要告诉人家得了性病,借此骗取钱财。”在此之前,她经过深入调查掌握了性病游医、虚假广告的第一手资料,并写出了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高耀洁列举了性病游医骗人的真实事例,介绍了正规医疗单位的性病专科被游医垄断的详情。最后她写道:长此下去,我们河南将成为“性病大省”,郑州将成为“性病大市”。她的话直接促成了以游医为对象的整顿医疗市场行动。 对儿女永远的愧疚 高耀洁说,现代社会与我格格不入。这应该和她的经历相关。 1927年,高耀洁出生在山东曹县的一个大户家庭,这个13代都是地主的大家在当地很有些威望,今天的“高新庄”的名字便是因高家世代居住而得名的。与高新庄相邻的梁堂村党支部书记张荣桂说,那时这里的地都是高家的,在这里,高耀洁在曾是前清翰林的外祖父的关照下,进了私塾。 1939年,为了躲避战火,高耀洁的父亲带着子女举家迁往河南开封,所以至今高耀洁仍然是一口标准的开封口音。 “我是一个聪明的人,高二的时候我参加大学的招生考试,平均分是65分。”本想读中国文学的她最终选择了河南大学的医学院,只是因为负责招生的人在看过她的手后说,这双手不学医学可惜了。那天,为了不让人看出自己是小脚,高耀洁穿了一双35码的球鞋。 1953年,本应秋季毕业的她,因为政治学习的安排,离校的时间延迟到12月3日,她成了省直职工医院的一名妇科医生。 1966年6月6日,山雨欲来时代的开始,高耀洁被调离临床一线,到太平间工作。作为医院的先进工作者,高耀洁参加了赴天津的参观团,因为在大沽口炮台照的一张照片,她被扣上了妄图复辟的帽子。此前,她已被揭发为“杀人不见血的刀”——作为一位知名妇科医生,她常做流产手术。再加上她的出身,很多年,高耀洁的生活如履薄冰。 1974年4月12日,高耀洁解放了,来到了河南中医院附属医院。在那之后的十几年的春节,高耀洁都没能完整在家呆过,不是在单位值班,就是在病房陪着病人,以至于孩子们回到家里,总是先叫爸爸。曾与她共事的医生这样评价她,“她不是一个随和的人,几乎和每个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也很少出现在办公室里,更不会参加大家的活动。”高耀洁说,我没有什么朋友,和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很少往来,读书和工作的时候我都在拼命,我宁可在病房也不在办公室里和人聊天或者打毛衣。那时是高耀洁体重最轻的时候,只有70斤。 高耀洁是好医生,但可能不是好母亲。 在高校担任副教授的儿子曾对她说,“妈,今天的社会已经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了。”一个月前的搬家给了母子一次交流的机会,儿子哭着说,“我这一生从你这里得到的只有灾难。”高耀洁流着眼泪,“‘文革’开始时,只有14岁的孩子因为画了一张画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为了能把他投入监狱,孩子的年龄被改为19岁,其实就是因为我。” 一个特殊年代永远翻过去了,高耀洁在儿女心目中的形象却没有变化。 在她1998年上书整治游医后,女儿郭炎光首先受到牵连:作为河南某医院皮肤科医师,郭炎光所在的科室也被游医承包,并在随后的全省清理整顿中被有关主管部门赶走。医院损失了承包费,郭炎光也没法呆下去了,“女儿回到家中要自杀,我想给她调个工作单位,省里的领导也同意了,可是一直没着着落。” 如今,她的两个女儿,一个于2001年随丈夫去了加拿大,一个已不在临床一线工作。 老人计划的身后事 年过古稀,谈起身后事,高耀洁很平静,她想把“事业”和所有的资料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待选的是复旦大学教师高燕宁和北京大学李冬丽博士,因为她相信,他们会继续做下去。 6月14日,我们留在高耀洁家吃午饭,老伴忙了一中午,在平常高耀洁是不下厨房的。豆角、别人送的烤鸭、还有每人一碗的菜汤,因为习惯不同我们的胃口都不太好,高耀洁说,这些餐具被很多艾滋病患者用过,但你们不用紧张。 这天下午,郭明久与前妻的一个儿子带媳妇来看他们,高耀洁坚持把家里的唐三彩给了儿媳,还要他们拿着一个花瓶,儿媳没要,高耀洁有些遗憾地说,这可是钧瓷的…… 6月15日一早,我们和高耀洁同车出发,从中牟县、开封市、兰考县、商丘市、夏邑市、永城市一路过去。为了不让老伴担心,她趁老伴出门买菜的时候溜了出来,出租车的后备箱被她带的物品塞得满满的,那里有十几双旧鞋子、一包麦片、一斤大白兔奶糖,还有共计四期2200份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小报、30本《艾滋病性病防治》,两本《鲜为人知的故事》。鞋子被她沿途抛下,她说那些生活困难的人会拾回家,糖留给了永城的4岁艾滋病患者伉伉,那些书和资料她交给了伉伉的爸爸,希望她能代她做些宣传。 车上,高耀洁不断往嘴里塞些小饼干,她胃部的五分之四在1967年被切除了。司机王宝才夫妇给我们的包车价格并不公道,高耀洁说,“现在愿意到下面的车子并不多,这个司机的车子我一直在用。” 这个下午,高耀洁在伉伉的床上睡着了,这时的她才更像一位77岁的老人。■
订阅新浪新闻冲浪 足不出户随时了解最新新闻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