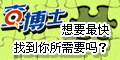| 和艾滋病人相处的一个下午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26日04:54 中国青年报 | |
|
本报记者 王尧 11月21日,北京。一群艾滋病人、大学生志愿者、司机、记者、医护人员在一起,度过了极具戏剧性的一个下午。 “病人坐一下你们的车,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你心里有点不舒服,我们能理解…… “我们要组织17名来自河南农村的艾滋病人,逛逛北京的公园。陪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大学生志愿者。你们报社感兴趣吗?”北京地坛医院宣传中心的陈明莲在电话里说。 陈明莲参与编辑着一本关爱艾滋病人的杂志《携手》。诞生在地坛医院的这本杂志,有艾滋病人参与编辑,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家。 北京地坛医院,在今年因作为SARS定点医院而被公众关注。其实,它从1987年就开始接收艾滋病人,1996年被确立为北京市艾滋病临床研究中心。1999年,这里成立了关爱艾滋病人的机构———“红丝带之家”。现在,已有400多名志愿者不定期参加一些和艾滋病人的交流活动。 11月21日中午,记者赶到地坛医院。 正准备出发,陈明莲的电话响了,她在电话里解释着:“请你们绝对放心,病人坐一下你们的车,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你心里有点不舒服,我们能理解……” 接着,又一个电话响了,陈明莲说:“您是出租车公司的调度吧?你们别紧张,我刚才和司机沟通过了,乘客确实是艾滋病人,但艾滋病是通过血液传播的,不会通过空气传播。” “如果坐公共汽车就能传染艾滋病,那可是世界新课题。”陈明莲特意把语调放得轻松,“我们今天的活动,也会帮助老百姓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我们很多人,还有志愿者,都和他们坐在一起。我们能保证你们的车和司机的绝对安全。” 放下电话,陈明莲对记者:“订车时,我们确实没有告诉出租车公司,他们是艾滋病人。我们担心说了租不到车。” “我们都是多活一天算一天的人。你们来看我们,我们太激动了。” 我们上了停在地坛公园牌楼前的一辆大巴。 汽车前排是艾滋病人,见有陌生人上车,他们的眼神有点紧张,也有些说不清楚的东西。汽车后排,坐着大学生,他们是中央财经大学的10名青年志愿者。 坐在我身边的张博同学说:“开始有30多个同学报名,后来选出了我们10个。我不怕,来之前读了点书。其实我想和他们坐在一起,医生说,分开坐也好。我们就分开了。” 有记者和艾滋病人并排坐在了一起聊天。 车开动后,陈明莲对记者说:“这些病人的年龄在30岁~50岁之间,已经经过了5个月的治疗,一些指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请各位记者朋友注意,你们的报道,无论文字,还是图片,如果里面出现了病人,一定要征求他们的同意,并且是书面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他们的隐私权。” 她又走到前排提醒艾滋病人:“记者要采访你,如果你不愿意,可以不回答。如果有记者要拍照,你不愿意,可以拒绝。”病人们的脑袋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开始商量。 陈明莲对大学生志愿者说:“我希望你们多在细节方面关爱这些病人。” 车行途中,车前的一个扩音器响起,是一个穿军绿色棉大衣的艾滋病人在讲话:“我们来自河南省××县××乡××村,我们村有3000多人,有500多人得了艾滋病,现在已经有100多人死了。有的人家失去了儿女,有的人家失去了爹娘。” “我的名字叫谭××,我家里的电话是××,手机是××。我们都是多活一天算一天的人,每天都是挣扎过来的。你们来看我们,我们太激动了,就是死了,也值得。”他的声音因激动有点颤抖。 “我们不是因为嫖娼、吸毒得这个病的,我们都是通过‘献血’得病的。”他们说的“献血”其实是卖血。 “我们每个月来北京检查一次,为了凑够路费,有的人要卖麦子、卖苞谷。”老谭说这话时,有病人和志愿者在抹眼泪,摄影记者开始照相。 带队的志愿者陈晓云也接过话筒:“我们还没有做什么,你们就夸奖我们,我们很惭愧。看到你们这么纯朴,这么善良,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俺一共卖了16次。每次都抽俺两大袋子血,有400毫升。一次给俺40块钱。” 到了北海公园,地坛医院给所有人买了门票。 大学生志愿者的胸前都别着一个小小的红丝带,这是全球艾滋病志愿者的标志。围着兜售纪念品的人指着“红丝带”问:“你们这是什么旅行团?”但没有人回答。 志愿者们为了讲解,带队的陈晓云同学去买公园简介。但是她遇到了尴尬———卖公园简介的人隔着玻璃盘问她:“你是地坛医院的医生,还是病人?”陈晓云说:“我给他们普及了好多艾滋病知识,才买到书。” 上山看白塔时,志愿者们开始搀扶一些年岁大的艾滋病人。摄影记者们忙成一片,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权,他们想拍艾滋病人是背影、志愿者是正面的照片,一直没有等到好角度。 等到了景山公园,多数艾滋病人都走不动了,不愿再登山。只有33岁的王红艳(化名)愿意上去看看:“要是自己出钱买公园票,俺是不会来的。买不起。” 她说自己有两个孩子,都在读书。丈夫和她都得了这病。刚知道的时候,她一下子就垮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俺只是哭,一见到孩子就哭。我们死了,孩子怎么办?” 她说,自己是卖血感染的。“俺一共卖了16次。每次都抽俺两大袋子血,有400毫升。一次给俺40块钱。” 站在北京的景山上,她第一次知道了,前边是过去皇帝住的故宫,旁边还有国家领导人办公的中南海。 “你们就这么把我们打发了?把我们拍来拍去?为什么不给我们钱?” 短短的游览结束了。艾滋病人们还要赶今晚的火车回老家。 记者和志愿者这才知道,这些艾滋病人都是前一天下午离家,坐一夜火车到北京,上午在医院检查完身体后,晚上再坐火车回去。老谭说:“我们不回去,谁会留我们呀?”大学生们决定跟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 陈明莲提醒记者,图片里千万不要出现这家出租车公司的名字,这是公司打电话来再三提的要求。 突然,大家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本来艾滋病人已经上车,但有三位妇女冲下车来大喊:“你们就这么把我们打发了?把我们拍来拍去?为什么不给我们钱?” 一位妇女对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嚷:“你们拍我们,不就是为了挣钱嘛!到我们村。拍照片挣钱的记者多了。不挣钱,你们拍什么?” 地坛医院的医生们在中间协调:“老谭,你们和医院一直配合得不错,怎么能这样呢?回去的车票钱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也有记者急了:“你们再这么不讲道理,我叫警察了。”老谭说:“你叫警察吧,赶紧叫吧。” 这边,地坛医院的医生们打电话给院里,征求处理意见。那边,大巴司机很认真地问我:“如果今天你的家人是我这个司机的角色,你会让他来开车吗?”他还说:“我怎么才能得到这个‘红丝带’?” 这个北京小伙子说:“客人上了我的车,无论是谁,我都不能把他们赶下去。”他也跟地坛医院的人商量:“能不能把客人送走后,用你们医院的专用设备给我的车消一下毒?费用,我们公司出都可以。”医生说,不用消毒的,坐车不会传染。这个善良的司机还在坚持。 那个嗓门大的女艾滋病人放下话:“如果不给我们钱,到了火车站,我们就不下车!”本打算送行的志愿者们,大多自己走了。“真是农民的劣根性。”有人说。一位女学生说:“想想我也能理解他们。他们不在北京要点儿钱,回去谁管他们呢?” 最后,一起来的地坛医院工作人员,全都随车去了火车站。 两天之后,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最后都解决好了。至于办法,就不说了吧。”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