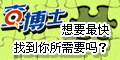| 河南平舆残害男生案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27日15:01 三联生活周刊 | |
|
记者吴琪 离奇的连环失踪 2001年9月24日晚,接到在平舆县城读书的女儿路欢欢的电话时,高洋店乡大陈村委路湾庄的38岁农民路德全心里就犯嘀咕:在县二中读书的15岁儿子路宁波一直是个好学生,怎 一宿没睡好,路德全带上妻子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赶到离家25里的县二中。正在主持学生晨读的班主任高老师以为是路宁波请了病假在家,警觉的路德全一下子慌了起来——他说,这么爱读书的孩子不会逃学,一定是被人控制了! 路德全于是跑到管辖区的古槐镇派出所报案,接待的警察说,“可能逃学了”。跑到县公安局,刑警五中队队长做了记录;放不下心的路德全又跑到学校旁边的永乐派出所报案。想到电视影响力大,路找到县电视台播了两天寻人通知。乡下20多个亲戚朋友也出动了,第一次打印了600张寻人启事,分布在县里的18个乡镇张贴。第二次打印了800多张在邻近县市张贴,白天跑政府部门请求帮助调查,晚上沿着县里惟一的一条小清河边走边喊。“一个活生生的大孩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路宁波的失踪在这个80多万人口的豫南县城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被问及的人们多半好心地提醒,孩子是不是出去打工了?平舆县是农业大县,90%以上的农业人口使这里成为劳务输出地,外出打工近则在60多公里外的驻马店市,远则北上北京,南下广州。虽然不大相信,“孩子出去这么久,总会遇到困难,有困难能不给家打电话?”但路德全没法在家坐下来,全国各地只要听到一点线索就去找。在两年多的奔找中,他惟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孩子可能被骗进了一些城市附近的“黑工厂”,失去了人生自由。 2002年7月,县电视台登的一则寻人启事引起了路德全的注意,一名叫王要东的17岁青年神秘失踪,双方家长联系上后一起开始找孩子。 真正让平舆县人“感觉到不对劲”是进入到2003年后,十几个15~20岁的男孩几个月内相继没影了。县二高的18岁学生王亮元月3日一天没上学,家长发现他的学生证、生活用品、衣服都在寝室,不像出走的样子,但谁也不知其去向。在县六中读初二的韩鹏正月十六去上学,平时两周回家一次,家长在正月二十八没见孩子回去。向同学打听,有人说头天在校外见过,突然没了音信。 比起毫无踪迹的“人间蒸发”,另外一些孩子则提供了失踪地点的线索。在县一高读书的辛店乡学生梁政威3月30日中午与同校的余向前等人一起吃午饭,饭桌上18人喝了40瓶啤酒。余与另外两人陪同梁一起进了游戏厅,在他们三人有事离去后,梁就消失了。20岁的赵明华在县自行车厂上班,4月16日中午去县文化馆附近录像厅看录像后没回,父母拿着照片去录像厅找,老板说,“有印象,他经常来”。三天后,在县里打工的17岁男孩翟鹏超同样在这间录像厅里出走消失,父母半夜找到他留在录像厅里的雨伞,自行车在楼下停着。9月5日,万金店乡在县里私立学校读书的15岁学生冯省失踪,父亲冯占学从孩子经常上网的“新世纪”网吧找到北京、深圳,杳无音信。 越来越多青年莫名失踪,在县中心区商业街开饭馆的田老板记得,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当地电视台隔三差五播寻人启事,街上经常看到几个中年人拿着照片逢人就问。慢慢地家属们聚到一起,发现失踪的孩子几乎全是农村到县城读书打工的,父母不在身边。失踪的地点集中在游戏厅、录像厅、网吧三大类娱乐场所。虽然心里还抱着一丝幻想,每一个家长又坚信自己的孩子不会自己不辞而别,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家长们整日在公安局、县政府、教育局之间奔波,“有的官员说孩子们出去看花花世界了,等着他们玩够了回来吧。”有的反问:“那么多学生,为什么你的孩子失踪了?是你自己没教育好。” 受害群体的被引诱空间 11月12日最后一个失踪者张强的报警给了寻亲家长们始料不及的噩耗,当地长期不被重视的现象突然以恶性刑事案件的方式呈现在了公众面前——一个叫黄勇的29岁无业青年在家残忍杀害了数名男孩。11月13日,村干部跑到路德全家中,通知说乡长让他去乡里谈一谈孩子的事。突然受到乡长的重视,路德全知道孩子出事了。从高洋店往出事现场玉皇庙乡赶的路上,路碰到了另外几个孩子家长,陆续得到消息的其他家长也从全国各地回到了平舆。可到了凶手所在的曾庄村大黄庄,家属们被当地村干部堵在了门口,家长只能配合DNA检测,见不到孩子尸体。记者11月19日早上到达平舆时,微雨的内陆小城表面上看不到任何异样气息,经济的欠发达直接表现在临街两三层的破旧建筑上。农业大县里原本仅有的六个工厂近些年倒闭了一半,剩下的酒厂、纸厂与自行车厂效益也并不好。有意思的是,楼宇簇新的十几所学校反而成了县城里略显奢华的标志性建筑。当地百姓告诉记者,县城里除了在机关上班的“国家的人”,老百姓多靠租房给外地学生挣钱。从下面乡镇来打工的农民也多是开小店做学生生意,于是在壮劳力主要外出打工的平舆,几万名学生组成了主流的消费人群。而此次事件的20多名受害者中,学生也成了主要的犯罪目标。 平舆一高与二高在县城北面隔街相对,四周的民房、小饭馆全是以学生为消费对象;往南经过月旦桥,10分钟的步行路程便是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道——建设路、商业路、清河北街。2000年之前,县里仅有的两个溜冰场和清河闸是学生们聚集的娱乐聊天场所,而网吧近两三年的“入侵”几乎改变了平舆的娱乐业结构。在建设路上做了32年生意的余老头见证了网吧的兴起,“我们这条街不到50米的距离开了三个店,广告牌上写着玩通宵的价格,学生就没断过”。红火的生意使县城网吧大大小小达到50多个,“跟饭馆一样多”。 平舆一高是县里最好的高中,校长刘松林介绍说,“现有的3000多名学生中,农村学生占到了60%以上。”一个学生一年近5000元的消费在农村不是小数目,所以送孩子来读书的不会是种地的农民,而是“长年在外打工,经济条件在当地很不错的家庭”。按照学校规定,农村学生可以在学校免费住宿,但规定不是硬性的,因为“有很多孩子在当地有亲戚”。记者向学生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同学在外自己租房住的情况很普遍,一间房月租从20元到60元不等,基本负担得起。而被害学生韦雷、张昆仑、梁政威、秦继飞等正是一高的农村在校生,前三位在校外自己租房,分别于今年2月12日、3月5日、3月30日失踪。家在邻县的秦继飞住校,10月24日上课的时候被人叫走未归,成为最后一名遇难者。略为讽刺的是,家长和老师的首次接触是在事故之后对责任的争论中建立的。 面对发现孩子失踪后没有及时报警的指责,校长刘松林提醒记者注意县城高中的现实——农村家长基本在外打工,没有准确的联系方式。学校没法开家长会,而孩子的“失踪”对学校来说不是新鲜事。“有的孩子偷偷出去找父母了,有的自己打工去了,有的转学走了。”“学校跟企业一样,学生越多越好,我们当然不希望学生流失,因此很多学生转学是不通知学校的。”所以尽管学校规定连续4节旷课就开除,真正执行起来“很慎重”。张昆仑消失后,学校没法找到他在上海打工的父母,要求其亲戚代为询问。梁政威的父母在新疆打工,学校找到其爷爷,确定报案已经是孩子失踪第四天。家长们将矛头指向学校的“封闭管理”,学校称失踪的孩子共性为“成绩较差,有厌学情绪”,所以尽管学校不让学生上网吧,“出了校门我们也没办法”。松散的学校管理与疏远的子女关系使得孩子的个人生活是在失踪后进入家长与学校视野的,有的家长承认:“想着孩子能上一中就是好学生,每个月给500元生活费,平时他们跟谁交往我们也不知道。”学校则是“更多精力用在保证升学率的提高,差学生也就没那么注意”。 模糊的罪犯认知 平舆县不算大,可要找到认识凶手黄勇的人忽然间变得困难。知情者告诉记者,县里所有网吧在出事之后一夜间都关闭了,网吧老板各自散去,“这里开网吧的都是有关系的人,有的直接在县公安局、工商局上班,现在躲还躲不及呢”。记者晚上9点坐车沿中心区绕了一周,除了几个小规模的卡拉OK厅外,几乎见不到热闹场所。当地百姓介绍说:“比以前冷清了不止一半,以前到晚上12点网吧周围的地段都不能安宁,有学生也有社会青年,现在一个学生两个家长接送。” 但是黄勇案件一经曝光,震惊之余的人们立即把他与年初轰动县城的“双手案”联系了起来。在建设街做生意的余老头至今还清楚记得邻居与黄勇发生冲突的那天,黄勇打完电话不愿付钱,在IP电话超市门口叫骂,“个头不高的一个小伙子,看着像个学生,但是闹起来样子可狞了”。走的时候甩下一句话,“我是有杖头(靠山)的”。第三天清早(3月1日)超市门口放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两只手,信封上用米尺比划着写道“给店主”,里面还有一封信“奉手一只,借钱五百,将钱送到月旦桥车亭子底下,不送则后果自负”。这时距第五个学生韩鹏失踪仅两天,余老头感慨,“这人的报复心真强”。 县一高校长刘松林提到,当地公安机关曾到学校对失踪案件调查,但由于失踪的全是男学生,让人很难推测案犯的作案动机,“他各个击破,失踪的学生彼此之间不认识,一人出事不容易引起其他人注意”。而对于学生与社会青年的交往,一些学生告诉记者,他们并没有严密的组织,主要是在网吧酒桌上结交点朋友,遇到事情一起出头,而黄勇在这个圈子里几乎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色。 黄勇作案的隐秘性成为人们的另一个疑点,记者来到黄勇在大黄庄的家中,30多里的车程后还要步行5里多狭窄的土路。让人惊讶的是,黄勇的小院四周全是邻居,西头的一家与之共用一堵1米多高的围墙,其余几家的距离也不过一两米。记者扮成受害者家属,在其他家属陪同下进入村庄。黄勇家一字排开的四间砖房十分破旧,东屋地下发现了两个直径1米、深约1.5米的埋尸大窖,西屋地下的泥土全被公安部门翻找过,屋内臭味扑鼻。黄勇简陋的木板床上还放着一本同学录,翻开的一页正写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一整段祝词,三斗屉上还放着两瓶未喝完的“金星啤酒”。约一百多平方米的院子种着二十来棵小杨树,因为是埋尸地泥土全被翻动过。一些受害者家属形容,黄勇会记下每一个孩子的名字、作案日期,他的床下还有剪过的受害者照片,被挖去了头部或四肢。村子里的人提到,黄勇平时住在县城里,十天半月回来一次,一般都是在天黑时候,大家也没注意,只是确实发现“他老领着男孩子回来,没看见带出去”。 在作案现场的每点发现都成为推测凶手动机的凭证,记者见到一张受害者家属从黄勇抽屉里发现的日记纸,里面提到“我”和“亮”之间的冲突。受害人王亮的母亲推测黄勇将对王亮的谋杀过程形容成日记里主持节目的过程,认为黄勇有心理变态嫌疑。 而最后一位逃脱者张强显然是关于黄勇最权威的讲述者。记者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张强的家人,凶手至今被遮掩的真实面目成了这家人紧压心头的担忧。 生还者叙述:离真相有多远 11月22日傍晚,记者来到张强家略显简陋的客厅里。母亲秦翠莲(化名)皱着眉头,不时习惯性地竖起羽绒服衣领,将脸完全埋下去。天色渐暗,不一会儿将她淹没在夜色里,没意识到拉拉手边的灯绳,她反而将头埋得更深。 隔壁房间里,经过十来天治疗的孩子身体好了些,可由于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没法见生人。父亲张永刚(化名)从房里出来看了看记者,叹着气,又转身将房门带上,焦虑地坐到对面的条凳上。 县城的人都说张强“这孩儿命大”,忍受住了歹徒4天的折磨,成功报警后牵出惊天大案,“要不是他,还不知有多少孩子会受害呢”。头天(11月21日)的《新闻联播》播出了这宗17个男孩被害案的告破,凶手黄勇的缉拿归案给了受害者一个交代,可锁在张家人脸上的愁云似乎更重了些。“本来孩子捡回一命就是最大的安慰,但现在说不定哪天又会丢掉。” 让张家人担心的是,作为惟一活着的受害者,张强讲述出的信息让人怀疑案件远非个人变态行为那么简单。秦翠莲说,虽然没有问孩子过多的细节,但是相比于孩子因单纯而受骗,凶手背后的动机显然十分复杂,“他是有计划的”。 这种计划性首先体现在黄勇对张强行踪的掌握。16岁的张强已经随父母到60多公里外的驻马店市打工一年多,今年11月3日他第一次回平舆的家看奶奶,三天后张强与同镇男孩去网吧玩时“偶遇”了黄勇。同去男孩因与女友有约离开后,黄勇坐到了张强旁边的位置上。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但是主动搭话的黄勇与张强聊得十分投机,当黄提出自己钱不够用、要求张陪他一起去取时,张并无半点怀疑。离开网吧后,黄说必须回家取钱,便带张上了通往玉皇庙乡的公共汽车。张强事后向家人形容,“黄看上去非常斯文,谈话也不错,哪有一点凶残的样子?”黄温顺的外貌轻易获取了张的信任。 到了远在30多里地外的黄勇家中,黄首先自己躺到由轧面机改装的“魔椅”上,然后让张玩玩,张强躺上便被机器牢牢地卡住了手脚。秦翠莲分析到,黄是一个个头1.68~1.70米的瘦弱青年,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次次靠暴力得手,便用“魔椅”作为他控制人的工具。 张强接下来经历的正是每一个遇害者生前遭受的残害。四天里被勒晕过五次,晕死后用凉水泼醒,然后再勒;肚子上被针头戳出洞,用镊子挑,要让张“排血”。根据黄与张对话中透露的动机,秦翠莲推测黄勇的作案有集团性,黄提到“我杀一个人是有钱的”。张曾经问黄,“我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杀我?你不害怕杀人吗?”黄的回答是,“杀第一个的时候我也怕得好几夜没睡,慢慢就好了。”而张强几经折磨仍然存活后,黄说,“你的命真大。我的任务完成了,下一步就看你是否挺得过去了。”黄清楚地记得自己每一次作案的时间、对象,甚至对张提到:“这次是你,下一个就轮到某某了。” 至于最后黄居然放了张强,秦翠莲说是孩子的性格救了他自己,“他很老实的一个人,不会激怒别人。”于是只要有说话的机会,张就求黄放了自己。张最后的求情多少让黄动了恻隐之心,“我若死了我父母多难过呀,就像你突然被人杀死了,你的父母不伤心吗。”黄威胁张不准报警后放了他。张害怕黄的跟踪,当晚躲到同学家中。等第二天被同学送回家时,家人见到的张强已经“两个眼睛红得看不见眼珠,脖子上都是淤痕,肚子被针头扎得像个马蜂窝”。 对于是否要报案,张家人是有过犹疑的,这种犹疑在“破案”后的今天并没有消失。“黄勇确实被抓住了,可他杀人就是取乐那么简单吗?如果他的后面有一个团伙,谁来保障我们举报人的安全?”张强的父母一脸茫然。孩子逃回来后一直在改变行踪,不敢在某个医院连续住院。新闻上关于案件告破的提法更让一家人忧心,秦翠莲反复唠叨一句话是:“孩子好不容易捡回一命,就怕他哪天又丢掉。”张家人多次向县领导和公安局表示有情况要反映,但“他们一直说忙得顾不过来,一点安慰都没有”。于是“县里急着破案交差,我们就怕案子没完”。 声明:《三联生活周刊》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