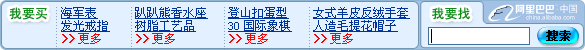| 女教师同居期间猝死 “约会强暴”应如何面对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15日18:00 观察与思考 | |||||||||
|
观察记者韩晓露 引子 2003年2月24日发生的一桩命案在网上引起了相当热烈而广泛的讨论。那就是湘潭女教师黄静猝死的案件。死者死亡的时候身上一丝不挂地躺在自己宿舍的床上。黄静死亡当夜
黄静死后,黄静的母亲为女儿四处奔走呼告,指认女儿的该男友强奸了女儿,并且不忍法官解剖女儿的尸体。该男友则有自己的说法,认为两人只是同居,并未施以强奸。黄静的案件一直没有定案。 这桩命案作为一个引子,引出本文论及的妇女问题研究专家们最近热烈讨论的一个新概念——“约会强暴”。 提出一个新概念 “约会强暴”,顾名思义,也就是在约会时发生的强暴行为。 这个全新的概念,有其特殊的涵义。因为有很多妇女曾经为此煎熬过,痛苦过。她们曾经因为有过类似的遭遇而遭人谴责甚至是亲人的奚落。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之后,受伤的往往是妇女,虽然错不在于她们,可是目前社会上的舆论往往会偏袒男人,使原本受伤的妇女遭遇更大的社会和精神压力。假如整个社会都能对这类事情持有正确的是非观,那么,受伤害的妇女也许会获得一种完全不同的对待,开始一种全新的人生。 记者曾经在采访中认识这样的一个女孩。她刚走出校门不久,年轻的脸上还带着稚气。但是记者和她在咖啡馆里坐下聊天的时候,女孩却泪流不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女孩如此的伤心,花样的年华却如此的神色暗淡。劝了半天,女孩才絮絮叨叨的告诉记者:不久之前女孩和一个大学同门师兄一起去酒吧玩。酒量甚好的师兄当晚就把女孩给灌醉了。然后把她带到自己的住宿处。等女孩第二天酒醒之后才发现,师兄一丝不挂地睡在自己旁边,而自己也什么都没有穿。她当即就尖叫了起来。被惊醒的师兄却冷言冷语地威胁她,说要是把事情说出去了,他倒是没什么,女孩子自己却要被人说成是犯贱。女孩不相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最要好的大学女同学。事情果然如师兄所言,女同学不仅不同情她,还笑她老土。而且更不曾料到的是这件事情被她男朋友知道后,两人大吵一场,男友还骂她不贞洁,并且从此和她断绝往来。她真是哑巴吃黄连,现在的处境苦不堪言。 其实,女孩的遭遇就是一种典型的约会强暴。 妇女问题研究专家王金玲教授告诉记者:就约会本身而言,确是双方自愿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约会过程中,双方之间发生的任何行为都是自愿。也就是说,在约会过程中,会发生有违一方意愿的事情。而无论从道德层面来讲还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当一方已表示不愿意,另一方却强行实施自己的意愿,这就是对人权的侵犯。由此,约会强暴是一种“罪行”,约会强暴的实施是一种“犯罪”,约会强暴应该遭到社会谴责,受到法律惩处。但是事实上的情况往往是,约会强暴的实施者不会受到任何惩治和谴责,而约会强暴的受害者,尤其是妇女却遭遇了社会的谴责。这其实是侵犯女性权利的一种表现。 亲密关系之下的暴行 王教授告诉记者:在现实生活中,从实际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不少约会强暴的现象。如果约会的一方只愿意局限于精神层面上的交往,而不愿意产生性行为,而另一方不顾对方的意愿,强行进行性交往,这就属于强暴的范围之内了。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性强暴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的两个人之间,尤其是在热恋者之间的性行为,不会是强暴行为。由此,一旦约会强暴事件被暴光,人们往往会持怀疑态度,舆论往往会很微妙地出现对女方不利的倾向,女方更容易受到各种的谴责。这些谴责有的是对女方不守贞操的责难,比如有很多人会说女方“是自找的”,“自己不自重”,甚至更严重的认为“女方自己犯贱,勾引男方,是个坏女人”;有的却是对女方反抗暴力的嘲笑——当有的妇女由于反抗约会强暴而受到对方的暴力伤害时,有的人就会说“如果她愿意和他玩,不就没事了吗?”处在这一双重压力下,受到约会强暴的妇女往往或处于别人的冷眼中,或只能自己默默地吞咽苦果,承受着巨大的身心痛苦。 所以,我们应该从更为广度的人权的视角来审视约会强暴,认识到这不仅仅是“将应该在婚床上进行的事移到了婚床外做”的违背婚姻道德的事,更是对对方人身权利的侵犯,对对方身体和心理的侵害,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文化意义上的探讨 王金玲教授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对约会强暴进行探讨。 从约会强暴的事实看,更多地表现为男人是强暴者,女人是被强暴者,即,男人更多地认为自己拥有占有对女人的权力,更多地实施这一权力。这可以从“男强女弱”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原因所在。在“男强女弱”的文化规定中,男人必须是强者,必须表现为强者,男人必然和必须拥有强权,社会也更多地要求和容许男人实施强权。于是,即使是在与恋人的温情脉脉的约会中,暴力也难免会在一些时候掀起它的盖头。 一旦约会强暴被暴光,社会舆论往往更习惯于开脱男方,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正常的;而更倾向于责怪女方,认为她才是首恶者,尤其是恋人之间的约会强暴更是如此。这种将男人的犯罪正常化、将妇女的受害罪恶化的现象,可以追溯到“男宽女严”的性道德双重标准。在这一更多地宽容男人的“失贞”,更多地要求妇女“守贞”的规定下,社会难免更倾向于容许男人非婚性行为,而对妇女的非婚性行为进行严惩。于是,只要是受到了性强暴,即使是被陌生人性强暴,即使是拼命反抗了,妇女也难逃被他人指责,也难逃自我责难。 王教授认为,事实上,包括约会强暴在内的性强暴对受害人造成的伤害是双重的:一方面身体上受摧残的,另一方面心灵上受打击。而由于在约会中被强暴的妇女往往更处于无处诉说,甚至难以诉说之中,约会强暴对妇女身心理上造成的伤害更严重。 要减轻包括约会强暴在内的强暴对妇女身心的伤害,要使妇女走出被强暴的阴影,我们就必须挑战这一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文化制度,使男女获得平等的对待。 被强奸是否比被抢劫更可怕 网上曾经流传着这么一则故事:有个农妇拎着一篮鸡蛋去城里赶集,路上遇见了一男人。农妇捂紧篮子连连后退,两膝发软,心里打颤。事后,农妇掸掸身上的尘土,说:“咳,原来是这事,俺还以为是抢鸡蛋呢”。 网上是把这个故事当成笑话来讲的,笑农妇的愚昧,把抢劫看得比强奸更可怕。但是,为什么对女人来说,强奸比抢劫更可怕,甚至被认为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对女人来说,失去贞操就往往意味着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为什么对女人来说,处女膜的价值有时会高于生命的价值?在回答了这些为什么后,也许我们会对这则笑话有一种新的看法。 王教授告诉记者,在男权传统文化中,妇女的身体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某个男人,妇女对于自己的身体只具有托管权。当妇女的身体遭受暴力,尤其是性暴力时,如果施暴者不是妇女身体的主人,那么,对这一强暴对该主人来说,就意味着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财产的公然抢夺,是对他财产权和尊严的严重侵犯;对被强暴的妇女来说,则意味着她没有照管好丈夫(包括未来丈夫)乃至夫家(包括未来夫家)的财产,这是一种严重的失职。既然这一严重失职对主人的财产和尊严都造成了严重损失,那么,社会对失职者的谴责直至惩罚、失职者的自我谴责直至自我惩罚也就是失职者的“罪有应得”了——从物质到精神,被强暴的妇女都会处于无地自容的境地。而这也是约会强暴、婚内强奸不被认为是一种犯罪的原因所在——施暴者被认为是妇女身体的主人,这一暴力便成为财产主人对财产托管者应有的权利,财产托管者对财产主人应尽的义务。在今天,尽管妇女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正不断获得认同,但男权文化的惯性势力依然是强大的,并且,妇女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也只是确认“财产就在妇女身上”或“妇女自己就是财产”,即,妇女的身体仍是财产,只不过财产的拥有者发生了变化。由此,妇女的被强奸在被认为是托管者的失职的同时,也被认为是财产拥有者的失职——“贞操”的丧失就更意味着自我的丧失。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非夫妻(包括恋人)间,尤其是陌生人间的性暴力犯罪才从暴力犯罪中分离出来,被命名为“强奸”;被“强奸”的妇女除了身体的痛苦外,更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强奸犯罪被确认为一大恶性犯罪。而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强奸对妇女的心理和精神伤害——对妇女来说,强奸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妇女往往生活在被强奸的恐惧之中。 妇女之所以恐惧被强奸,与其说是害怕身体受伤害,远不如说是害怕被强奸后会处于社会的不公正对待之中,受到他人的非难、谴责乃至惩罚。而这一恐惧的存在以及社会对妇女相对于男人来说更容易遭遇强奸的担虑,已成为今天妇女的发展空间较小、发展机会较少、更多地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影响了妇女的发展。 把强奸吓得魂飞魄散 一直有许多的忠告告诫妇女该如何避免被强奸,在遭遇强奸后该怎么办。但是,即使在今天,几乎所有的忠告都在重复着男权文化的话语,复制着性别双重标准,强化了妇女对强奸的恐惧。比如,告诫妇女不要穿着太露的忠告,实际上是指认妇女应该对强奸犯罪的发生承担首要责任,妇女是“首恶者”;告诫妇女夜晚最好不要外出的忠告,实际上暗示着男人对妇女暴力伤害的权利和力量,缩减了妇女的活动空间和发展机会。 王教授认为,在今天,要使妇女真正摆脱强奸伤害,脱离强奸阴影,最有效的应是冲破男权文化的束缚,看到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让自己成为战斗者,让自己的身体成为战斗的身体。这其中包括: 1)不再认为贞操高于自己的生命,将强奸视为一般犯罪——比如,抢鸡蛋; 2)认识到强奸犯罪更多地是针对弱者而不是针对强者的犯罪行为,即相比较而言,强奸犯较少会对强者产生强奸的念头,较少会对其认为会进行强力反击者实施强奸; 3)必要时也成为“暴力”主体,使不怀好意男人认识到他/他们如果对妇女实施暴力,那么,妇女也同样可以对他/他们实施暴力。 总之,要消除妇女对强奸的恐惧,要建设一个没有强奸恐惧的社会,我们首先必须把强奸吓得魂飞魄散。 尾音 关于“约会强暴”以及相关的妇女权力问题,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有更深的研究。以下是记者对艾晓明教授的言论整理,以及采访记录。在此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实际上中国刑法在强奸定罪这一点上是具有先进性的,它强调了强奸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为特征。但是有关刑法名词的解释却反映了男权思想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刑事档案公司”的网站上,对于强奸的解释即为:“本罪侵犯的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又称贞操权)”,这个“贞操权”的说法,就带有封建男权思想色彩。因为贞操是封建社会男性对妇女身体提出的要求,要求妇女为了某个男性特有的性权利而坚守自己的性(不失身、不改嫁,是为贞操;为保贞操宁死不从,是为节烈,可立贞节牌坊。)要强调妇女自己支配身体的权利,说明“妇女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性行为”,原本已经足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行动纲领》就把针对妇女的暴力确立为十二各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反暴力也是妇女运动持续的努力,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个目标终于成为了国际人权领域的重要关注,对妇女的施暴被看作对妇女人权的侵犯。 ——妇女战胜暴力这个口号强调了妇女的主体性、能动性。它不是那种“给妇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或者“为妇女撑起一片蓝天”的说法;在后者,妇女的人权不是与生俱来的,仿佛是被恩赐的、被赋予的;所以需要别人来“给”、“为”她们做事。我坚信的是,妇女是人,每个妇女都有人的权利,她们有尊严、有权利、也有强大的解放自己的能力。假如说妇女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那不是妇女本身弱,而是男权控制和压迫的结果。妇女的人权不需要论证,如果我们说给男人人权吧,肯定有人说你废话,我天生就有这个权利,还要你来废话吗?那么对妇女也应作如是观。妇女天生有人权,这个权利不需要赋予,不需要恩赐,不需要论证,是彻底的、纯粹的、普遍的,无论妇女的阶级、种族、职业、宗教、财产、年龄、面貌、身体、性取向如何,她的权利与任何人的权利一样,是平等的。那么当我们说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时,口号不应该是把妇女界定为弱者、等待别人来保护的、被动的主体,我认同这个“妇女战胜暴力”的理念,原因就在这里。 ——您感觉女性意识有没有在中国女性身上觉醒?妇女节到来之际,可否对中国女性说点什么? 你说的女性意识,你有你的意思,我可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一回事。让我换一个说法吧,咱们说“性别平等意识”好不好?你要我就中国女性而言,这个范围太大,我无从说起。女性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女性中有很多差异,有不同阶级、职业、年龄、性取向等,各自在经济结构中的处境也不同。对性别平等和平等权利的认识,不可能都是一样的。而且,男权中心的传统那么深厚,靠什么?当然也靠从文化、意识形态上控制女性的身体、思想,不让她们认识到自己的受压迫地位。所以,所谓觉悟、“性别平等意识”,我们不能做一个泛泛的定论,只能就具体事情来说。要不你自己去看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有关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报告,或者看我们国家给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报告好了。 我要说的话:立法消除歧视,维护妇女权利!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