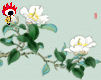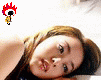| 刘树勇: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声音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08日15:20 中国“幸福工程”组委会 | |||||||||
|
于全兴历时一年有余,为“幸福工程”拍下的这些图像,对于记录这项功德无量的救助计划的实施状况,其无可替代的价值,不用我来多说。我感兴趣的,一方面是,作为一项重要的图像记录活动,一开始便有该基金会列入计划并出资组织专业摄影师付诸实施,且历时达一年之久,这在国内尚不多见。我想此项富有建设性的工作后面,定有明眼高人,看到了图像记录及传播的长远价值。过去看到美国FSA小组的工作,大为叹服。倒不是因为那些了不起的摄影家,而是因为这项计划的运作方式。如有更多的官员认识到这种工作的价值,这种
当然,从摄影的角度说,我更关心的是于全兴所使用的图像方式。2001年春,当于全兴带着他用135的小相机拍回的第一批报道式的图片回到北京,急切地印出小样摆在冬平、京涛、星明和我的面前时,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全兴胡子拉茬面带倦容,用很快的语速不住地说着这一趟下去的所见与他的震惊:那些穷困得我们难以想象的母亲们;那些竟然从未见过糖果为何物的孩子们;那些穴居的家庭;那些离我们很远的地方的人们的饥馑、旷野里凛冽的风、积雪和寒冷。我们看着摊在我们面前那些尽可能悲壮的、但又拍摄的匆匆忙忙的图像,我们知道他为一种无法抑制的情绪引领着走得太远了。他已经方寸大乱,忘记了此行的目的。他只顾去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到那些穷困的人们手中;他只顾激动、难过、甚至陷于深切的怜悯和伤感之中不能自拔。可是那些图片呢?作为一个肩荷了重任的摄影师,拍回来的那些支离破碎的图像仿佛一些散碎无序的句子,它们尽管光芒闪烁、但却急切焦燥语焉不详。它们只是零乱地堆集在一起,让我们无从看到这样一个大的救助工程之下的那些贫困母亲们的真实状态,同时我们也无从感知他的那些激动从何而来。 采集到一组好的图像难道真的需要你置身事外,冷漠、近于残酷地打量他人的贫困或者不幸?京涛他们从心境、技术、方法各个方面和他交换着意见,我坐在一边想着这些没有答案的老旧问题。此后的一段日子里,全兴在家埋头做案头工作。它与许多身边的朋友交流,也跑北京来一边涮羊肉一边听我们几个朋友给他出的馊主意。这个吧那个吧,一大堆,我真怕大家伙儿把他搞糊涂了。与我同龄的全兴拿个小本儿,一个劲儿地写写画画,记着别人的喝多了之后的说法。眼神中那种孩子一样的单纯和干净,让我想到小时候在一起玩尿泥时的童年伙伴儿。过些时日,话说得差不多了,见他仿佛有了主意,然后就见他紧着忙活买大机器。再然后,在机场打个电话来,说,我走了。就走了。 回来的全兴神色平静。我们倒没有太当回事儿,因为心中没底。说是到东营去找京涛过来一起看看,开车就去了。照片放在后备箱里,车在空旷的荒地公路上开成了风。在《东营日报》黄利平兄的办公室里凑齐了,将一大摞小样一一摊开来──也有一些是135相机拍的──看着,一伙人禁不住就高兴地骂起来,知道是成了。纷纷挑好的,争执,都有一套说辞,各不相让,全兴一脸的孩子笑,那个高兴啊。晚上,我们都喝得差不多了。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一种说话的方式,对于全兴来说这才是最最重要的。那些135相机拍的图片被大家放到一边──较头一趟去拍得已经好得多了,但与这些120机器拍的图片放在一起,依然是弱。我在一旁看到,这倒不是因为这一伙人心存偏见。没有哪个人更加迷恋方画幅的图像而排斥其它。 严格地说来,在一般的状态下,没有哪种言说的方式是对的和好的,就像你不能说哪种色彩是好和不好的一样。但是,具体到某一个画家和歌手,那些色彩和声音会因为他的好恶和习惯(风格?)而呈现为一种取舍──他会偏爱某种色系和声音去表达他要表达的东西,同时他会觉得换一种色彩或声音会造成表达的障碍。仿佛两种声音在讲述同样一件事,对于全兴这个摄影师个体而言,不仅他意识到、而且大家也看到了,那种方形的图像较他使用另一种图像语言,表达得更为准确丰富,也更宽阔厚实得多。 由此我想到,全兴也许就不适合去以一种新闻报道式的图像语言来呈现这样一个“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换一个人,也许可以?我不知道。数年前编辑《中国故事》一书时,尚不认识全兴。全兴寄来两组他早些年作摄影记者时拍的有关天津一所福利院收养残疾儿童的图片故事,图像与大家所作无异,没有什么特别之外。做得好的倒是他的文字,详尽而丰富,把事儿都说明白了,真是好用。何以在他来说,通过这种135相机拍下的图片就不能表达得更充分一些呢?我想不出原因出自何处。我甚至想到了这可能是全兴在天津美院受过专业绘画训练的原因。绘画的那种关注静态图像的手工制作,那种在画布上的考究和经营,与方画幅的取景状态更为接近。但这仅只是手段上的相似,更重要的在于,就像绘画的一个画面一样,每一个画面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视觉系统。画布中的物象无论是面对现实物象的写生(这更近于摄影的图像采集),还是想象的场景制造──即使是有关运动的描绘,它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图像系统。或者说它即是一“物”,是一个自在、自足、自为的图像实体。无论是它来自现实之象(如具象绘画或者是摄影),还是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创造之物(如冷抽象艺术),它都在最后的图像状态时割断了与现实的实在联系。它不再向两侧延伸,不需要那种与无限时空的持续关联。于是图像的内涵开始深向图像本身的领域,而不再是依赖它所描绘的外部世界物象。这样的图像便可以获得一种自主的生命。它可以被你独立地观看,它亦可以在静默之中对你长久的凝视──你注意到那些母亲的造像对你的凝视吗?你一幅幅看去,每一幅图像之间并无关连,每一幅图像都不再需要解释,不需要背景,不需要一旁的图像在那里不住地对你进行提醒和佐证。每一幅图像都是一个单元,就像是一个深邃的空洞,它向图像的背后延伸而不是向两边。它吸纳着你的注视,它注视着你的注视。你深入其中,极力穷尽其奥秘。然后,抽身出来,移动脚步,再陷入另一个空洞之中。 所以,于全兴不是在报道,而是在记录。尽管历时一年的时间对于那些长于报道摄影的摄影记者来说,足以成就一系列的图片故事,尽管沿途的所见所闻足以做成一个系列追踪式的报道,但是他却不善于这种线性的叙事方式,不擅长那种对动态的物像进行捕获的方法,更不善于把照片拍成那种开放式的互为因果关系的连续不断的图像群。当他感到那种仅止于“知道”和“告知他人”的图像采集方式不足以表达他对这个专题的更为复杂和丰富的领悟时,他便放弃了这种报道的企图,并且很快地转为一种探究式的凝视。他凝视一个点,他企图使这个点从时空当中分离出来,静止在那里。他想深入这个点,它尽可能平静下来端详(而不是像刚开始时那些冲动地通过身体和镜头掠过)那些身处在自己生存环境中的母亲,意欲通过营造一幅完整的图像──就像画完一幅画那样,主要形体的位置,空间的比例,边边角角都收拾到了。那些与此对象的生存状况相关的符号:她们的孩子,她们的屋舍和家什,她们的田园和庄稼,在这个方形的画布上被组织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最后结合为一个封闭的构成。这些符号成为图像的肌理,同时也成为主体的一个内涵支持,它们不仅仅在图像中表达着自己,同时也以一种隐喻的甚至是象征的方式,使图像的主体内涵变得较为暖昧和丰富,以告知我们更多的东西。就像画布上那些似乎漫不经心的涂抹留下的痕迹一样,它不表达什么,但整个图像因为这些痕迹而变得丰富和隽永。──然后,他慢慢地离开,再去经营另一个画面。 他把叙事和图像本身的经营划分开来,他把叙事的功能单纯地让给了文字。整个“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的运作计划和基本原则,地方政府在具体实施这一救助计划时的运作过程,贫困母亲们的生存状况的真实细节,由贫困到脱贫这一变化的一系列数据,万水千山走遍的那种难以描述的丰富感受,成为与这一图像群平等存在的一条潜在的河流。文字可以洞穿图像而进入图像本身所无法企及的领域这一优势,与图像可以直接显现的力量结合于一体,近年来已经为越来越多的摄影师所重视。但是,如何将这种关系处理得更单纯,文字的叙事更充分和完整,图像更具有内在的丰富性和力度,却一直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不信,你注意一下通过媒体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的那些数量巨大的图像,在简单地告知我们一些即时的信息之后,便从我们的记忆当中永远地消失了。 因此,我有理由在看了他拍的成千上万张图片和大量文字之后──而不是因为这个过程的不易和他吃了多少苦──敬服他所做的工作,并且喜欢他这些内涵丰富的图像。我有幸看到了于全兴在放下相机近十年之后,重操旧业,造得这一批打动于我的图像的整个过程。其中艰辛、犹疑、颓唐乃至无奈,自不必说,因为最后的图像从不因你这过程的不易而被人格外地看重或者宽恕,图像的评价系统也从不会把背后发生的一切作为一个参照之物。我想,作为一个值得注意的个案,这个运作过程本身对摄影者所提供的有价值的启示之一就在于:一个摄影家,如何找到一种对于自己来说最为流畅的语言,以进行自由的言说。这种语言不再是外在于你的头脑和表达,也不再受到那些所谓经典的摄影理论说辞的指摘和左右。在它的最佳状态里,它应该成为你机体的一部分,在这一时刻,摄影便成为你身体和心灵的一种自由的移动。 这个状态真是令人神往。于全兴后来频繁地到各地去拍照,陆续带回来的照片越来越好,“幸福工程”的图像记录渐渐显出轮廓,文字也大致齐全了。再见到全兴时,已是一种心中有底的表情,依然孩子一样笑着,用道地的天津话说是,“咱做个展览吧?”于是,2002年5月12日,母亲节这天,这个工程的一部分图像以“母亲”之名在北京三联书店旁边的“大众影廊”展出。我去时,在门口看到他,怀里抱着三百支粉白色的康乃馨花。 2002年5月 北京 相关专题:中国“幸福工程”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中国“幸福工程”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