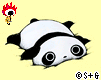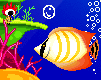| 中国职业试药人群体大揭秘:医学院学生最受欢迎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04日20:59 东方网 | ||||||||||
|
不过,在中国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数量相当可观的群体——职业试药人,即便是风险最大的一期临床试验,他们也愿意参加,为的就是可观的报酬。然而据媒体公开的报道称:中国临床试验成本低廉。一方面,在中国招募同等水平的科研人员,报酬比欧美国家至少低一半,另一方面付给中国受试者的报酬一般只有几十上百元的差旅费和误工费,发生事故的补偿也相当低。而在美国,一个试验对象获得的报酬往往在几百甚至几千美元,一旦引发纠纷,赔偿金额更是高昂。据业内人士估计,中国临床试验的费用比美国至少要低三分之一。
目前中国的职业“试药人”的构成较为复杂,但基本上由学生、医护人员和社会无职业者组成。而其中医护人员与学生是药物一期临床试验的主力军。 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药理基地的蒋萌主任介绍,药品的一期临床试验是一种特别的试验,试验对象不是病人而是健康人。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新药的药理、药性和合理的药剂量。有更多人参加试验,对药物的副作用了解肯定会更加深入。考虑到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国内的一期临床实验试药者一般不公开招募,主要在医学院校的研究人员和本科生中招募。 在一些高校尤其是医学高校校园里的布告栏上,经常会看到一些招募学生志愿“受试者”的启事。相对利用社会型的职业“试药人”而言,医药厂商与研究机构更倾向于利用高校的学生,因为学生无论是文化素质还是身体健康状态都更符合要求。并且学生大多无不良嗜好,这对临床试验的质量和结果都非常有益。另一方面,利用医学机构提供的“有偿”试验机会来缓解自己经济压力,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学生“试药人”的想法。 除了学生之外,由医护人员构成的“试药人”群体显得尤为特殊。医护人员懂得新药物的药性,以及它有可能带来的其他副作用,所以大部分的第一期试验都是由医护人士完成的,当然大多是有偿的。不过遇到一些药性很烈的新药,医院及医学机构还是要将临床试验转给社会的职业试药人。 而中国目前每年有800多种新药进行人体试验,每种药需要30名左右的健壮人员试药,基本是国外新药为主。 一个试药者的亲身经历 记者费了一番周折,找到了一位学生“试药人”。这位姓李的同学来自南京某医学高校,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第一次”完全是因为手头紧、凑热闹。“我是在学校保健室的公布栏中看到了招募‘试药志愿者’的公告的。平时就听周围试过药的同学讲对身体没什么影响,酬劳蛮高的。正好当时手头有点紧就报名参加了。报名的人多着呢,队伍排了好长! “第一次试药,虽然听别人说没什么,可是心里还是有些怕。但试过以后就发现真的没什么,就是会有些头晕、恶心、腹泻的症状,过一会就没事了。一般做过第一次,自己感觉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就会做第二次,第三次……但是出于健康考虑,我多少还是有些心理压力,所以大学3年来我只做过两三次。当然,也有同学成为那种职业试药者,一年会参加四五次或者更多的试验。” “参加药物临床试验有什么特殊要求呢?”“一期临床试验仅要求是身体健康的人。一般我们报名后,医院会给我们进行一次体检:从B超、胸片、心电图、到肝肾功能、尿常规再到体重、血压,完了后我们就等通知。为了配合试验,试验期间我们不能吸烟、喝酒,甚至不能喝咖啡等饮料。有些试验还要求志愿者必须在临床观察室内活动,服从医院的安排,不得随意离开。 “为了不耽误学习,我们一般只在周末或节假日去指定的医院。我试的主要是抗高血压的药物,药性算很平和的,没什么大的副作用。我的报酬是按针数算的,打一针30块钱,一般要打20—30针,就有600—900块的收入。也有学生参加那种为期一两个月的实验,能拿1000—2000块钱。试验方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要求,我们只要按时完成实验就可以了。” “难道从来没有担心后怕过吗?” “后怕?当然也有过。”他笑笑说,“参加这样的实验,首先要确定的肯定是安全能得到保障。不过我们毕竟自己就是学医的嘛,知道能够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均是完成了动物实验、毒性实验等临床前环节,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已证明了80%。再说,在校内招募志愿者的临床试验一般都经过学校的过滤,药物的危害性更小,试验的风险系数更低。像我试的抗高血压的药物是中药制剂,药物本身的危害性不大,副作用很大的实验我也不会去做的。像抗肿瘤之类的药毒性比较大,国家有规定,是不允许在健康人身上做的,相信学校也不可能公开招募学生试这样的药。尤其是听说北京地坛医院的事情以后,我基本上不参与外国药商的医药临床试验了。不过也有同学胆子大,为了挣到更多的钱,自己跑到外面联系参加药物试验。” “学生中很流行做试药人吗?” “医学院参加这种试药的人多得很呢!我们班共有19个男生,有十来个参加了药物实验。没参加的可能是没得到消息。一般试药的志愿者只招男生,女生要得很少。可能是男孩子的抵抗力比较强,血管比较粗吧!” 当记者问及这位同学是否了解有关保护试药者的法规时,他一笑置之,“我们对实验的安全性很放心。还没听说过谁因此出过什么事,不清楚也觉得没必要去管这方面的知识。”据记者调查,参加试药的人对此都很保密,特别是对家里人。在一些城市药物临床实验一般在医科类院校自己就能消化,很少向非医科的大专院校寻求。 “不过,要说学生成为试药者的目的百分百是为了钱就偏颇了!”蒋萌如是解释医学院学生积极参与试药的原因,“当然,报酬是原因之一,但是参与到这样的实验中能积累一定的临床医学科研知识也是重要原因。许多医学院的学生是基于这两点考虑才参与实验的。” 隐秘的“中间人” 药物的二、三期临床试验通常在相关的病人身上展开,而不少经济拮据的病人或者绝症患者就会借此寻找一线希望。 记者和一位姓梁的试药者取得了联系。梁先生因为患胃癌在住院治疗期间接受过试药。目前,他仍靠大量药物和放化疗来控制病情。他说,之所以当试药人,一是可以拿一些报酬,二是指望给疾病治疗带来转机。 去年9月,在他住院期间,有医生和他商量是否愿意接受一种进口免费新药治疗,结果遭全家人反对。但梁先生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条件,医这病已经欠了许多债,孩子还要上学等等,决定参与试药。反正自己服用了大量药物,放化疗都没有收到什么明显的效果,可以说是“无药可医”了,试试新药说不定还能有康复的希望。“都得这病了,还在乎头晕、失眠这些小小的副作用吗?” 梁先生告诉记者:“虽然试药者本人都是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但大多数试药者都不愿曝光,一方面是隐私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们在情感上很难接受人体实验。医院会替试药人保密,在试药档案中我的名字都是使用代号。” 但像上述的学生、医护人员以及梁先生这样的重症病人也只是中国试药群体中的一部分。据悉,目前国内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试药群体,组织严密。 一名知情的试药者透露,除了直接与进行试验医院取得联系,也有不少“试药人”是要靠“中间人”进行“牵线搭桥”才能进入这个领域,尤其是一些不便公开招募志愿者的药物临床试验。“中间人”有的是以注册公司的方式,有的是独立地与临床试验项目的负责人揽活。因为“中间人”握有相对稳定的“试药人”资源,又与医院的一些负责人关系比较熟,医院为了省事,也经常委托这些“中间人”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寻找“试药人”。 “中间人”的加入使得原本较为简单的试药变得更加神秘。据说,有时候没有“中间人”的介绍,医院就不接受社会上零散的“试药人”。而一些职业试药人为了保证有钱挣,就不得不去与这些“中间人”搞好关系。不过,“中间人”虽然能够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项目来源,但他们的提成比率也比较高,一般是20%—30%之间,有的项目还高达40%。因此试药人经常会与“中间人”在提成比例问题上发生矛盾,有时到大动拳脚的地步。 无知村民被骗试药致死 更让人震惊的是,一些国外医药企业与国内机构相互勾结,严重违背生命伦理,有的医院以药物治疗的名义对患者进行试药,患者并不知情,得不到任何补偿与保障。“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新药试验事件”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去年3月5日至11月2日,共有39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选中参加北京地坛医院“胸腺核蛋白制剂(英文缩写为TNP)”药物试验。来自河南的36名试药者中死亡7人。直到今天,对于河南双庙村的部分村民来说,地坛医院那段长达3个月的经历,仿佛噩梦一般。 李秀萍,一名普通的河南妇女,艾滋病毒携带者。她是这次试药事件中的幸存者。2003年3月5日,李秀萍与其他38名感染者分别与北京地坛医院签订了一份带有许多英文单词的《患者知情同意书》。在签字之前,传染病区负责人向所有的感染者保证胸腺核蛋白好得很,可以延长生命,至少20年没有问题。 但是在临床试验进行到第7天时,李秀萍便觉得效果“不理想”。她说,针剂还没有用到一半的时间,其体质迅速下降。在试验期间,经常高烧,除此之外,还经常出现一些腹泻、皮疹、口腔溃疡等各种不良反应,CD4免疫功能指标降到了60。医院对此的解释是:“这种药是先杀艾滋病毒,杀完了之后,免疫力便自然上升。” 但李秀萍还是偷偷服用了四次丈夫买的抗菌药物,之后效果明显,身体立刻好转。正是这些抗菌药救了她的命。但是自参加完这次药物临床试验后,李秀萍还是明显感觉得到自己的免疫能力骤然下降,原来还可以干一些轻松省力的农活,现在连走几步路都喘不过气来。 相比李秀萍,从中间挤进去的感染者朱茂龙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为了“能延长寿命20年”,以向医院做出“打针打死人不负责”的承诺而获得了“治疗机会”,而且他还不能享受路费与伙食补助。然而他没料到的是这次治疗竟成了他生命的终结。 在试验之前,他的身体状况还是好好的,可当他用了针剂后的第二天,出现感冒、发高烧等多种症状。医院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便让他回家。回到家后不久,他的身体又开始恢复,这时医院看他身体恢复了,让他将“TNP”针剂带到家里自己打,可惜带回家的七针还没有用完就死了。据说在试验期间,他一直发高烧,不能吃东西,只能喝凉水。 “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新药试验事件”被媒体公之于众后,中国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在2004年4月中旬公开声明,胸腺核蛋白制剂的临床试验从未经过国家药监局批准,是违法的。 “试药人”的权益保障棘手 9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药品临床试验规范指导原则》并向各国推荐。1998年3月我国参照这一原则制定了《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试行),1999年底修改后的《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正式颁布,2003年9月1日又重新改版,更名为《药物临床试验治疗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改版的《规范》从三个方面来加强对“试药人”权益的保护:一是强调了《赫尔辛基宣言》的原则;二是明确了受试者应对有关临床试验的情况享有知情权;三是规定了研究单位必须成立伦理委员会。新《规范》明确提出“受试者的权益、安全和健康必须高于对科学和社会利益的考虑”,要求伦理委员会“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制度;必须“定期审查临床试验进行中受试者的风险程度”;明确规定“研究者在临床试验过程中,不得向受试者收取试验用药所需的费用”。新规范还明确,“受试者参加试验应是自愿的,而且有权在试验的任何阶段随时退出试验而不会遭到歧视或报复……如发生与试验相关的损害时,受试者可以获得治疗和相应的补偿”。 尽管如此,“试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事件仍不鲜见,其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主要是知情同意、实验中对受试者的保护和意外伤害的赔偿等问题。1999年的葛长荣诉北京某医院的在体检过程中做“人体测试”的案例就证实了这点。葛长荣在体检到神经科时被要求多做一项检查,测试后出现严重失眠、情绪激动和烦躁不安等症状。与医院交涉后,医院付给葛5000元作为一次性精神补偿费。后因后期治疗问题双方未达成一致,葛于1999年4月起诉医院,最后葛败诉。 此案例说明的问题很多,主要的是未在测试前取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对受试者缺乏应有的尊重。早几年,研究人员只是征得受试者的口头同意,没有任何的书面协议。而近几年,按规定研究者都要与受试者签订知情同意书,研究者必须把试验药品的安全性、治疗效果和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告诉患者,让他们选择。即使同意受试的患者,也有机会中途退出。但对于试药人来讲,他们往往对相关知识一知半解,将信将疑,知情同意书流于形式,关键的时候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出事之后也大多只能自己承担。他们能做的只是期望“不要出什么事”,可谁又能保证这一点呢? 这里就隐藏着更深一层次的问题:我国在人体实验方面实验者本身的头脑中还没有形成规范的意识,试药人与临床项目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为了平衡这种不对称,《规范》要求按国际惯例而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对试验方案、受试者的入选方法、试验的风险程度以及受试者因试验而受到损害后的治疗或保险措施等进行审查。而这一团队一般由具备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师主事,辅以5—10名成员。并且有非医药相关专业的代表、法律专家和其他单位的人士,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试验的客观公正,避免试验朝着有利于申办方药厂的方向进行。但由于该委员会常常与项目研究人员具有行政或业务关系,不仅很难做到利益超脱,甚至还有“合谋”的情况发生,因而试药者权益的切实保护往往需要经过一定的抗争。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