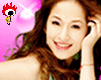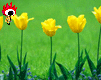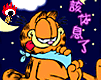| 新民周刊:被脱掉的脏衣服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11日09:56 新民周刊 | |||||||||
|
撰稿/边 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默东森林是从我们家开车出去十来分钟就可以到的一片栗树林,在巴黎西南角。秋天,树叶变得金黄时,我们常去那里,捡栗子。与森林紧挨着的默东镇,在一个高地上,可以俯瞰巴黎。这是巴黎周围星罗棋布的小镇之一,除了地势略高,可以远眺这一优势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那时秋天来捡栗子,春天来看看新绿,冬天偶尔也会来,看失去叶子的枝叉高高地在天上绘出任何画家都提供不了的图案。然而这只是我的旅程,我内心版图上的一条线,与他人无关。默东镇里那些人的生命旅程,只和我的偶尔交汇一下,甚至都是觉察不出来的,我们常常在这样的状态下,可以生活很久,我称之为各行其路。 1961年夏天在这里发生过一件事。这一年7月4日是个星期二,天空下着细雨,默东镇应该不完全是现在这个样子。早晨8点45分,位于镇子主干道卫士路25号的马伊杜别墅里送出了一具橡木棺材,后面跟着十几个人。一行人在雨丝中向位于更高处的“默东—美景墓地”走去。 近半个世纪后,我走的路线正相反,我先到“默东—美景墓地”。自从我带了“目的”来探访,我过去那些“无辜”的漫步,便都好像被贴了标签,冥冥中与那个人牵扯上了。 葬礼中的天意 路易-费迪南·塞林纳这个作家,原本在写《一支沉没的舰队》时,是想一并放进去的,但写到最后,觉得放进去怎么写都不谐调。这不但因为他在二战末期逃得比兔子还快,盟军未到就先逃离巴黎,德国未被攻下来,又逃往丹麦,一心只想保命。现在回头看,以战争刚结束时那喷发的仇恨,他若不逃,命自是难保;还因为这不是个理想主义人物,与那些不管为什么理想牺牲的人相比,多少有些煞风景。但跳掉又实在可惜,并非为了他的文名,而是从这个人物的命运可以拉出西方历史的一条根脉,他是这条根脉上最后一个公开的符号。这里说公开的,是因为不公开的什么符号都还有,作为公开的,塞林纳是个句号。下文会再细说。 写到这里众人都应该明白那个躺在橡木棺材里的人是谁了。1932年他写出成名作《茫茫黑夜漫游》时,没有人预料到他的结局是如此寂寞的。进先贤祠自然是免提,“爱人类”是其通行证之一,而塞林纳在我看来是“反人类”作家,他锐利的眼睛一眼穿透所有的逢场作戏,直达人性恶劣的本质,所以他不可能不对人性大“呕”特“呕”。我称这类少数分子是“永远搭末班车的人”。他就是进巴黎那三大名人公墓:拉雪兹、蒙马特和蒙帕那斯公墓,也是没有资格的。德图什家族,德图什是塞林纳的本姓,在拉雪兹是买了墓地的,他做小本生意的父母就葬在里面,他也想进去,但未能进。我倒想,他这人身上集中了太多的仇恨,进到那里面,恐怕远不如在默东这个小公墓里自在。至少知道他葬在这里的人没有几个。 那天,我在默东镇找这个小公墓,不好找,在一个老太太的指引下,走了弯弯曲曲一条迷宫般的小路,才在小路结束时柳暗花明,看到了公墓的大门。走进去一看,果然不大,在默东的最高点上,墓从大门这边顺着山坡铺下去,远处蓝色地平线那一边灰蒙蒙的地方便是巴黎。 一进门,就有个矮壮的中年男人迎上前,看墓人也。我一开口他便会心一笑把我带过去了。但一路上反复叮嘱:塞林纳的墓不得拍照。我走过那么多地方,墓地不准拍照,还是头回碰到。便问,哪来的这套规矩,他说是塞林纳遗孀定的。这个“反人类”的家伙果真是死硬到底,至死也不让人沾去便宜。 他的墓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花岗岩的,据说是他老家布列塔尼的石头,左上角画了个小十字架,尽管他是不信上帝的。正中央是一只帆船,到另一个世界去远游?每看墓地,看到从墓碑设计到题铭的用辞都有一定讲究,我总在问自己,为什么人从来没有将死当作真正的结束而是某种开始?船下面是他的笔名:路易-费迪南·塞林纳,再下面是他的本姓:德图什医生,1894-1961。 他喜欢以德图什医生自居,大概是把自己与那帮专吃文字饭的人区分开。其实是个半吊子医生,没进过大学,以一战老战士的身份,半走读半照顾性地做了医生。开私人诊所,又因脾气不好,一个顾客没有,只能在贫民医院里行医。 近半个世纪前的那个7月的早晨,在这里举行的仪式十分简短,五分钟,“茫茫死亡之旅”便在一个大地的黑洞中结束了。送行者中有塞林纳生命最后十年中的两个朋友,作家马塞尔·埃梅和战后年轻作家中的活跃人物罗歇·尼米埃。说到尼米埃,有个小插曲。 尼米埃喜欢玩车,某次开着辆跑车来见塞林纳,塞林纳对他说:“这将是你的坟墓。”塞林纳历来有“预言者”的美誉,被他这一断言,尼米埃送走塞林纳后不到一年就死于车祸,走时不到四十岁。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喜爱的东西全都将成为我们的坟墓,或迟或早。 那天送葬的人中还有一人值得一提,就是唯一在场的两个记者中的一个。塞林纳的本意是不要记者参加的,但遗嘱执行人尼米埃认为塞林纳毕竟非等闲之辈,他的死还是需要“目击者”。于是《法兰西晚报》来了一个,《巴黎报》派了一个,但谁也没想到后面的这个偏偏是个犹太人。 塞林纳一生的恶名没有别的根源,就是反犹,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真是命运最后的交响乐,这么反犹的一个人,告别这个世界时,送葬者精挑细选,总共十几个,还混进一个犹太人。连记者阿尔方本人也莫名其妙,他的推测是报社头儿怕遭人骂找个犹太人出面报道算是个挡箭牌。不管怎么样,一生妙算的塞林纳大概绝想象不到,天意自有自己的篇章,你可以导演生,未必能导演死。看看这个阿尔方在报道中说的一句话:“我让你们来想象在我的脑壳里正发生着一场怎样的风暴。被挑来,是因为不管是不是犹太人?还是恰恰因为是犹太人?才被挑来向这个我全身每一丝气力都在憎恨的人,致最后的……” 脏衣服 我发觉历史上有些人简直就像是被什么意志创造出来的人物,以一己之身搅上那么多的激情,他们在大地断裂时,拼了命地没有被一起拖下去,但一身已沾满了腥臭。谁叫他在1937年的那部抨击手册《为几个小钱的一场屠杀》里跳得那么高。 其实种族主义在文人中并不是自塞林纳始,也未至塞林纳而终。种族主义是西方历史的一条根脉。这条根脉在1945年似乎被一刀切断,塞林纳正好在这个切口上。自他以后,众人都闭了嘴,只不过要做的照做。一段历史要有一个公开的句号,文人中,塞林纳就是这个句号。 我无意为塞林纳辩护,只是觉得就这么画个句号,很是障眼,从此“正确思想”的西方就把“脏衣服”脱掉了。塞林纳1932年刚出道时,是个被左派欢呼的文人;但他1936年跳出来反苏,紧接着又反犹,便一下被划到右边去了。不过战前,持塞林纳式反犹观点的人,在人群中不说百分之百,起码也有百分之八十,而且从极左到极右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多大分野。左到像蒲鲁东、布朗基这样的人,反犹上也是不含糊的。蒲鲁东就说过:“要赶快把这个种族送回亚洲去,要不就把他们灭种。”而这是一个一生都在诉求社会公正的人。 要说透这其中的奥妙,没有谁比法属马提尼克岛黑人作家埃梅·塞泽尔说得更透彻了:“他们惊异,他们愤怒,他们说:‘这太奇怪了!不过,这是纳粹主义嘛,会过去的!’于是他们把真相对自己掩藏起来……是的,这是纳粹主义,但在成为被害者之前,大家都是帮凶……只不过大家都闭上眼睛,让其合法化,因为在此之前,这种野蛮的施予对象,不是欧洲人……说到底,他们不能原谅希特勒的地方,并不是这个对人犯下的罪恶本身,而是这个对白种人犯下的罪恶。” 只要看看法国1950年开始使用的小学六年级课本上写了什么,就会明白我说的“脱掉脏衣服”意味着什么。要知道这套教课书并不是1945年前的版本,而是在二战种族屠杀刚刚过去两年的1947年编写的!上面还在教育儿童犹太人有一个鹰钩鼻,金发的亚利安种优于其他人种。孩子们还在学西方文明“觉醒于和东方接触之时,而这个文明远胜于东方文明”。 再比如,澳洲移民法中曾有一个二战后仍继续延用的“秘密文件”,在可接纳的移民中(要知道这是在它地广人稀极需人力的情况下)有色人种是被排斥的,即使欧洲白种人,也是要“亚利安种族”,而不要那些用塞林纳的话就是被阿拉伯和犹太血液“污染”的南欧人。“亚利安种”这个给那么多屠戮以口实的词,在二战后照样出现在这个官方文件里!美国的移民法里也有类似的种族配额,比如1882年通过的移民法,就完全禁止中国移民。1921年通过的Quota Act写明优先接纳盎格鲁-撒克逊移民。 在西方呆长了,知道他们有一个常用词“civilisé”,法语中这个词直译为中文是“文明的、文明人”的意思,中文这么看是看不出什么的,其实里面浸透了潜台词。 比如你刚从中国回来,告诉朋友要去荷兰,他会毫无恶意地说一句:“啊,你要去文明人那儿了。”这对他们是那么的自然,他们那种心平气和、不带一丝犹疑的优越感,让我这个来自东方的黄种人常常有一种触及根上的忧愁。对于西方人来说,剩下的那部分世界是文明之外的世界。应该承认,这多少有一部分的真实,看你用什么标尺来量,不能说他们就是盲目的狂妄自大。这个世界两百年来的确是在围着他们转。就像我们的“低贱感”,也并不都是奴颜媚骨,至少对于一部分人说是清醒的表现。在西方,无论左右派,在这一观点上是没有什么分野的。那种优越感是在每一个人心里的。作为白种人之外的人种,你多多少少迟早都会感觉出来。除非你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不再做中国人。这种优越感是浸透血液的,在最平常的语言里,在最有礼貌的举动中,在似乎是最理想主义的思想方式中,无处不在。在这里,左派一点都不比右派公正,人道主义者只是更虚伪。 从墓地往山下走,想到另一个人,也是作家,可算是塞林纳的鼻祖。此人叫阿蒂尔·德·戈比诺,法国19世纪的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兼外交家。现在很少被人提起,原因是他1853年写了一本书《论人种之不平等》,现在属于被脱掉的脏衣服类。 戈比诺把人按肤色分黑、白、黄三种,等次是由浅到深,他说:“高等人种有权利也有义务向低等人种播撒文明。”他的理论粗略说,就是完全否定环境论,认为一切都来自血液。他是第一个将种族由一个事实变为一种价值的人,也是第一个宣称亚利安种族绝对优越的人。 一般说,戈比诺是现代种族主义之父。关于种族及亚利安种的神话,自此开始。这套理论对19世纪中后期铁马金戈横扫世界的西方无疑一帖兴奋剂。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当时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移民到他们军队占领的各大洲,没有一人需要申请签证。这使我想起西方近二十年来全面关起大门,像堵洪水猛兽一般不惜手段围堵“南方”人口爆炸挤出来的人。新的文明理论伴随着这股浪潮推出来,诸如“文明冲突论”、“文明不可融合论”,全是当年“种族论”的变种。说白了就是一句:我没法消化你,你现在离我远点。我们钱物交往,你别来“玷污”我的血液。当年找上门去可是没有邀请的。美国从1994年起,在美西边境以每年几十公里的速度,建一座恐怕比中国的长城还要“雄伟”的高墙,来围堵从南美过来的移民。试想想当年美洲印地安人也筑起一道这样的长城来围堵欧洲过来的移民,历史会是怎样一种写法? 我时常在巴黎三月广场看到那群向游人兜售饮料和旅游纪念品的非法移民,里面有中亚人、南亚人、非洲人,也有中国人。三月广场上并不都是新近涌来的中国游客。他们夏天露宿在草地上,冬天不知多少人挤在一间小破房子里。想想这块富得流油的土地,就是不愿意分一杯羹给他们。物质极端贫困倒也罢了,他们没有一个是想白吃饭的,关键是从一脚踏上这块土地,什么还不是先成了罪犯,被抓得惶惶不可终日,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同情者,“自找的嘛!” 就在我写此文的这两天,还传出一个案子,被判罪的是两个法国人,罪名是在家里收留无处栖身的非法移民。面对这些在生命中连生存权也被剥夺的“非法”移民,我看不出他们的命运比二战时的犹太人好到哪里,被排斥的命运是共同的。有一点也是共同的,这些人的不幸是大家都接受的不幸。来自异乡的、肤色不同的人,他们没有资本,他们不受欢迎。他们什么权利也没有,这是写进法律的,他们只有滚蛋的权利。既然“人权宣言”上有一条“人有迁徙的自由”,为什么“南方”就不能有这份梦想?非法移民正在成为21世纪的犹太人。 绝版 我又扯得太远,此时我已从山上“美景墓地”逆着那具橡木棺材当年走的方向,来到卫士路25号门前。一栋白色的花园洋房,铁栅门紧闭,塞林纳的第二任妻子尚在世,但显然已不住在这里。门上有新屋主的名字,但没有作家故居都有的那种纪念牌,当然不会有,“脏衣服”嘛。 塞林纳1951年大赦从丹麦回来,最后十年就住在这里。他以他战后的逃难经历,继续写作谋生,邻居们只知道他是德图什医生。他后来写的书,没有一部超过《茫茫黑夜漫游》,早知如此,1932年以后他若不再写了,未必不是上策。在文学上,成名作风格太特异,以后的作品没有突破便不被原谅。一般说他与普鲁斯特是法国现代文学中两个打破文字习惯的人,但他那种口语式文风我并不欣赏,把他抬得那么高,不失炒作和人云亦云成分。他完全把他自己的说话方式移植到语文中,那种文风译成中文无论如何都已经不是味儿了。不过他是凭极度敏感写作的人,这一点倒是和普鲁斯特一样,具有我称之为“艺术的脆弱”那种东西,这种东西在寻常的感觉之外再延伸出去,只一线之牵,多数人是走不过去的。只不过有时走得太远,这是传奇的代价。他是他自己的传奇。这还不够吗?他的那几部“大批判文章”,1937年的《为几个小钱的一场屠杀》、1938年的《尸体学校》和1941年的《漂亮床弹》战后都绝了版,他和他的著作权继承人都决定永不再版这几本书。这就让1945年前的版本成了旧书市场的抢手货,价格贵得吓人。你走进旧书店,那几本书是从来不放在台面上的。你对书商说要找那几本书,他脸上马上露出会心的一笑,走去店铺后面拿出来。 把那个阴雨的早晨向后退三天,是1961年7月1日。塞林纳在前一天写完了《双人舞》。星期六一早,他说不舒服,一整天和他的四只狗一只鹦鹉呆在一起,没有再写什么。他喜欢动物胜于人,我倒觉得不必如此决绝,人要爱,不妨远远地爱。将近晚6点时,他对妻子说,“不行,我去躺一躺。”他睡下后,再也没有起来,脑溢血,死在自己的床上,算是一个好死的结局。 他至死没有向犹太人道歉,真是个不怕臭名,只想活在自己的真实里的人。他生前说过一句话:“我把我这条命放在桌上……如果你不把你这条命放在桌上,你什么都没有,必须付账。”绝大多数人不把命放在桌上,做了坏事账都不愿意付。 三个人的活 我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想引用三个人的话,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犹太人。英国人叫约瑟夫·张伯伦,1895至1903年是英国内阁殖民部部长,后来那个参与签订“慕尼黑协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就是他的儿子。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是的,我相信这个种族,这是世界至今为止从未有过的统治人的种族中最优秀的种族,我相信这个骄傲而顽强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 法国人叫埃内斯特·勒南,19世纪的一个著名作家,戈比诺的门徒,我选他的这句话和上面张伯伦的话,是因为这两句话与现代国际关系的版图惊人地对称。他说:“大自然造就了一个做工人的种族,就是中国人,这个种族手很巧,又几乎没有任何名誉感……一个干农活的种族,就是黑人……一个做主子当军人的种族,就是欧洲人。” 犹太人中无人不晓的是马克思,他在1853年写的《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说:“印度社会完全没有历史,至少没有被公认的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它的历史的,只是它的一连串入侵者的历史……英国在印度有双重使命要完成,一个是摧毁,一个是更新,就是摧毁古老的亚洲社会,而建立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注:笔者不是直接译自德文,可能没有正式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文准确。)对于西方人来说,我们都没有历史,我们的历史从他们与我们接触的时候才开始。我引用这句话是想说明,西方怎么都是赢,伸出右手是赢,伸出左手也是赢。 我记得我有个大学同学,在学校就入了党,是组织培养对象,毕业分配时有好去处自然先考虑到他。他毕业后分到外资企业,没过几年就对另一个与他同样“幸运”的同学说:“我们都是高等华人。”看来我说的那种优越感还极具传染性。 我惊异于我们从一种立场跳到另一种立场时,几乎不加思索地省去了中间的过渡。我们走不出来,走不出来。 我们自然大可不必跑到大洋那边才能找到我们不幸命运的根源。但至少不要忘了我们从哪里来。 前两天严重失眠去看病,这个医生常给我开安眠药,算是熟了。我们谈起我的病,他抬起那双不知祖上第几代被蒙古人“污染了”血的欧式细眼睛,忽然问我:“你是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读了上文,应该不难理解这种思维逻辑的必然性:你如此睡不好觉,在你那样的国家里,一定是政治迫害的结果。我懒得解释,还之以一个玩笑:“我这人到世界任何角落都是持不同政见者,恐怕到了天上也不可避免,因为我不敢保证我会同意上帝的观点。” 相关专题:关注全球非法移民现象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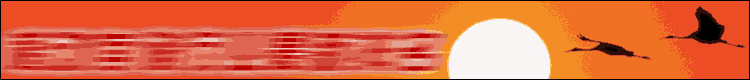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关注全球非法移民现象专题 > 正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