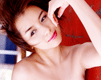宁愿有尊严地死去?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5日15:59 新民周刊 | ||||||||
|
那一瞬,我就想着,我要是死了一定要穿红衣服,好变成厉鬼找我妈和那个医生报仇。我迅速冲到了四楼,没有迟疑 ,一下子就跳了下去。 撰稿/杨 江(记者) 孤注一掷
此行,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在重庆大渡口区,是一个叫做周颖的28岁女子。因为在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所做的开颅 戒毒手术“失败”,她的情绪失控,于今年3月21日,从所在的居民楼四楼飞身跃下,幸运的是没有摔死,但造成了尾椎骨 骨折 。 与杨大武一家相似,周颖对于记者的到来心情复杂:究竟是相信媒体好呢,还是防着媒体好?见面后,她的这个问题 令我有些尴尬。 她递给了我一支烟,我没有迟疑,接了过来。她愣了:“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对我,这很难得到。” 她并不像我以往接触过的那些瘾君子那样面黄肌瘦,眼睛泛青无神,相反,她的面色红润,不过,眼睛里还是流露着 一种无助与忧郁。 她说,已经两个月未曾吸毒,但是谁也不信她,包括她的父母。“这并不是手术的成果,事实上,我在手术前已经成 功戒毒半年,在做完手术后却很快复吸了。并且有了很多并发症。” 周颖说她有两个埋怨的对象,一是母亲,是她执意强迫女儿接受开颅戒毒手术的;二是媒体,老人之所以如此,正是 看了重庆一些媒体当初对开颅戒毒手术“惊奇成功”的报道。 她染上毒瘾的过程与大多数吸毒者相似:年少无知时,缺乏父母管教,混迹江湖,被瘾君子拖下水…… 周颖已经被父母赶出家门,在征得她的父亲周小平的同意后,我们得以进入她的家。这是一般吸毒者家庭可以想象的 残破与贫穷:昏暗的走廊让人踉跄,屋内淡淡霉味,一台电视机是仅有的家电…… 周颖侧对着父亲,香烟一根接着一根。 1995年,一向忙于生意的父母发现我吸毒后,把我从广州带回重庆,从此想方设法给我戒毒,前后进强制戒毒所 十几次,但每次我都是心瘾难除。 长期以来,我依靠药物治疗毒瘾,“美沙酮”、“那曲酮”不知吃了多少,一小瓶“那曲酮”就要600多元,费用 很高。 后来对这些药物也有瘾了,每天超数倍的剂量服用,吃下去人像疯了一样,脑子一片迷糊,眼珠子发亮,却死死地盯 着前面,一动也不动。 虽然吃这些药能够摆脱毒瘾发作时那种浑身疼痛、流鼻涕、万蚁噬心的痛苦,但终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 月上千元的治疗费,把开面馆的父母压得喘不过气。 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觉得不能再这样堕落下去,我就让父母把我反锁在家里,吃安眠片,没日没夜地睡觉,睡着 了就不会想毒品了。 我坚持了两个月,再见到毒友时,他们在我面前吸毒,我也能忍住。但是我对自己还是缺乏信心,我想尽快彻底除掉 心瘾。 2004年9月3日,一个曾令我们全家欣喜万分的报道刊登在重庆一家报纸上:全程直击开颅戒毒手术,报纸还刊 登了大篇幅照片。 两天后,父母就去了泸州,他们看到了报道中的那个小伙子,他当时做完手术,满脸浮肿,还在乱摸,喊着要白粉, 但是医生说这是暂时现象。 周小平说,他与妻子瞒着周颖去了泸州,在医院内,他们听说有一个成都人交了住院费,但是并不需要手术,而在病 房内卖白粉,就在周颖做完手术后,还有人跑到周颖身边问周颖要不要“药”。 做父亲的考虑过手术的风险,毕竟医院的宣传中说手术成功率是90%,并非百分之百。“但是我们宁可要一个呆子 ,傻子,也不要一个吸毒的女儿,何况,医院宣传单上说,尽管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性功能减退等后遗症,但会逐步恢复正常 。 因此,周颖的母亲拍板:立即让周颖住院。 飞身纵楼 当时,医院的一个保安私下对我说不要做这个手术,说有一个人手术后傻了,还有一个人大小便失禁。我也很担心, 但是9月22日上午,我还是手术了。主治医师是陈礼刚,手术也由他亲自主刀。 我被剃光了头顶的头发,后脑穴位被注射了麻醉剂,然后戴上一顶金属圈。后脑的皮肤因为压力开始收缩,最后鼓起 几个巨大的包,医生就在这几个包上扎上了4颗螺丝钉,然后在头盖骨的两端分别开了两道口子。 我当时是清醒的,没感觉疼。就听见医生用钻钻骨头的声音,特别响,震得我耳膜快破了。我吓坏了,只好大声尖叫 。 我很奇怪,这样的手术,医生竟没有为我戴氧气罩,打的麻药从头顶一直流到脸上,又渗进眼睛里,像火烧一样疼。 手术临近尾声的时候,医生问我:“你现在还想不想吸毒。”我回答,你不说当然不想,你一提到我就想了。而后, 我就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脸上因为麻醉剂的侵蚀已经红肿。我突然发现我的嗅觉没有了,食欲开始下降,我以为是暂时的。 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恢复,而且我很快开始偏头痛,记忆力迅速下降。30日,我出院了,共计花费3万多元。但一 出院我就想毒品,我脑子懵了:完了,手术失败了。 我四处找毒品,一个月内吸了不下20次。 就在此时,周颖的父母还蒙在鼓里,他们放心地把周颖留在家里,经营着小面店的生意,就因为医院曾宣传,手术失 败率只有10%。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邻居却跑来告诉他们,周颖因为吸毒被派出所抓走了。 母亲赶紧跑到派出所,看到女儿直愣愣地望着派出所民警,民警问她任何问题,她也不回答,最后干脆一把扯下头上 的假发,对民警说:“我刚去泸州做了开颅手术,你们看嘛,还有两个大口子。 周颖头顶的两道伤疤触目惊心,民警动了恻隐之心,对她一番教育后放她回家。 一个“面目全非”的周颖开始展现在父母面前。 每天夜里我都会因为头疼呻吟吵醒父母。那种痛,根本不能用语言描述,就像有人用铁丝用力扯着你脑袋里的神经一 样。最痛的时候,我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敲碎。 我的情绪开始失控,很暴躁,觉得活着没意思,想自杀,也想出家,思维开始迟钝,说话不流利。 我的头脑开始恍惚。3月21日晚上,父母回到家刚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从床上一骨碌爬了起来,双眼斜视着他们 ,一边穿旅游鞋,一边把粉红色的外套往身上套。 我当时就想着我死了一定要穿红衣服,好变成厉鬼找我妈和那个医生报仇。我迅速冲到了四楼,没有迟疑,一下子就 跳了下去。 我并不知道我在自杀,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手术前,我是一个很怕死的人,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跳楼前我曾到泸州反映手术失败的问题,医生说如果手术不成功,吸毒量会变得变本加厉的。 屋子外面嘭一声巨响,父母都以为我死了,他们气乎乎地坐在屋内,110来了,他们不肯开门看看我到底怎样,120 来了,他们还是没有出来。 后来医院打了十几个电话,爸爸才接了,听说我只摔伤了尾椎骨,他就去了医院,但母亲没肯去。 我知道他们恨死我了。但是手术后,我整个人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我开始卖家里的东西,有次毒瘾犯了,想也不想 就把家里的洗衣机、空调和功放机以一两百元的价格全部卖给了收破烂的。 卖到只剩一台25英寸的电视机时,因为家里的大门被父母反锁了,我就让收破烂的人站在家窗外,捅烂防盗网,再 一起把电视机抬出去。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好邻居及时发现,保住了这台电视机。我以前吸毒再厉害,也不会卖家里的东西。 我现在控制不住自己,看见水杯放在茶几上,就觉得应该把水杯摔在地上,然后就会马上去摔。事后,清醒了,也不 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并非个案 周颖无助地抽着烟,她的父亲却在一旁驳斥她:你那不是卖,是偷!小偷!他为此把女儿三次送到派出所,要求民警 法办。邻居们也开始鄙视她,周颖参加社区的劳动,有人讽刺她。“我要捍卫我的电视机。”周小平当着我的面跟女儿针锋相 对,他在女儿骨折恢复后将其赶出了家门。 “你们从来都不相信我。我不是卖去吸毒,我是筹集生活费。现在已经两个月没有吸毒了。”周颖有些恼怒,她曾私 下告诉我,跳楼受伤在家养伤期间,母亲日夜照顾,令她心生愧意,决心不再碰毒,于是边借助烟酒麻醉自己,每天能喝近一 斤白酒。 “你继续撒谎吧,谁信?!”周小平有些不屑,“杨记者,她把两个手机都卖了,你问问她干什么去了。” 周颖不言语了,她开始干咳,吐痰,坐立不安,然后赶紧抽烟…… 跳楼后,一名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一路问讯找到了我家,她说她儿子也是在泸医附院做的开颅戒毒手术,经常在家里 莫名其妙摔东西,前一秒可能规规矩矩看电视,后一秒就可能把家里砸个稀巴烂,还时不时自残,割腕,用香烟烫自己。 因为泸医附院专门交代患者之间不要互留电话号码,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我一个人手术失败了。其实,就在我自杀前一 天已经有6名与我相似的患者家属到泸医附院投诉手术失败,要求给个说法。 过了一个星期,来自四川各地和重庆的9个手术失败的患者家庭,包括我父亲又相约去了泸州交涉,但医院就是不承 认手术失败。 经过一天一夜的协商,医院答应5月对我们进行全面检查,但是后来又变卦不肯报销车费。 5月12日,我接到泸医附院电话,到泸州接受检查,但是整个过程简直就是“敷衍了事”,检查的结果直接关系到 卫生部对他们的鉴定,我真的怀疑,他们会不会如实检查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把结果如实上报卫生部。 周颖是在9月22日接受手术的,我获悉,21日接受手术的成都患者余柯志、张时栋,23日接受手术的雅安人方 咏、泸州人李果,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头痛、脾气暴躁、自残、失去嗅觉、复吸、人格变化等情况。 “既然治愈率90%,为什么这三天的失败率是100%?!“周颖现在居住在一个朋友家,此人曾经是一名瘾君子 ,但周颖介绍,说他成功戒毒十多年了,周颖渴望像他那样。 5月29日晚上,在周颖母亲的面店,我劝慰这位饱经沧桑的母亲给自己女儿一些信心,不要让她有被抛弃的感觉。 老人一直没有说话,要么盯着地面,要么抬头望望女儿,周颖还是那句话:“妈妈,我真的不吸了。” “撒谎!” 周颖不言语了。 就在记者回沪写稿期间,周颖打来一个电话,她说,她期望重新回到父母身边,但是又一次被父母拒绝了。 “弟弟,我这是最后一次打你电话,我这回准备从十几层跳下去,我这样生活太累了,没有希望。” 她把我叫做弟弟,说是这么久,我是她第一次碰到的尊重她、相信她、鼓励她的人。 我说,包括我和你父母,从感情上可以相信你,但理性上,我们告诉自己,不可能,除非你以一个彻底的新的生活面 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你看,你现在一刻不能离开“烟”。 周颖沉默了:“我现在是还没好,这需要时间……手术后我控制不住自己,很绝望……” 这些都是后话,我当时决定,第二天带她去成都等地一起走访张时栋、方咏等人,让她亲见吸毒导致家破人亡的现实 教训。 她有些惴惴不安,但是她的母亲却对我露出了一丝笑容。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