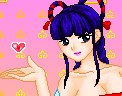78岁老人苦撑养家:儿子发疯儿媳失明老伴瘫痪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07日18:01 南方都市报 | |||||||||
|
本报讯 黄显年已经78岁了,体重不到50公斤,当他的同龄朋友在晚辈照料中安享晚年,或者在家做操试图恢复健康的时候,他还佝偻着站在高州一所民办学校的讲台上授课。“文革”期间,他的儿子因遭受打击而变疯;3年前,儿媳突患眼疾双目失明;去年,老伴中风瘫痪,而孙子和孙女都在读书,全家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对这个家庭来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这是一个真实的悲情家庭样本,从中我们既看到了历史与命运之惨烈,更看到了人性之坚忍与温暖。
在学校,他就没有烦恼 他从未因家庭困难而影响教学,从脸上也看不出悲观 离家越近一步,现实就向黄显年逼近一步。他的脸色开始凝重起来。 2005年12月11日,周日,一周里唯一不上课的日子,今年冬天的第二次寒潮已经降临。黄显年穿上毛衣,外套一件酱灰色的宽大夹克,这使他显得更加瘦弱单薄。喝过早餐稀饭,他走出高墙围绕的富山学校,等候公共汽车。 在茂名东南郊的这所民办学校里,没有人比黄显年的年龄更大。他可能是整个高州乃至广东年纪最大的一线老师。因此当有新老师刚刚进入这所学校,看到一个驼着背、发须间白,只有1.6米高的老头,居然是初三毕业班语文老师且兼任校文学社社长时,往往惊奇不已,而这个老头都会微笑着主动和他们打招呼。 每次,黄显年佝偻着缓步走上初三(1)班的讲台上,台下37名学生比上其他任何课程都要显得安静。“同学们都知道,在年近八旬的黄老师面前讲悄悄话,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这个班的班长潘晓丽说。 他已经在这里教了4年书。而在他漫长而曲折的59年教学生涯里,他教过多达15所学校的语文,1989年从高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退休,高级讲师。 除了校方照顾不担任值班和生活老师,78岁这个年纪并没有让他显得和同事们有什么不同。一周他教16节课、4节自修课、2节早晚读课,包吃住月薪1000元,是全校最高之一。每周六上午,他要连续讲4堂课,而且一直站着,课间才去办公室坐一会,喝口茶。 但他的肺气肿越来越厉害了,走到教室二楼半时,他必须站定,调整下有些困难的呼吸,才能继续走上三楼。今年3月,他犹豫再三后,花2890元买了一台脑病生理治疗机,用来解决他“头晕睡不着、脑子混沌”的问题。老伴瘫痪后,他感觉自己明显衰老了。只有在讲台上,黄显年才恢复了作为一名教师的自信。 “黄老师的课我们都爱听。”潘晓丽说,“今年开学听说他担任我们语文老师,同学们都担心他年纪太大讲不好,但最近的期中考试表明,语文课是我们班进步最快的课程。” 50年前,当他还是一名村小教师的时候,就因为讲课生动吸引了县教育局局长前来旁听。后来,他把许多语文知识编成歌谣,有修辞歌、阅读歌、作文歌等十多种。“读起来琅琅上口,饶有兴趣。”富山学校董事长邱炽华说,“从这些歌谣里哪里能看出黄老师的悲苦呢?” “文革”期间,黄显年的儿子因遭受打击而变疯,3年前,儿媳突患眼疾双目失明,去年老伴中风瘫痪,孙子和孙女都在读书,全家开支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邱炽华和初三(1)班班主任毫不吝啬对这位老人的溢美之词:师德高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工作负责……“尤为难得的是,他从未因家庭困难而影响教学,从脸上也看不出悲观。” “他那么苦却那么坚强、乐观、豁达。他讲课幽默风趣,下课和我们聊天,也是笑眯眯的,他就像我爷爷,也像我们的朋友。”潘晓丽说,黄老师教会了她怎样面对生活。 黄显年一走上讲台就忘记了尘世的喧嚣与虚无。“我爱学生,学生也爱我。我最大的喜悦就是看到学生进步、成才。” 在学校,他就没有烦恼。 失明儿媳:最重要的助手 她就这样摸索着照顾人,很善良,很细致 黄显年挤上16路公共汽车进入茂名市区,然后花2元钱乘摩的来到一家医院,咨询他儿媳阿兰(化名)的眼睛治疗情况。这次接待他的是他曾经的学生,也是他同村老乡,一名60岁的眼科副主任医师。“他不会像其他医生那样说大话的。” 但当医生毫不掩饰地告诉他,阿兰很难重见光明时,他的眼睛顿时黯淡下去,垂眉半晌不语。医生安慰式地开了些药,并告诉他病人要多吃富含维生素A、B的蔬菜。他小心把清单放进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 “他是我们村的秀才,多才多艺,为人诚恳热心,乡邻没一个说他不好的。要不是几次受到冲击,他可能早就做大官了。”医生热情地对旁人介绍说。黄显年有些苦涩地笑了。 很多个休息日,黄显年都在高州、茂名多家医院探听能否改善儿媳的病情。对于他来说,失明的儿媳已经是照顾家庭的最重要的助手。 绝大多数时间里,阿兰把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反锁上,把自己和这屋里的人锁在一起,这让她觉得安全。实际上,他们又各自被锁在三个世界里。她的丈夫被单独锁在二楼,因为他是个有暴力危险的精神病人;她中风瘫痪的婆婆被锁在一楼潮湿的房间里;她自己则被3年前的突然眼疾终年锁在黑暗中。2002年,阿兰与同事出游归来突感双眼肿痛,被诊为视神经萎缩,次年彻底失明。 每天,足不出户的她就摸索在这三个世界当中:洗衣、做菜,定时给两个病人送药、送饭,不断扶婆婆坐起、躺下,以及忍受她没有来由的埋怨与责骂。从法律上说,阿兰和这个家庭在1994年就断绝了关系。那年,她和一犯病就打人的丈夫黄可明离婚。阿兰在高州独自生活了10年。“我虽不舍得,但她还年青,不能耽误了她。我现在还把她当女儿,她也当我是爸爸。”黄显年说。 2004年夏,阿兰重回黄家。她记得那一天是7月8日,婆婆瘫痪在床一个多月了,上初一的女儿打来电话说:“妈妈,我好累,好想哭,奶奶又拉屎在床上了。”然后,她决定立即动身。但她并没有和前夫复婚。 “我和黄可明之间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爱也没有恨,只是觉得他可怜,其实我也很可怜。”阿兰说,“我过来只是因为我的两个孩子。我不来,又请不到、也请不起保姆,女儿学习就要耽误,爸爸就要扔下工作,赚不到钱,我的孩子就读不起书。” 她为黄可明生下了两个孩子,男孩在湛江读技校,女孩现在正读初三。想到他们,阿兰就很开心。 “她就这样摸索着照顾人,很善良,很细致。”黄显年60岁的外甥闭着眼睛、移动伸出的双手说。他和他80多岁的父母经常来这里探望和帮忙,他们是这个家庭在当地唯一的亲戚。 每天女儿放学回来,才给这个沉寂的家带来一些生气,她一边帮阿兰干活,一边说话。今年国庆长假里,刚去湛江读书的儿子也回来了,晚上父子俩隔着卧室的“铁窗”一起看电视,但都没什么话。第二天,儿子带母亲回高州散心。每天睡前,儿子都对她说:“妈妈梦想成真,做个好梦眼睛就好了。”临走前,他唱着“再见吧妈妈”这首歌。她说,儿子长大了! 阿兰每月还能从单位领到800多元工资,其中500~700元用于吃药。失明后,她开始收听广播,“这样什么烦恼都跑掉了”。 “屋子里好闷啊!” 失明的媳妇,发疯的儿子,瘫痪的老伴,封闭于各自的世界里 中巴车到达15公里外的高州市分界镇时,已近中午。黄显年又去镇上药铺给老伴和儿子买了些药。这天,他一共花了100.2元。 他不得不精打细算。他每月1420元退休金和1000元教课收入是这个家庭全部生活来源。老伴每月吃药200多元,儿子吃药350元,家里生活费500~600元,自己花销100~200元,孙子孙女读书850元,一个月下来就剩不了几个钱,这还是放弃进一步治疗后的紧缩性开支。 黄显年不想让儿媳摸索着再去准备饭菜,花1元钱在一家小店要了碗云吞。这时他衣兜里200元买来的二手手机响了,孙女问他怎么还没回家,一直阴郁的他终于舒心地笑了,说自己还在外面忙,来不及回家。 在去年回分界镇读书以照顾奶奶之前,孙女在爷爷身边生活了两年。富山学校免去了她所有的读书费用。她的理想是长大后,像爷爷那样做一名出色的人民教师。 “现在,她为照顾奶奶耽误了学习。”黄显年慢慢说着。他吃完云吞后,再花1元钱,买上5个小包子向家里走去。门,仍然是反锁的。 这是一栋16年历史的两层混砖结构楼房,坐落在分界镇一条主要街道旁,不时有大货车轰然驶过。但阿兰把门反锁后,房子里却显得异常安静,偶尔从二楼传来黄可明含糊的说话声。今年4月,一名阿姨指责说他拿石头打破了她的头,黄家只好给她200元赔偿。从那以后,黄可明就一直被禁闭在楼上。 他今年48岁,脸庞端正,一双大大的眼睛,长期吃药使他看起来很结实。“但他没有力气。”阿兰说,“离婚前的一个晚上,他突然拿起一根粗木棍打我,被我抓住,两个人就这样顶棍,顶了好久,儿子就睡在身边看我们顶。他还把爸爸的头打破过,把妈妈打得爬不起来。” 黄可明是父亲唯一幸存的孩子。他高中毕业时的成绩,在200名同届学生里大约排在20名,但时逢“文革”,父亲“地主出身”、“摘帽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黑手”这三个身份破灭了他读大学的梦想,最终黯然回到老家种田。不久,他就疯了。 “他曾是我们家最大的希望。”现在,这个希望开始转移到孙子孙女身上。 黄可明先后进城治疗两次,1980年病情趋于稳定,1983年与阿兰结婚。“大人都说结了婚他就会好的。”阿兰说,那时,黄可明26岁,她20岁。作为对优秀教师家属的照顾,她从农村调入县城与岳父同在一所学校,担任后勤工作。她想不到,结婚后7年,黄可明还是病情复发了。 “我想上大学”,黄可明有时会突然嚷道,但现实决定,他的最佳去处乃是铁门后的二楼空间,他吃喝拉撒睡全在那里解决,那里有两个房间和一个用铁条封闭的阳台。他喜欢翻看孩子们读过的课本,一边念念有词,有时则半天不作声。他还在街上闲走的时候,喜欢对人说:“你好叻,我出坏世。”嘲弄自己经历的不幸年代。 镇上一名卖水果的妇女说,大家都对他避而远之,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捡起石头砸人,但他从不攻击比他高大健壮的男子。每天,阿兰给他送3次饭和药,却不敢踏进铁门一步。她说眼睛看不见了,再也无法抵抗挨打。 到了晚上,女儿去学校上晚自习后,他如嚷着要看电视,阿兰便把前堂大铁门反锁,再把二楼铁门打开,同时也把一楼走廊前的铁门锁上——自房屋建成,这里就专门设立了一道铁门,防他进入走廊后的屋子,除了他,所有人都住在里面。黄可明下楼来,坐在铁门前的凳子上,隔着加了铁栅栏的卧室窗户看电视。这是一台快要报废的黑白电视机,再怎么转动天线,也只能收到两个台。这时,阿兰就去厨房听广播。两人隔着走廊和铁门,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在一楼,终日躺在床上的妈妈却不知道儿子这样被关锁着,她手里如有了好吃的东西,总忘不了喊“可明”过来。她喊得最多的则是丈夫的名字,但都没有人应答。 老人的胃口特别好,吃了面包还要吃番薯,好像总也吃不饱。瘫痪后的她火气也很大,喜欢骂人,有时从夜半骂到天亮,阿兰只好把收音机打开,用耳机塞住耳朵。 “屋子里好闷啊!”阿兰说,但在女儿明年考上高中之前,她不会离开这个家。 在历史中沉浮 从一等劳模到“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手”,那个年代他不愿提起 敲了许久的门,阿兰终于从黑暗中摸索着迎出来。黄显年把药品递给她并告知怎样用药,刚刚还在大声高兴说话的她突然静下来,使劲眨了几下眼,然后闭上,眼眶分明红了。 黄显年打开一楼里面房间的锁,推门进去,老伴正赤脚躺在没有棉絮的木床上,一块宽大的薄膜支撑在半空,防止雨水渗过墙面滴落下来。她和儿子一样,吃喝拉撒全都在一个固定的空间。见到丈夫归来,她转过灰白色头发下瘦骨嶙峋的脸庞,语气哽咽。这对同是地主出身的患难夫妻一直聚少离多。结婚57年,真正团聚的时间只有14年。 黄显年总难忘记,土改中,他被调往邻村教书,为“划清地主阶级界线”,他被禁止回家,也禁止寄钱寄物回去,妻子没有分到田地,独自带着两个幼儿艰难度日,结果两个孩子先后饿死。直到他调到另一个乡,一天晚上,妻子步行近20公里偷偷找到他,他才知道儿子死亡的消息。这时,双方已2年多没见面。 第二天早上,他妻子就含泪离开了。 “她比我小1岁,和我同村,为了让我安心工作,她再苦也是独自默默承担,她是一个伟大的妻子,我一直很感激她。”黄显年把老伴扶坐在椅子上,然后爬上床,把紧闭的窗户打开,一股清凉的风吹了进来。 黄显年1946年高中毕业拿起教鞭后就一直在高州不同地方的讲台之间漂泊,他的命运也在随波逐流。 1955年,黄显年因教学有功被调进高州一小,评为高州县优秀教师,经常为全县语文教师举行公开课。1956年评为县一等劳模,开劳模大会时坐在主席台上,并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激动得差点掉泪,会后走上大街游行,沿途锣鼓喧天、掌声如潮。1957年,当选广东省优秀教师,1个月内两次从广州载誉而归。 他再次出现在浩大人群里,却是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手”。他脖子上吊着沉重的黑板,双手被涂满了墨汁。一名农村的学生家长把身上的汗巾摘下,给他垫在黑板铁丝挂下,才没有让他的脖子勒出血来。 十多年里,他几次经历了天堂到炼狱的坠落。还没从劳模与优秀教师的喜悦中回过神,就被卷入反右狂潮。刚刚上任镇上的小学整风小组组长,几天后即因“向党提意见”被打成小学第二号右派,1年后赦免,却仍是“摘帽”的。“文革”开始后,前几天还有校工会送来奶粉,犒劳他为提升升学率作出的巨大贡献,转眼即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手”的黑板游街。 在前来拜访的人士面前,黄显年都是笑着把这段历史讲出来的。“那个年代实在荒唐得可笑。”他说,“但如果你们不主动问的话,我都不愿意提起。” 平反后的1980年,分居32年之久的妻子回到身边,在他所在的乡下中学养猪,1983年一起进城。1994年儿子离婚后,妻子回分界照顾神经错乱的儿子,双方再度分开,只在周日才得相聚。去年6月的一个周日,他再次回家,用铁锤打开反锁的大门时,发现妻子已经中风瘫痪倒在厨房里,儿子在旁浑然不觉。 “那一刻,我觉得从未有过的无助心慌。”黄显年承认,当时自己泪流满面。 在这个清风吹拂的下午,黄显年默默陪伴在老伴身边,给她喂饭,喂包子,偶尔说说话。最后,他把剩下的2个包子给了儿子。 隔着铁门,他没有和儿子多说什么——多说也是枉然——也来不及等孙女下课,便告别家人。这里没有他睡的地方——要睡,只能蜷缩在客厅的长凳上,或者去姐姐家借宿。他还要回学校批改作业,那里能让他安静下来。 中巴上,他躬着背,缩着肩,两手紧紧抱在怀里。他似乎很冷。 有时觉得挺幸福 “我要像我学生寄语的那样,挺住、挺住、再挺住!” “你哭过吗?”“哭有什么用?”老人平静地说。 他“哭出声”的有两次。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他看到一位老师的一对儿女淹死在河里,让他想起自己已经死去的两个孩子;一次是10年前他大哥过世,他自小失去父亲,大哥辛苦把他养大,还给他娶上了媳妇。 此外,他都能在再大的打击面前,忍住哭声。“苦难接二连三,但这并不是别人给你的,这是命运的残酷。但相比为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士,这些又算得上什么?”他说。 “总不能去跳湖吧?”老人笑了,随即,严肃起来,“我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不是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我是好人。” 烦恼的时候,他就写戏曲,写绝句、律诗,“都是积极健康向上的那种”。 现在,他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正在读技校的孙子能早日找到一个稳定工作,娶上满意的媳妇,但他担心支撑不到那一天。 “我死了,这个家也就塌了。”他说,“所以我要像我学生寄语的那样,挺住、挺住、再挺住!” 去年11月28日,高州市副市长邓建和率人来到黄显年家,送上慰问和祝福。“他对此没有任何抱怨,这种生活态度深深感染了我。”邓建和说。 当地民政部门想把他家纳入低保户,但不管用哪种方法计算,他家人均月收入都远远超过了169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 有人问黄显年月收入多少,回答说2420元,对方吃了一惊:“很高嘛!”黄报之以苦笑。 高州市民政局局长吴家骥说,在高州,特别是农村,还有很多人远比黄显年家境贫困。“我们只能开展一些临时救助,比如送一些慰问金。”邓建和虽表示了对他的同情,但并无更多长期稳定救助办法。 目前,黄显年已接到捐助1万余元,其中7000元是高州市教育局和他退休所在的高州市教师进修学校捐助的。他想利用这笔钱,在寒假里把房屋修补好,这样就不担心老伴的房间漏雨了。 “其实,有时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我已经活了78年,也教了59年书。”在由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三张小桌子组成的寝室里,黄显年突然这样说,“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教满60年。” “世上还是好人多,我相信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好的。”老人很认真地说。 他认为这一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他被打成右派后,被罚给学校喂兔子,学生们就偷偷把青草割好放在路边;“文革”中,他又被逼劳动,一天要挑450公斤石头,先是有一学生家长造了辆鸡公车送他,后有另一修自行车的学生家长把那轴心换成了自行车的轴心,推起来又快又轻松。(记者 袁小兵)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