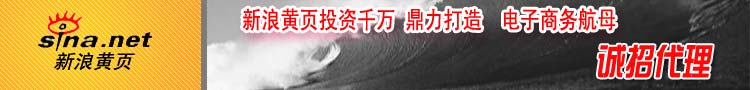探访都市垃圾村里的拾荒者:风湿病是家常便饭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07日09:33 南方农村报 | |||||||||
|
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兴丰垃圾场被誉为“亚洲最大、世界最先进”的垃圾场,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市环卫局便会组织群众去参观这个新式垃圾场,垃圾车、铲车有序作业,已填埋的垃圾被塑料膜覆盖,这里没有拾荒人的存在。 然而,如果你出奇不遇地来到垃圾场,你会发现有一群穿着桔黄色荧光衣、头带怪异帽子的拾荒者,拥簇在垃圾填埋区,他们勾着腰,在潮湿而又令人作呕的垃圾上,像苍蝇
你若再沿着垃圾场入口靠右走,到路灯底下,你就能俯视到这些拾荒人的“领地”——不到1平方公里的山沟里,有五六十个窝棚,地上污水横流,苍蝇乱飞,间或有一些小孩追逐打闹。 2年前,一名刘姓的湖南老板把他们带到这里“安了家”。附近村民把这里叫作“垃圾村”。当记者问及对这一称呼的看法,来自湖南益阳的54岁的老杨笑了笑说:“他们喊我们垃圾村,我们就跟着喊垃圾村,本来就是垃圾村。” 风湿病是家常便饭 垃圾村的人都以拾荒为生,每天他们爬上小山坡,走向垃圾填埋场,他们捡完了一个填埋场,接着去下一个。现在,他们爬上山坡还要走20多分钟的路程才到新的填埋场。 为了节约时间,他们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了中饭,装入保温杯,中午就在垃圾场吃饭。“还有什么味道,早就习惯了,最开始也吃不下。”老杨说。他们有的晚上“上夜班”,戴着有手电的帽子,天不黑就上山,天亮才回来。 “别人上夜班,我可受不了。我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老杨今年54岁,把家里的田租给别人种就和老伴一起出来,他的儿子也在外面打工,他说:“老子打老子的工,儿子打儿子的工,各混各的饭吃。” 然而,令老杨烦恼的是,他来垃圾场不久就患上了风湿病。“每天脚关节痛得厉害。”一个益阳老乡听老杨说起风湿病,他很认真地说:“我保证这里面100个有99个有风湿病,你下次可以带点风湿膏来卖。” 老杨关节痛的时候,一般去镇上买些膏药贴,“也没那么多钱买,痛了才贴膏药,花的都是辛苦钱啊”。有一次,老杨治感冒就花了200多元。而来自衡阳的老王还患有皮肤病,“手痒得不行”,看一趟手,他也花了差不多200元。 垃圾场湿气重,风湿病是家常便饭,但要遭遇了安全事故,那可能是灭顶之灾。有一回,一个姓王的女拾荒者被埋在铲车铲起的垃圾堆里,险些送了性命,经抢救,腰椎还是被压坏了。“铲车开得很快,车又高,司机根本看不到地面。”还有一回,泥头车的车胎突然爆了,一个拾荒者的手被打脱臼。 10月30日早晨,记者打电话给垃圾场一位拾荒者,他告诉记者:“昨天垃圾场压死人了,被压死的是益阳人。”记者还未从其他方面核实这一消息。 老板和厂方(垃圾场)都为安全事故伤透脑筋。现在,每个拾荒者都必须带安全帽、穿荧光衣,而且必须在插了彩旗的安全区域内工作。但,对于身体健康的保护几乎没有,为了防晒,他们把安全帽和捡来的草帽缝在一起,组成了灰色和橙色交错的“铁草帽”,他们的手套都是捡来的一般工匠用的白棉线手套,但他们从不戴口罩。 对于这些危险和伤害,衡阳来的老王说:“我们都习惯了,没什么。”而益阳来的老杨则说:“命要紧,车要来了,隔老远我就跑了。” 老板是主心骨 拾荒人遇到意外事故,老板一般都要“管一管”。刘老板就给了姓王的女拾荒者5000元医疗费。老板既是这群漂泊在外的拾荒人的主心骨,也是他们的经济收入的来源。 在兴丰垃圾场,所有填埋场的拾荒权都承包给了刘老板,也就是要去垃圾场拾荒,必须经过刘老板的同意。刘老板则通过独家低价收购拾荒人捡来的垃圾,再高价卖出,赚取其中的差价。 但这与工厂里工人与老板的关系又不一样,拾荒人自由劳动,多劳多得,也有不参加劳动的权利。“除了身体不舒服,一般人都不会闲着。”老王说。每天把捡来的垃圾过磅,刘老板按已定的价格记账,每个月结算一次,给他们发“工资”。 “一个月一千五六(百元)没问题,多的时候有两千,不会比工厂少,而且都按月发。”记者采访老李时,他正从一本捡来的《武林传奇》中转过神来。他说的是夫妇俩一个月的收入,他们年轻,眼疾手快,合作默契,“有的人只捡一种,但我们什么捡,老板要的都捡,比如膜、铁等等。”他说,他们夫妇俩一个月花三四百元,每月能“积千把块钱”。 工资是他们生活的唯一来源,但每月发工资时,他们还要被扣除一笔“管理费”——刘老板向当地村委租下了那片搭窝棚的土地,他们要在那里住,就要交钱给刘老板,一般100块,少的时候60块。碰上填埋场作业空间狭小,或者有领导检查、市民参观,他们不被允许上山,下雨天他们一般也不上山。有时一个月有1/3的时间不能上山,这时刘老板就把管理费降低。 此外,刘老板还提供简单的入职工具,如每个加入垃圾村的新人,首先去刘老板那领取安全帽、荧光衣。如果有空余的窝棚,他们就自己随便挑一个,略作修缮;如果没有,刘老板会提供木料、铁丝,自己再去垃圾场捡上塑料毡,新的窝棚马上就产生了。 有些人是不用交管理费的,那就是刘老板指定的“队长”。拾荒人主要来自湖南3个地方,按地方不同老板指定了3个队长。平时,垃圾场要传达通知,队长便召集大家开会,“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老王说,他记忆中最近一次会议是在去年下半年。如果一段时间村里的卫生状况太差,刘老板也会让队长通知大家搞好自己室内门外的卫生。 村里派系分明 当然,队长有时也会维护老乡的利益。去年,一个益阳人被怀疑“偷”了垃圾,当场,他并未否认。第二天,刘老板又来找他,他却否认了。刘老板于是动手打了那人。益阳人都觉得老板打人不对,于是联合起来“罢工”,都不上山捡垃圾。但益阳人的“抗议”并未取得多大效果,被怀疑“偷窃”的益阳人最后被“开除”,而其他人仍照常干活。 垃圾村虽小,但并不是铁板一块,就连居住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拾荒人主要来自三个地方:湖南邵阳、益阳和衡阳。垃圾村内唯一的砖瓦房是老板的,因为老板是邵阳人,收购、过磅等杂事多交给邵阳老乡来做。垃圾村内,邵阳人被认为是“管理阶层”,他们的房子分布在垃圾村不同地方,如老板的亲戚与老板一起住唯一的砖瓦房,一个负责收购的人员住在益阳和衡阳的交界处,他开了个小卖部。益阳人和衡阳人则分横竖垂直方向居住。 来自衡阳的老王说,平时,他一般只找衡阳人玩,“与益阳人不熟”。但同一地区邻里之间,他们就像在农村一样,比如谁家做了好吃的,附近的人也来一起吃,有的端着饭碗跑到别人的窝棚里。 这些湖南人多数与老板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而村中唯一的一个四川人则显得有些孤单,这个来自四川南充的彭姓拾荒者风格鲜明,他讲究穿着,“一看以为是老板,皮带上还挂着手机”。过去,与老彭一起来垃圾村的四川人有20多个,后来全部走掉了,就剩他自己。 老彭的窝棚与益阳人在一起,记者说想看看他的窝棚,他说不行,“电视上说的,陌生人不能进入”。在一群人面前,他始终没有说出其他人出走的原因,益阳人都爱拿他开玩笑,他也不生气。 平日里,要是不能上山,三三两两的拾荒者就聚在一起打纸牌、打麻将,还有的就闲坐着。他们赌钱,但数目不大。过去有些人还通宵赌博,现在老板已经不允许了,一个刘老板的亲戚说:“那样影响工作。” 村里有个不到5平方米的商店,主要卖些蔬菜。店里有一台电视机,但没接有线信号,山沟沟里,什么台都收不到,只有放一些捡来的碟子。拾荒人都愿意来这里看电视,因为村里只有两台电视机,另一台在刘老板家里。 冬去春来,拾荒者在这个山沟里平静地生活了2年多,有新来者,也有离开者,大多数一直坚守在这里。如果这个垃圾场关闭了,他们又要开始寻找新的拾荒地。 本报记者 谭翊飞 实习生 海鹏飞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