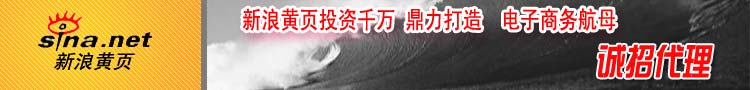摄影师拍摄艾滋孤儿无助生活(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13日04:08 中国青年报 | |||||||||
 曲江涛在跟踪拍摄赵骏 本报讯 (记者 周欣宇) 第一次走进赵骏的家,曲江涛突然喘不上气来。他觉得,空气中弥漫着的,是一种“死亡的味道”。 瘦瘦小小的赵骏,光着上身,挺着皮球一样胀鼓的肚子,面无表情地坐在板凳上。
这个家里有5口人不久前因艾滋病先后辞世,其中包括赵骏的父母。几年前,他们为了获取两袋血换53元钱和一袋鸡蛋糕的收益,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赵骏一出生,便从母体感染了病毒。奶奶因接连失去亲人疯了,而两个叔叔拒绝抚养这个有病的孩子。 不久前,以赵骏为主角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与另外7部影片一起,入围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这些影片中将有3至5部,于明年1月23日获提名,角逐本届奥斯卡桂冠。这部纪录片以安徽阜阳颍州地区的艾滋病儿童为拍摄主题,由旅美华人女导演杨紫烨执导,曲江涛担任摄影。 那种“死亡的味道”,在一年多后的今天,仍然令曲江涛刻骨铭心。每当谈起这个话题,这个30岁的摄影师,总要一支一支地燃起烟,原本轻松的谈话也瞬时变得艰难起来。 “开始时真犯怵,拍了一次之后就不想去了。”他深吸几口烟,一副自嘲的表情。 夏天,曲江涛在艾滋病患者家拍摄,两条腿上被蚊子叮了40多个包。他心想:“这蚊子要是刚咬过艾滋病人怎么办?”去年春节,他和导演又在艾滋病患者家吃饺子。 “说不害怕是骗人,但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因为这些人其实特别敏感。”他笑笑,“但到了后来,我从心里盼着能多去几次。因为有的人,也许下一次就再也见不到了。” 去年春节刚过,曲江涛接到当地人的电话,说赵骏的奶奶去世了。在安徽一家民间机构“阜爱协会”的帮助下,有一对夫妻愿意收养赵骏。他们也都是HIV病毒携带者。闻讯,曲江涛立即坐上从北京开往阜阳的火车。 赵骏被送走的那天,曲江涛是流着泪完成拍摄的。 这个没有人知道确切年龄的孩子,被两个叔叔送到收养者李山峰夫妇的家。新妈妈搂着戴绿色绒线帽、穿黑棉袄的赵骏,一个劲地夸:“这孩子长得真好!”一家人围着他,乐得合不拢嘴。 自始至终,赵骏一直低着头,没有表情。跟踪拍摄几个月了,曲江涛从没听他开口说过话,也没见过他有任何表情。他曾私下问过赵骏的叔叔,这孩子是不是不会说话?叔叔回答说,自从父母去世,赵骏就不再说话了。 傍晚,两位叔叔走了。赵骏还是没说一句话,表情漠然,好像他与整件事无关一样。新家的哥哥领着他出去玩,刚走出院子,却突然发现,两行眼泪在赵骏脏脏的小脸上无声地滚落下来。 “他哭了!他哭了!”小哥哥惊讶地喊起来。赵骏仍然低着头,眼泪泉水一样喷出来,却一声也不吭。 一旁拍摄的曲江涛刹那间理解了这个孩子:“他心里什么都懂,可他能怎么样?所以他什么也不说!”他顿了顿,有些哽咽,“当一个人被踩在最底下的时候,任何事都能平静地接受。这些,平时我们理解不了。” 一年多的拍摄过程中,最令曲江涛感到温暖的,是在赵骏被送到新家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发现,赵骏说话了,甚至会跟他打闹着玩了。 “打你!打你!打死了!”赵骏乐得上气不接下气。曲江涛配合地倒在床上,闭眼,吐舌头。两人玩得不亦乐乎。 “那时候,你会完全忘了他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曲江涛说,“那是赵骏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曾送给赵骏一个黄色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成了这个孩子形影不离的伙伴。 赵骏到新家3个月后的一天,曲江涛拍到了他最喜欢的一幕。新爸爸李山峰抱着赵骏,走在一片金黄色的花海。他们是去接新家的小姐姐放学。赵骏手中举着一大把野花,笑容绽放在小脸上。 “你说,姐姐过来拿花呦!赶快呦!”李山峰这样教赵骏。 “过来拿花呦!赶快呦!”赵骏挥挥手里的花,跟着喊。父子俩同时咯咯地笑起来。 举着摄像机看到这一切,曲江涛的心跟着明朗起来。他以为,这个孩子的苦难也许就此结束了。但是,几个月后,当曲江涛再一次来到阜阳,情况却发生了逆转。 因为国内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的抗艾滋药,赵骏只能按照成人药一半的剂量服用,但副作用大,效果也不好。赵骏的身体越来越差,大小便常常拉在床上,还长时间高烧不退。李山峰一家决定不再收养赵骏了。 曲江涛记得,李山峰倚在门框上,眉头紧紧拧在一起,低沉地说:“不是不想养。可是看到他让我害怕,怕自己有一天跟他一样。” 离开李家前,新妈妈喂赵骏吃药,哄他说:“我的乖,能得很。甜不?” 赵骏费力地咽下药片,瘪瘪嘴,艰难地吐出一个字:“甜。” 最终,赵骏被送往一个新的家庭。在纪录片中,赵骏的故事结束了。曲江涛再也没见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有时候,他会给联系收养赵骏的机构打电话,问问他的情况。他希望能找个时间,再去看看这个孩子。 令曲江涛牵挂的另一个艾滋孤儿王欣欣,是个16岁的漂亮女孩。通过“阜爱协会”,一位美国老太太定期托人给她带来专门的儿童抗艾滋药物。据说,欣欣是已知由母婴方式获得HIV病毒的人群中,存活时间最长的。 曲江涛记得,最初见到欣欣时,她头发乱糟糟地粘成一团,脸色阴沉,脾气暴躁,还不停地咳嗽。跟她熟了以后,他发现,欣欣其实很爱美,特别喜欢偷偷照镜子,梳头发。 “她脾气大,是因为心里的苦没处诉说。”他叹口气说。欣欣的大姐早就出嫁了,婆家听说她的小妹有病,不让回娘家。相依为命的二姐因为害怕,一个人跑了。 曲江涛摇头叹息:“这就是很多艾滋孤儿需要面对的现实,别说外人,就连亲人都歧视他们。” 曲江涛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最初去拍摄时,左邻右舍对艾滋孤儿们似乎都唯恐避之不及,更没有孩子愿意跟他们玩。可渐渐地,人们的态度好像缓和了不少。 “我们去了,总会抱抱他们,在他们家里吃饭。村民慢慢开始觉得,跟他们接触也是安全的。”曲江涛分析说。 据统计,中国约有7.5万个孩子因父母患艾滋病而成为孤儿。“他们遭受着人们的歧视,亲情的冷漠,疾病的折磨。”曲江涛说,“可他们却生活在最没有人注意到的角落。” 长达一年半的拍摄中,十几个艾滋孤儿的故事被收入曲江涛的镜头中,可最后剪辑出的影片只有短短39分钟,多数孩子的故事都被剪掉了,曲江涛觉得颇为遗憾。 他忘不了,一个奶奶一边讲述要把一对双胞胎孙子送人,一边嚎啕大哭的情景。他也忘不了,刚刚失去父母的黄家三姐弟,在给父母上坟时撕心裂肺的哭喊。 因为害怕束缚,曲江涛2001年从新疆电视台辞职来京后,一直拒绝任何固定工作。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自由人”,有感兴趣的题材便忙活上几个月,没有也便乐得自在。他曾用一星期时间,花费600元,以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经历为题材,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短片,居然获得第16届东京录影节优秀作品奖。他也曾拍过有关同性恋的纪录片,甚至有过被男同性恋者追求的尴尬经历。 而现在,曲江涛最大的愿望是,能把这几个孩子的故事一直跟踪下去。“这是很少的值得我长期坚持的事情之一。我突然发觉,如果能一直做这件事,一直和这几个孩子在一起,绝对不是什么束缚,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幸福的事。”他动情地说。 今年6月,在华盛顿电影节上,《颍州的孩子》获得国际卫生纪录片最佳奖。尽管还没有在国内公映,已有一些看过影片的外国人,表示要帮助赵骏和欣欣,并给他们寄去捐款。 然而令曲江涛担心的是,纪录片中拍摄的孩子只是极少数,那7万多个在相同的阴霾里挣扎的艾滋孤儿们,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哀?他们能否得到世人的关爱和帮助? “我能做的,只有用镜头记录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伤痛。”曲江涛摇摇头,“但是,一个人、几个人、一部纪录片的力量毕竟太小了。”(文中赵骏、王欣欣、李山峰为化名)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
|
||
|
孙振军:为煽情非得把艾滋孤儿整哭? (2006-12-05) 澳门青年和艾滋孤儿的特殊友谊 (2006-12-04) 阜阳艾滋孤儿欢欢喜喜归来 (2006-12-04) 温家宝总理世界艾滋病日邀请艾滋孤儿参观中南海 (2006-12-02) 温家宝总理邀请艾滋孤儿及患儿参观中南海 (2006-12-02) 总理邀请艾滋孤儿参观中南海 号召全社会关爱他们 (2006-1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