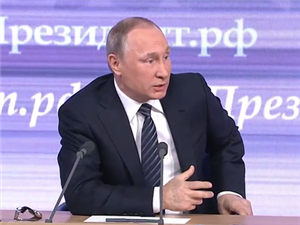拿着申诉状的蔡金森
拿着申诉状的蔡金森
接到再审通知书的那天晚上,堂弟带来一支红酒。二十多年没喝酒的蔡金森,第一次喝这种洋玩意,几杯下肚,就醉了。
他躺在床上恍恍惚惚,似睡非睡。有时梦到村子里鞭炮震天,他正在大摆筵席,每个人都来给他道贺终于平反了;有时又梦到好久不见的三个伙伴,他们终于出狱了,却对他冷若冰霜,责怪他当年把他们拉下水。
终于清醒过来,坐在黑夜中的床上,蔡金森痴痴发呆,他也说不清心中是悲还是喜。
他想起21年前那个走街串巷的下午,想起将他打入黑暗的审判,想起许玉森,想起许金龙,想起张美来,想起前妻,想起狱中20年那喊过无数次的冤。
二十年以后,这身心的枷锁终于要脱了么?
回家
蔡金森接到福建高院再审案件的电话时,正在隔壁村子里的染布厂里上班。
他的工作是检查这些布匹染得是否合格。五颜六色的布,一堆一堆的混搭,常常让他有些头晕目眩。
2014年出狱之后,蔡金森先是跟着亲戚到天津打工。与此同时,他的申诉之路也开始启动。为了方便到福州申诉,蔡金森辞去了在天津的工作,回到福建老家。
他现在的这份染布厂工作,一个月2000多块钱工资,是亲戚们托了几层关系才求来的。厂子里听说蔡金森“杀过人”,一开始没敢轻易收他。“平反了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蔡金森经常念叨的话,也是最有体会的话。
蔡金森还记得,出狱那天,妹妹和堂兄弟来接他,大家大悲大喜,哭红了眼眶。
看着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蔡金森恍恍惚惚。身后那座监狱大门,他这一进一出,从21岁穿越到41岁,却还背着“杀人犯”、“刑满释放”的标签,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外面这个陌生的世界。
换新衣、放鞭炮、跨火盆。回到村子里时,蔡金森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家。“路和房子都变了。”
家里的老房子因为常年失修,已经不能居住。蔡金森出狱前夕,亲戚和村里的乡亲们筹钱给他修了一所房子,他和老父亲有了落脚之处。
回家后的生活让蔡金森措手不及。
刚回家的那阵,蔡金森闻着喷香的肉都不敢吃,担心吃了拉肚子。走进超市,货柜里的食品让他眼花缭乱,太多他都不认识。坐在电脑前,脑子里一片茫然,即使帮他开了机,他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为了给他“开眼界”,叔叔蔡文琴带他去了北京。看到幢幢高楼,蔡金森表示不解,这么高怎么修的?坐地铁时,更是“完全晕了,还差点走丢”。
坐牢之前,年轻的蔡金森走村转巷,帮人补锅。在村民的眼里,这是一项“下等但赚钱”的手艺,一天能赚100多块。蔡金森为人热情,谁家需要帮忙他都会去。这也为他赚来了好口碑。
但现在,他已不敢随便独自走动,怕走丢。“4 1岁的人,说起来真丢人……”
如今,蔡金森的堂兄弟做着钢材生意,他的一些朋友也都盖起了楼房。
“周围的人好像都富了……”蔡金森对着四面空墙的家,既羡慕又失落。
20年的时间,在他和亲朋好友之间无情地划下一道鸿沟,这距离,既有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世界。
如今,即使他再认真地听着朋友讲话,也是似懂非懂,一会就走神了。
噩梦
翻天覆地的不仅是生活,还有蔡金森的个性。
叔叔蔡文琴说,蔡金森入狱之前是个活泼开朗的人,跟谁都能开玩笑。而现在呢,脾气古怪,经常发呆不说话,不知道在想什么。
出狱这段时间,就没看蔡金森笑过。这让蔡文琴一直放不下心。
20年的牢狱,让蔡金森的记忆力和语言能力衰退得厉害,失眠更是像幽灵一般出没于夜晚。
因为失眠,已经20年没抽烟的蔡金森重新染上了烟瘾。几块钱一包的廉价烟,他一支接着一支。
蔡金森还成了惊弓之鸟。蔡文琴记得,他带蔡金森去北京玩,住旅馆的时候遇到公安查房,吓得蔡金森几天不敢出门。半夜一两点,睡得迷迷糊糊的蔡文琴突然被摇醒,蔡金森在黑暗中一脸惊恐,说有人要害他。还有一次,蔡金森做梦大喊:“不要杀我,不要打我。”
加之20年的生活断层,蔡金森的心智和社会经验都让蔡文琴忧心忡忡。“他呀,就像个八九岁的孩子。”
寡言的蔡金森也有唠叨的时候。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当年被刑讯逼供的过程。
开始被打是在南日岛边防所,被吊起来打,先用拳头打,又用木棍打,把木棍都打断了。疼得实在忍不住想喊叫时,被用擦桌子的抹布堵住嘴巴。后来到了莆田刑警队,被轮班打,用夹报纸的夹子打,用扳手打肋骨,不让吃饭睡觉,有时一天就给吃一碗稀饭。
熬不住的蔡金森开始胡乱供述,先说是与父亲、妹妹一起作案。公安说不可能是你家人,只好又供出许玉森、许金龙、张美来等人。
提起许玉森他们,蔡金森更加寡言。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蔡金森还记得开庭那天,四人在被告席上站成一排。没有机会和他们三人说话,蔡金森也不敢说,内疚正吞噬着他。他甚至不敢看他们的眼睛。
判决以后,蔡金森在监狱又遇到了他们。
第一个遇到的是许金龙,他是四人中年纪最小的,被抓时还是个17岁的少年。
许金龙一见到蔡金森就很生气,劈头盖脸地问蔡金森为什么害他。蔡金森讲了被打的情形。
有同样遭遇的许金龙就沉默了。
情义
蔡金森刚进监狱时,逢人就说自己冤枉,无论同监仓狱友,还是监狱管教。
诉说归诉说,喊冤归喊冤,但在实际行动上,蔡金森却没有像同案其他三人那样坚持申诉。在他的认知里,申诉就是不认罪,不认罪就没办法减刑。蔡金森的家境不好,父母亲离婚,没有人能帮他在监狱外面奔走。
所以那20年的蔡金森,在监狱里安安静静地服刑,努力工作,努力表现,争取一次又一次的减刑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我得尽早出去。
在监狱里的20年,蔡金森白天做衣服鞋子,晚上躲在被窝里哭。心情差到极点,他就让同监室的狱友往他胳膊上刻字,工具就是他做鞋子用的针。
蔡金森的胳膊上文着“情深似海,爱重如山”八个大字。这份削皮蚀骨的爱为谁所镌刻?前妻?蔡金森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他说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心情差,随便狱友们在身上文什么。
蔡金森被抓时,21岁,刚刚结婚18天,正是爱意浓烈的时光。被判死缓后,新婚的妻子一直守候着他,这一守就是七年。
七年之痒。
七年之后,眼看出狱无望,蔡金森不忍心让妻子苦等,坚持离婚。18天的相守,七年的等待。蔡金森只能把前妻的这份情义埋在心里。
出狱后,蔡金森打听过前妻的情况。他想去看看她。但他知道他不能去看她。“她现在有自己的家庭,还有两个孩子,挺好。”
柔情被时间碾碎,但生活必须继续。
蔡金森出狱之后,亲戚们就开始给他张罗娶媳妇。说了好几门亲事,对方一听说蔡金森坐过20年牢,还“杀过人”,立马就“灭灯”了。
终于,蔡金森在去年年底结婚了,媳妇是自己的“妹妹”。
在蔡金森被抓的第二年,父亲抱养了一个女儿,取名蔡丽萍。在蔡金森相亲屡次碰壁后,婶婶找到了丽萍。丽萍考虑了很久,终于点了头。丽萍不否认有报恩的心态,“我是蔡家养大的”,蔡金森老实的为人也让她感到安心。她经常嘲笑蔡金森胆子小:“杀鸡杀鸭都不敢,连智能手机也不懂用。”
两个月前,蔡丽萍生下了一个女儿。41岁得女,蔡金森开心得不得了,即使身在农村,他也不介意香火问题,“现在男孩女孩都一样。”
入狱第十个年头时,蔡金森的妈妈病逝,她临死也坚信蔡金森是冤枉的。
蔡金森决定过几天去祭奠母亲,告诉她,案子终于要再审了。20年的牢狱,让母亲临终前都没能见上他一面。
在那个喝醉的夜里,有那么一瞬,蔡金森恍惚见到了母亲20多年前那张年轻温柔的面庞。
采写:南都记者 曹晶晶
编辑:SN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