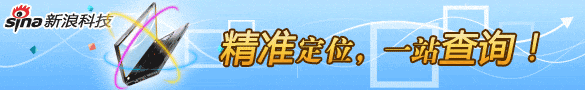媒体重新考究天皇裕仁《终战诏书》
一场“没有结束的战争”
重新考究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我们发现,中日“历史包袱”的纠葛原来是一场不可名状的历史和政治差异的误会。
文|刘怡
关于65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的种种论争也从未停止过。
笔者一位日本好友S君出生于政治世家,和战后数位日本首相皆有亲戚关联,本身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君子,他以礼貌的态度辩称战争是“因为一班拙劣的军人当政,造成了那种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是由真正优秀的日本人来执政领军的话,悲剧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对于大多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而言,他们都和S君持相同观点。那么,日本人的这种情结到底来自于哪里呢?
谜一样的“终战诏”
不无悲壮意味的“忍所难忍、耐所难耐”,来自8“ 15”之日最核心的文件——“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份“终战日密码”,65年来,日本关于二战历史问题的全部论争,都是围绕它展开。而终战诏书在言语、逻辑和叙述方式上,又与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之际颁布的“对美英开战之大诏”紧密相连,结为一体。
终战诏以“兹告尔等臣民”的训诫语气始,以“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的严峻训示终,通篇的叙述仅存在于天皇和臣民两个主体间,却一字没有提及“战败”一事。
在此之前3年多,当“开战大诏”经广播布告于全国时,它的基调亦是自赞自恋的。更荒唐的是,开战诏断言中日问题已经解决,则自终战诏颁布之日起,围绕战争问题所作的一切辩论都应局限于1941年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而此前半个世纪中日本割占台湾、侵略东北、屠城南京之类暴行,就成了“对世界和平做贡献”的“善行”,可以匿而不书。日后将一直纠结不清、有理却难辩的钓鱼岛等岛屿和领海问题,也在这一刻埋下了全部伏笔——真是“孤臣孽子,操心危矣”!
天皇对国民的责任,至此已悉数撇清。国民对此的“回馈”,则是由战败后第一届内阁总理东久迩宫稔彦王,在1945年8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诱导性地提出来的。
东久迩宫的字面表述是:“军官民、全体国民都应该彻底地反省并忏悔,全国人民总忏悔是我国进行重建的第一步。”举出的例子却是什么“作战力量迅速毁坏”、“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统治体制”以及“国民道德的低下”,言下之意,忏悔的原因是没有努力把仗打好,才造成终战诏当中“战局并未好转”的恶果。
比起诏书中洋洋洒洒的体恤之意,这段诱导性讲话已露出了图穷匕见的嘴脸:天皇的宽大隐忍乃是因为他宅心仁厚,尔等自己还是应当沉痛反思、总结教训,以便在日后继续报效朝廷、甘做牛马走。
终战诏及其一系列附属文书的最险恶之处,就在于人为建构了一个完全封闭的责任体系。在此之中,天皇既深明大义又忍辱负重,而在终战诏里一度被体恤的“陆海将兵”、“百官有司”、“一亿众庶”,则应当为自己作战不力、统治不当、道德低下,造成天皇不得不“忍所难忍、耐所难耐”的困境,报以真诚的忏悔。
至于海外各国的反应、被日本所侵略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感受,在此并不重要。是“败战责任”而不是“战争责任”构成这战战兢兢的“一亿总忏悔”的灵魂,而这名实不副的“忏悔”却在日后60多年里屡屡被日本政客利用,作为“日本人民真诚谢罪”的一个佐证。
“国体护持”的幽灵
“终战诏密码”和“一亿总忏悔”的直接产物,便是自东京审判起流毒至今的“军部神话”。
这个以S君口中“一班拙劣的军人当政”、善良的天皇与愚昧的国民皆为其左右作为基本逻辑,以天皇处心积虑、国民心领神会、军人心甘情愿、观察者(亦可称为默许和指使者)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听之任之的“协作”共同炮制的故事,所要掩盖的正是终战诏中隐藏于种种文饰下的实在目标——“维护国体”。
对自明治维新到1945年8月15日为止的日本而言,“国体”绝非空洞的概念词汇。它是以“万世一系之天皇”神话为先导,以天皇家世代相传的“三种神器”为正当性象征,以一身兼有宗教的“现人神”和世俗的政治—军事主导者双重身位的天皇本人作为最重要核心与最终寄托的一整套政教合一体系。
它绝非习惯上所认为的“封建残余”或者属于中世纪的陈腐存在,而是一架借助先进高效的宣传工具、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我们熟悉的“特高课”)与以《治安维持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层叠而成的现代国家机器。
甚至连天皇亲自宣读终战诏的“玉音放送”,都带有浓厚的算计痕迹——当几十年来不闻其身、不见其人的臣民突然从广播中听到“现人神”尖细单调的嗓音时,难道不会产生由衷的恐惧和愧疚之情?而这正是“一亿总忏悔”和“国体护持”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
“国体护持”的关键,在于如何掩盖天皇具有双重身位的事实,将天皇作为最高统帅和开战决策者的身位隐藏起来,使裕仁成为“一亿总忏悔”唯一的受众而非参与者。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昭和天皇及其“忠臣”们得到了负责战后日本占领以及整个政治-经济系统重建的麦克阿瑟及其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默许。
后者出于提前萌发的冷战思维,特别是“防止共产化”的强烈情绪,急需保留作为既有体制最重要支撑物的天皇本人。就这样,在日美双方的合谋下,“军部责任观”这一扭曲的解释在东京审判中粉墨登场,以“忠臣”自居的东条英机等人在主事者的授意下,以大义凛然的悲情姿态成为替死者和“烈士”。
曾经节衣缩食支持侵略战争的“广大日本人民”,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可以替自己免责的解释,然后回过头来继续对那位“万世一系之天皇”进行其“一亿总忏悔”——都解脱了!
必须指出的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耿耿于怀的宪法第9条放弃军队和战争权,与困扰战后日本半个多世纪的冲绳问题以及美国驻军问题,首先是作为昭和天皇“护持国体”的“投名状”交给美方的。
作为再造日本的指导者,麦克阿瑟当然不会允许两位一体、人神合一的天皇制继续存在下去,但他成功地利用了裕仁对“国体护持”的执念,以日本放弃军队、租让冲绳以及颁布《人间宣言》为条件,放弃了对天皇以及日本国民战争责任的追溯,使日本成为无法脱离美国单独存在的小跟班。
在“国体”的法律和机构肌体已被拆除、天皇宣言自己回到“人间”之后,“皇祖考、皇考”的幽灵以及依然飘荡在人世。而他们的“魂兮归来”,就系于表面上仅是历史问题、实则有着巨大政治象征意义的靖国神社参拜。
参拜靖国神社,绝不是什么简单的“悼念战死者”活动。它既是对终战诏人为割裂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此前的侵略史、造成从1874年入侵台湾到1937年—1941年侵华战争中的毙命者“魂无所归”局面的一种补救,亦是以实体形式“护持”昔日“国体”的重要手段。
天皇在丧失作为最高统帅和政治统驭者的“人间”身位之后,依旧是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与阵亡者的最高祭司。战死者为“国体”“捐躯”,其犯下的罪行在神格化之后已经不复存在;而祭祀活动本身又足以唤起生者对死者以及“国体”的愧疚,唤起对原本是战争责任者的天皇的“总忏悔”。祭司与死者“合谋”,生者心照不宣地加以配合,回到“人间”的天皇在祭祀之中又暂时恢复“现人神”的身位,提醒着生者自己的不容置疑。
这就难怪,战后的日本宗教界人士要死死咬住国家神道乃是“祭祀”而非“宗教”。当旁人眼中的神道仅是作为单纯的祭祀仪式保留下来时,它与“国体护持”的暗中勾连却被掩盖了。65年过去,这种神秘莫测的仪式发生的唯一变化,仅仅是主祭者从“现人神”的天皇变成了作为俗世政权领袖和最高决策者的首相而已。
矛盾的话语空间:检证未终了
“国体护持”的成功,在今日造成了如此荒唐的景象:以“爱国分子”自居的日本极右翼,一方面将矛头直指宪法第9条,妄图崛起为拥有常备军与宣战权的“正常国家”,另一方面却不敢也不愿放弃美日安保,时时以日美关系的特殊性质为倚靠。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自居之人,本质上却是压抑日本独立主权和国家性格、反民族主义的魁首,正如同当年日本口口声声鼓吹的“东亚共荣”,实质上却是一派鱼肉乡里、唯我独尊的大骗局一样。
也正是因为这笔过于“丰厚”的历史遗产,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日本政治家始终无法实在地确定一个清楚明白的对外方针,无法以诚实一贯的态度面对世人。倘若他们彻底“向右转”、意欲全盘否认日本对外侵略的责任,则势必触及“对美开战责任”的红线,将昭和天皇苦心掩盖起来的罪责全盘挖出,并直接影响日美特殊关系,造成现有体制的整个崩溃;倘若他们大胆到全部应下“罪在朕躬”的历史责任,则又无从解释围绕着“国体护持”、由全体国民积极参与并最终完成的“战败责任神话”。
靖国神社中的牌位,死去的天皇的魂灵,生者对祖辈所犯罪行的掩饰和逃避,“国体护持”之手段与实质的冲突……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夹杂在一起,远未因时间的流逝而稍有削弱。
笔者截稿时,听闻新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可能模仿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的讲话,于2010年八一五之际发表对中、韩两国的“谢罪谈话”,表达反省和道歉之意。这位首相出生于战后的1946年,未曾亲闻“玉音放送”,大约也和身为80后的S君一样,愿意将战争反省视为纯粹的“历史问题”。然而,当“历史问题”屡屡成为日本国内外政治斗争的焦点,可以一次又一次影响得票率、外贸数据和防务开始时,它真的仅是“历史”吗?在65年前的8月15日以“终战诏”方式宣告封存的这场战争,真的已然彻底终结了吗?
没有,绝对没有。
至少还有那么一个日本人,以自己的整个人生充当了这八一五之日的注脚——1944年12月,毕业于“间谍摇篮”陆军中野学校的小野田宽郎少尉奉命到菲律宾卢邦岛开展游击战。他不愿也无法相信日本已经战败,孤独地指挥着几名同伴,为一个不存在的“帝国”又坚守了近三十年。
当小野田在1974年3月接到过去的上司送来的投降令、走出丛林向警察缴械时,他已经是一个52岁的老人了。这位“最后的鬼子兵”今天依然健在,然而已经无法适应战后的日本社会,只能移居到南美,不时发表一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言论。
在小野田宽郎的时间维度里,一切都还停留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只有在那里,他才能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一个位置。顺着他的视线望去,我们恍惚又看到了默念“忍所难忍、耐所难耐”的昭和天皇,慷慨陈说“军部领导责任”的东条英机,乃至身着祭服参拜靖国神社的历任首相。这些人的眼神空洞而冷漠,面无表情地在错乱的时空里走来走去。
抽文:
昭和天皇已经死去20余年,“现人神”的神话于可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再被恢复。唯独在形式上已经化作历史的“国体”,依旧凭靠其世间的代理人,在每一个终战纪念日从靖国神社里探出头来张望。
图说:
从终战诏书到参拜靖国神社,昭和天皇以一系列苦心孤诣的手法完成了对“国体”的改头换面,代价则是内部问题的外部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