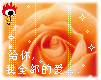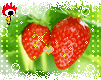| 槟城琐记--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故事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2年09月06日17:23 南风窗 | |||||||||
|
本刊国际问题观察员庄礼伟发自马来西亚槟城 Y道士 从槟城飞返吉隆坡的头天傍晚,我和我的同事与Y道士一起,坐在海边的大伯公庙前吃烤螃蟹。
螃蟹是肥厚甘美的那种,火烤之后几乎不需调料就已有美汁于胸,又仿佛圣境归来已修得舍身饲虎的超然心态,一言不发列于石案上。我们几个人饿虎扑食,一直吃到十指腥黄。那腥黄,赛过天边的夕阳。 Y道士是螃蟹宴的东道,这两天一直陪着我们看槟城的古迹。他拿过美国的比较宗教学学位,在槟城从事华人历史与文化研究,从古老公祠房顶上的一根草,到从“唐山”原物搬来的乡村土地神,他都掌握它们的案底。这是一个极热爱槟州的人。我之所以称他为Y道士,是因为他几乎就是一位道教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且在“全马”某道教组织中高居要职。有一次他来广州,在暨南大学招待所门口的南湖边,和本地的一位博士较量功力。Y道士神气活现地说:“你半夜来,我让你看看这池湖水,都会蒸腾起来!”可见他确实是一位道士,只是头发不够长,不能披发仗剑。 Y道士曾经指导过一位来槟城研究华人问题的日本女博士。那位女博士笔者见过,是一位佳人,只是不敢妄猜年龄。Y道士指导女博士用力甚勤,顺带连自己的学问都长了。而女博士拿了日本某基金会的一笔巨款,早已做好了在槟城尽情折腾的准备。两人先是采取英国式的导师制,师生必在一桌吃饭,于是将槟城万国饮食博览会一般的餐馆一间间吃将过去。后来这种指导研究的体制渐次转为美国风格。女博士喜欢槟城海边的古旧栈桥,于是就租住在沿栈桥而建伸向海中的高脚屋村里。他们俩在印度洋上的水上村庄、在又咸又湿的海风中发生的故事,自然会有点咸湿。 这自然也是一个很幸福浪漫的故事。 大伯公庙右侧的观潮台下,有潮声低低伏地而来,让人在陶然之余醒觉这里是一个岛,孤悬海上。夜里入睡前我仍然在想身处的这个岛,和岛上的这些杂色人群。刚才还从印度夜市中穿过,尚武的泰米尔人做出的面食小点和华人餐馆中的面食小点一样玲珑温存,而且他们和华人摊贩们一样能熬夜做生意。这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我在这里只有两天多时间,半夜里来,坐凌晨最早的班机走,除了古迹没看别的地方,但我已经深深喜欢上这个岛!半夜里来的时候,车行走在13.5公里长的槟威大桥,前方是一个灯火明暗不定的大家伙。夜色、水面皆如泼墨,这其实是一个睡在大陆之外的小家伙,睡得颓然而恬然。走进去,看到沿街老式的骑楼,黑蚂蚁在石柱和旧木梁上忙碌地讨生活,雕花的铸铁栏杆,三轮车夫在昏黄的街灯下瞌睡,于是,立刻就喜欢上这个叫作槟榔屿的岛。 一直想头枕海洋入睡,一直想睡在一个凝滞的时间里,在槟城,慢慢地有了这种感觉。头枕海洋入睡的感觉是如此不同。在陆上坚实的水泥森林的一扇窗里躺着──即便是在空旷的大地中心躺着,仍有一种被一层黄土压着的感觉。而在夜的海上,在波涛轻摇中,灵魂就不知不觉地被托浮起来,自由地化作大星之南的一丝云气。 弗朗西斯·莱特 走进槟城,就走进了过往。在“全球化”这个时髦名词后面,有着长长的、迤逦的航路,有着许许多多像槟城这样的地理和时间上的重要节点,有着南洋华人这样的全球化的早期参与者。 槟城(即乔治城,槟榔屿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坐落在槟榔屿的东北角)位于马六甲海峡面向印度洋的一端,是19世纪欧亚航路上的一个重要口岸,吸引了来自南洋各地、中国、南亚、中东和欧洲等地的诸多商人和移民。像今天Y道士和女博士之间的浪漫故事,在这座混血的破旧低矮的国际化都市(向天空发展的上海浦东新区,则是中国人所诠释的“国际化都市”的范本)中,200多年来已上演了无数。 槟榔屿的开埠,与英国人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有关。这位英国退役海军军官于1786年登陆时,看到岛上森林密布,有许多槟榔树,因此为该岛取名为槟榔屿。1786年是槟榔屿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关键年份,莱特在这一年说服槟榔屿的拥有者吉打苏丹将岛割让给英国东印度公司。莱特原先是想把槟榔屿规划成一个大型种植园,他还命令士兵用大炮把银元发射到森林深处,以鼓励华工前去垦殖。然而由于槟榔屿在欧亚航路上的重要位置,以及周边已经开发出大片的种植区和矿山,它的发展方向被迅速定位为中转橡胶、胡椒、茶叶、布匹、锡锭、瓷器以及豆蔻、丁香的国际商贸口岸。 从重商主义时代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都需要开辟国际贸易网络。在整个19世纪,英国人正是以槟城为重要门户,通过贸易使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全球市场的组成部分。槟城成为了广义的全球化进程(以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为起点)的一个重要节点,并因此而迅速繁荣起来。 非西方地区的都市和市镇的兴起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假如没有像槟城、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雅加达、西贡、科伦坡、马尼拉、上海等等东方都市提供新的活力,假如没有中东、拉美、非洲的本土劳工和商人的辛勤劳动,西方资本主义就会像一个吸不饱血的臭虫,最终被时间的烈风吹干。全球化是由西方和非西方地区共同参与的运动,是双方都从中受惠的运动,尽管非西方地区总是处在不利的游戏地位,但这些地区的活力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它们会有自己强大的心脏,而不必总是依附于西方的“中央处理器”。槟州的演进过程也正在证明这一点,目前她已经转型为马来西亚的高科技工业区。不过,尊重历史的槟州人仍然感激那个给予“第一推动”,把槟榔屿一把推入全球经济的人:莱特先生。在槟州博物馆的院子里,站立着莱特的铸像。莱特没有留下标准画像,槟城人为了缅怀莱特,就依照其公子的画像铸成了现在这张莱特的面容,一张被海风吹过和刻画过的傲慢而执著的面容。 大伯公张理 19世纪的槟城,承受了两股巨大的历史潮流。一个是欧洲势力循海路西来向远东的扩张,一个是中国“出洋”华人南来开拓他们生存环境的新边疆。两股潮流不期然在槟榔屿汇合。此后,华人在南洋再组建一个农耕社会的蓝图很快就被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新方向所替代。华人下南洋是在清帝国走向衰败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天灾人祸不断,迫使东南沿海的农民乘槎浮海,来到过去断续已有上千年往来关系的南洋地区。15世纪郑和下西洋并没有把中国和全球联系在一起,而这群满腹辛酸和满怀希望的破产农民,却成为了最早参与全球化的中国人。 华人具有卓越的市场经济潜能,不过清朝皇帝看不出来,反而称出洋华人为“天朝莠民”。英国人考察了华人在马来亚早期贸易和矿业方面的成就后,便知道这就是最佳商业伙伴和最勤奋的劳动力。1860年英国与中国签订《北京和约》,规定中国政府不得禁阻华民赴英国所属各地或外洋工作,并要查照情形,会订章程,以谋保护。自此中国的海禁政策开始瓦解,华人下南洋的数量迅速增长。 促成槟城开埠的是莱特,不过,槟城的华人都说,若论开拓槟榔屿的早晚,中国客家大埔人张理要比莱特早41年。清乾隆十年(1745年)张理偕同乡丘兆进及福建永定人马福春等冒险出洋,目的地是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但天有不测风云,船被台风吹到了海珠屿(即今之槟榔屿),张理等人成为岛上第一代华人。张、丘、马各有技艺,管理乡人,指导土著,垦地筑屋,立章办学。中国的鲁宾逊们为岛上带来了先进文明,在岛上开辟出最初的“成熟社区”。张理后来在一次采药时不知所终,华人为纪念他,尊他为人格神“大伯公”,后来丘、马二人亦被祀奉为二伯公、三伯公。 欧洲人到来后,华人在槟榔屿的角色有了变化。随着商业法律与契约制度的输入,一部分华人成为最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本土商人”。当然,华人不是以与传统告别的姿态走入近代经济的,相反,他们守住了本族文化中能够带来温暖与和谐的种种根性,并延绵至今。前文中女博士租住的海上村庄,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些村庄又叫“姓氏桥”,共有一个姓氏的宗族乡亲,沿着吞吐货物的栈桥搭建起自己的水上村舍,栈桥于是又成了村中的主街。现在槟城还有若干座这样的“姓氏桥”,如周姓桥、李姓桥、林姓桥。村中居民,仍然是白天以水上生意为生,夜晚头枕海洋入睡。 在大吨位港口时代未到来之前,姓氏桥承担着处理货物吞吐的重任,成为国际资本主义商贸体系的前沿端口。但各姓氏桥(也即“码头运输公司”)在扩大劳动力方面,都是从中国故乡输入同姓族人,使“公司”保持着故乡宗族村落的原样。最前卫的和最传统的零距离共处,这就是华人先辈们参与全球化的个性化方式。 我在姓氏桥伸向海中的尽头处站了一会儿,觉得海水和海风快要把这些活着的历史物证吞噬、剥蚀掉了。 不过在岸上,槟城是全马华人传统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保存得最好的地方。龙山堂邱公司纪念馆,就是这样一个显示华人精神生活内里乾坤的范例。里面有古楼排列的街道,和仿清朝宫殿建造的祠堂,祠堂是福建邱姓宗族的议事、福利和教育中心。电影《安娜与国王》曾经把这里作为一处外景地,朱迪·福斯特留言称赞这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龙山堂在1884年失过一次火,据说失火前景观还要富丽堂皇。不过,失火的原因据说正是因为这里太堂皇而像皇帝的宫殿。可见皇威真是无远弗届,怒气都发到七洲洋外来了。 槟城的建筑和文化都是混血的,华人两层楼的祠堂,一楼是敦实洗练的欧式廊柱,二楼的雕花栏杆是婀娜的马来风格,二楼以上到房顶,则是堂堂正正的中华气象。南洋华人在“文化适应”上的率性和不羁,可见一斑。 位于莱特街的康华利斯堡(Fort Cornwallis)是1786年莱特上岸的地方。堡内有一尊荷兰古炮,当地人叫它“斯理难掰”(Seri Rambai)。据说这尊古炮会有极灵验的力量,盼望生子的妇女们只要把鲜花放在炮管上许个愿,就能如愿以偿。于是有不少华人女子来此许愿,然后回家香汤沐浴静候,只等康华利斯古堡一声炮响,给他们送来又白又嫩的大胖小子。古炮笔者只在旅游图上看到,那个粗黑家伙直直地面朝大海,果然凛凛英姿。 西方的古炮成了华人的圣物,这里有一种时光走岔了道的感觉。槟城的华人文化,就是这样一个不拘一格,海纳百川,最后自成一家的文化演化的典型个案。文化既有承继传统的倾向,也有“本土化”的倾向,南洋华人文化中的本土性,是以南洋而不是中国作为本土,他们在当地作出自由选择和自由发挥,使自己的文化具有了独特的本土特征。 打铜仔街120号 说到自由,我以为,相对而言,清朝下南洋的华人比同时代的中国人享有更多的自由。 华人来到南洋,成为了头枕海洋入睡的人。他们来到了一个新天地,虽然其中也有苦难、压迫和不公平,但这与国内铁屋般密不透风的环境相比,还是大不一样。本来,他们是南中国最没有文化、最没有幸福可言、最破落的农民(南来的华人中几乎没有士大夫阶层中人)。他们来到一个崭新的课堂里,在一个压缩的时间和多元的环境中,学到了比国内士大夫的“智识”和“风范”更先进的文明和生存方式,明白了人间最可追求的价值。他们是最早体验到个人权利、契约制度和自由选择的中国人,他们最终也成为了中国最革命的社群之一,黄花岗起义的志士和烈士中,绝大多数是海外华侨。华人在南洋是最节省最懂得资本积累重要性的族群,但他们在支援中国革命、奔赴国难方面,却从来不吝惜自己的钱财。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与深受自由、民主精神熏陶的海外华人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华人的抗争精神在今天仍在南洋华社中间延续,不过其表现的情景,似乎又多了点后现代的格调。在吉隆坡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人对前来旁听的拉曼学院的华人学生刚说了句“早上好!”,学生们便像对暗号似的齐刷刷地回答:“好—很好—非常好—越来越好—!”紧接着以减员一半的声音低声下气地说:“明天会更好……”这种很好玩的句式听来很反抗,也很压抑。华人以其聪明才智在一个并不完全公平竞争的种族环境中,自然会憋不住发出几声怒吼,并希望这种境况会不断地有所改观;但最后低八度的声音,又透露出一点点自嘲,和不自信。槟城的老城区密集得像老年人的皱纹,里面藏龙卧虎,是很自然的事。与槟城关系最密的知名华人,一个是辜鸿铭,一个是孙中山。孙中山曾在槟城多处逗留,其中最有名的住所,是建于1870年的打铜仔街120号。此屋是同盟会在东南亚的总部,两层深院结构,内有天井,兼有富商豪宅和私会党巢穴的模样。我们来到这里时已是黄昏时分,一楼的陈设基本照旧,都是当时之物,只是墙上多了些镜框,内有当时诸多有关人士的照片和事迹。其中还有槟城富商女儿陈璧君在槟城的旧事。后来她反抗封建家庭,逃婚逃到东京,遇见风度翩翩的革命少年汪精卫,便施展手段,三下五除二地拆散了汪与方君瑛(时任同盟会暗杀部部长)的恋爱关系并取而代之。方是兼具秋瑾和张幼仪品德的大家闺秀,后人议论说,汪如果和方而不是骄横的陈结婚,其结局可能有所不同。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令人惊讶的是,120号仍然是一所私人物业。在槟城读书、租住在120号二楼的广州女孩辛迪开门放我们进来,详尽地给我们介绍屋中文物和故事。她还指点我们看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今年4月来访时留下的签名。来访的中国贵宾当时在一楼会议桌边孙中山的座位上逗留了较长时间,他坐着观看屋内陈设,并听取有关的历史介绍。 据别人介绍,120号与孙中山的关系,是Y道士在10多年前勘定并大力宣传开来的。后来120号有了名,Y道士又极力主张保持120号物业的私人性质,他认为如果以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来宣传孙中山先生,是违背孙中山的信仰的。孙中山尊重民权、忧怀民生,体现他的精神,就必须照顾私人业主的权益,更不能强征过来用于牟取商业利润。所以,120号不收门票,但也不欢迎那些成群结队的观光客。看来,我们能进来,是沾了Y道士的光。 在二楼,看到辛迪整洁而简单的住房。这里的墙上似乎还叠映着历史上来来往往的很多人的身影,没关牢的绿色百叶木窗晚上也许会随风发出吱呀呀的声音。辛迪和另外一两个房客租住楼上的几间客房,大雨的夜晚,栖身古宅,会有怎样的感觉?我们没心没肺地对辛迪说:“这里今天晚上会有人—很多人—非常多人—越来越多人。”然后贴近她耳边诡秘地告诉她:“明天晚上这里会有更多人!”辛迪很配合地扮了一回很怕怕的样子,然后叹了口气说:“在槟城难道会有比这里更有意思的客栈吗?” 相关专题:全球化带来机遇和挑战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全球化带来机遇和挑战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