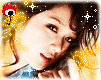| 死里逃生撒哈拉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13日09:01 扬子晚报 | |||||||||
|
1906年,英国探险家汉纳斯·威斯切尔开始了穿越撒哈拉沙漠中心地带的极限之旅。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海尔决定勇敢地踏上同一条路。这两个男人在一点上达成共识,那就是:如果没有强健的骆驼,他们必死无疑。 从死亡之洲回来后,约翰·海尔把他的经历诉诸文字,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撒哈
走进撒哈拉 用刀片在眼睛上动手术需要坚韧的毅力,而握着刀的手绝不能有一丝颤抖。我没勇气接受这样的手术,当约翰尼·帕特森用刀片刺穿贾斯珀·艾文斯左眼眼白里凝固的沙块组织层时,我转过脸去。在我们骑着骆驼横穿撒哈拉的探险中,没有医生随行,贾斯珀充血的左眼里那个肿块可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当约翰尼小心翼翼地撕裂薄膜,让微小的沙粒球状物滑落出来,77岁的贾斯珀毫不畏缩,他没有流血。约翰尼这个我们团队中最年轻的家伙出了名,因为两天后,贾斯珀的眼睛痊愈了。 我们已经骑着骆驼走了4星期了,但我们的这次长征持续了3个月,沿古撒哈拉商道,从乍得湖一直走到地中海边城市的黎波里,全长1500英里。 直到19世纪末,这条路实质上是从撒哈拉南部地区到阿拉伯沿海城镇间运送奴隶的通道,血迹斑驳,尸骨累累。只有最强壮的奴隶才能在沙漠行进中幸存,而活着到达利比亚西南的迈尔祖格的人,也和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了。从19世纪开始,当地的骆驼商人就干脆把这条路用作商道了。据称,最后一次走完全程的记录发生在1906年,这位勇士就是在瑞士出生的英国人汉纳斯·威斯切尔。 威斯切尔是谁? 实际上,我想从靠近尼日利亚北部乍得湖的库卡瓦起程,穿越尼日尔和利比亚到的黎波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威斯切尔的纪念。在英国人心目中,威斯切尔和闻名遐迩的南极洲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并驾齐驱。威斯切尔在尼日利亚北部深入人心,并不是由于他的撒哈拉之行,而是由于他顶住英国的反对,倡导一种革命性的教育制度。这种制度对以穆斯林为主的豪萨人的宗教和背景给予适当的尊重。在英国殖民地的许多地方,这一制度后来都得到了沿袭。 我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威斯切尔的著作《穿越撒哈拉》,它立刻吸引了我。书中描述了荒漠中激动人心的故事,威斯切尔告诉我,在撒哈拉,几天都找不到水,绿洲数量极少,并且相隔遥远。那时,我就被骆驼能在最艰苦的环境、最长的旅途中生存的惊人能力所吸引。威斯切尔提及了充满敌意的部落和四处劫掠的柏柏尔人,轻描淡写地点到九死一生的历险故事,并且释放了商队的奴隶,让这些人沿着古驼道,从的黎波里安全回到他们尼日利亚的家乡。 完成旅行后,威斯切尔向他在“北尼日利亚政治服务局”的上级请示,是否能从乍得湖到的黎波里去。1907年9月19日,他得到冷冰冰的答复——亲爱的威斯切尔: 我更希望我的员工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而不是去寻求个人荣誉或者在国外探寻地理发现。如果你执意要去旅行,你就辞职,把你的位子让给更适合它的人。实话说,我也愿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谨启W.P.休比 近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决定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完成威斯切尔没有成行的远征。经过6个月的等待,我最终获得利比亚当局的许可,骑骆驼穿越这个国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从尼日尔商人希蒂手中买了25只骆驼。此前,希蒂是作为一个柏柏尔人酋长被介绍给我的。通过他,购买探险队必需品还是比较安全的。鞍做好了,绳索也有了,2001年9月初,希蒂的骆驼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我们在尼日尔南部城镇恩格维格密的集合点。 我们远征队的组成情况是: 贾斯珀·艾文斯,来自肯尼亚的骆驼主和牧场主,他曾在1997年和我在中国的戈壁滩调查野生双峰驼的情况。贾斯珀是个很有魅力并且足智多谋的野外生存专家,同时也十分熟悉骆驼的习性,他可以被看作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兽医。 袁国英,远征队里的“教授”,60岁的他已经退休,是来自中国的动物学教授。他曾经给予我巨大的帮助,使我能够获准进入罗布泊研究双峰驼。当时,我试图回报袁教授的好意,邀请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骑骆驼穿越撒哈拉的中国人。 英国人约翰尼·帕特森,他比其他队员要小三十多岁,有长期穿越非洲和亚洲的经历。 卡斯滕·彼得,德国摄影师,越艰难的事情对他来说就越具有吸引力。 另外,还有4个图阿格雷当地人,他们是:希蒂的亲戚艾奥姆、阿格力以及图阿格雷奴隶的后代亚当和阿萨里。我们还雇了3名导游,他们分别了解不同的路段情况。(当年,威斯切尔没有请柏柏尔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们是沙漠掠夺者,专门在驼道沿线抢劫生活在绿洲上的人们。但是我们队伍里的柏柏尔人都非常好,他们知识丰富,诚实又卖力,而且对骆驼非常信任。 远征队一共有25只骆驼,9只是坐骑。另外16只每只要驮90公斤重的行李,它们中的5只身上有棕白相间的条纹。贾斯珀以前通过阅读得知这种骆驼生活在索马里和下撒哈拉地区,但他从未亲眼见过。通常,这种骆驼的眼睛呈蓝色,但我们有两只骆驼的情况比较特别,它们的眼睛,一只蓝色,一只棕色。这5只骆驼都是聋子,这也是这种骆驼的一个显著特点。可是,正因为听不见,它们5个是远征队里最不听指挥的。 当我们离开乍得湖开始艰苦跋涉时,首先来到了大片的灌木丛地带,它广袤无垠,如波浪般起伏,向北迤逦而去,这里就是“提恩土玛高原”。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障碍是看似平常实质却像芒刺一样坚韧的东西。这种小小的、锋利的刺果植物覆盖了全长150英里的整个高原。当时我们已经厌倦了骆驼背上的生活,但由于剧烈的疼痛,又不能下地行走。令我惊奇的是,骆驼因为有一层毛发的保护,腿上不会粘上芒刺。“提恩土玛高原”还潜伏着大大小小的蝎子。尽管我们也曾在睡袋下发现过6只一动不动的蝎子,可它们没有一个蜇人。为了防止蛇的袭击,贾斯珀拿来了一个由电池供电的牛刺。他说,如果迅速使用,电击可以减轻咬伤的影响。他在肯尼亚旅行时曾经用过这个牛刺。幸运的是,我们用不着检测这个可疑的毒蛇咬伤治疗法的效果。 我们在尼日尔的导游是一位叫阿巴的土布族人。土布族是自古存在于撒哈拉的原住民,他们在尼日尔北部、利比亚和乍得靠种椰枣和养牲畜谋生。在威斯切尔的时代之前,土布人和柏柏尔人时常争战,至今仍心存芥蒂。我从希蒂那里了解到,尼日尔土布人正在联合乍得和利比亚边境不满现实的土布人,急不可耐地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老谋深算的希蒂选择了阿巴,因为他知道阿巴和独立运动的关系非同寻常。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任何把我们远征队当作劫掠目标的土布人都会被阿巴轰走。要知道,阿巴每日的薪金,能时刻敦促他带领我们,安然地从尼日尔北上抵达利比亚。与喧嚣而忙碌的现代生活告别,融入一个与机械绝缘的世界,这一切并没有在一天就出现。但我很快学会了怎样干净利落地打包,怎么使用绳子,以及怎样在约翰尼挑剔的眼神下装载木制炊具箱。正午炎热非常,我们巴不得一直呆在树阴下,但我们也认识到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吃饭并不是个好主意。如果我们这样安排,就得把骆驼身上驮的东西卸下来。然后再装上去,这是一项耗时的运动。对我们来说,在劳累一天之后,最好就是把一切交给阿格力和牧人,他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而且我们自始至终坚持这条准则,直到旅行结束。 然而,连续7天,日复一日在毫无特色的草原上行进。约翰尼骑在骆驼上的时候还在看书。我也尝试过这样做,可是一小时后,骆驼摇摆的步伐就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我阅读时不能集中精神驾驭骆驼,这个聪明的动物感觉到了这点,它会自行其是,时常偏离远征队的方向。我还努力回忆脑海中的歌曲和赞美诗,试图歌颂穿越“提恩土玛高原”的旅程。当然,我可以骑着骆驼赶上同伴,和他们聊天,但如果狂风迎面而至,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我们吃力而缓慢地走着,周围的矮树在阵阵热浪中跳动闪耀,这片广袤的高原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尽头。蔚蓝色的天空笼罩着一层灼热的白雾,烈日恶意地摧残着干焦的地表和沙土,汗水在离开毛孔之前就已经蒸发了。有时候,路旁会刮起一个小旋风,卷起细碎草屑,随即就逐渐消散,但一会儿又再度卷起,螺旋越卷越大,迅疾旋转,向灌木丛袭去。然后再一次消散得无影无踪,但突然间,它又从天而降,暴跳着扑向我们,它的声音由瑟瑟低语变化成猛烈的咆哮。旋风卷起一团厚厚的沙尘,将落叶、树枝、碎石卷入旋涡,接着俯冲下来,把刺人的沙尘吹入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还朝我们的脸颊喷吐热气。然后,它再次跳进沙漠里,宛如一个有生命的个体,翻来覆去,左摇右晃,只留下焦渴的我们,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大漠生活 三个星期后,这片炽热的焦土被高耸的沙丘所取代。我们抵达了比尔马大沙漠。此时此刻,我们才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终于来到了真正的骆驼国度。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连汽车都无法征服的地方。有时,沙漠表面非常柔软,骆驼的腿经常会陷入松软的粉状沙中,它们使劲挣扎,曲折前行,向上,越过山丘。爬坡时,它们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下坡时则向前猛冲。运行李的骆驼都用绳索系在一起,排成长长的一列。它们走下陡峭的斜坡时,身材不到5英尺(1英尺=0.30米)高的亚当会在这些骆驼身旁来回奔跑,驱赶它们前进,以确保远征队的步调一致。万一步调不一,系绳就会断裂,那么远征队就会因此分散开来,导致整个队伍暂停,重新调整,重系绳子。 约翰尼的骆驼“艾伯特”从一个陡峭的山丘上滑下,突然开始小跑。毫无准备的约翰尼重重地跌进了沙里。约翰尼气喘吁吁地爬起来,一瘸一拐,所以我们提早扎营。那个夜晚,沉默寡言的阿萨里在沙土里生起一堆火,火烧了一个多小时后熄灭了,只留下一个烧硬了的坑。我们说服约翰尼在火烧过的地方进行热敷治疗,第二天早晨,他的僵硬感逐渐消失了。 穿越沙丘时,贾斯珀的骆驼为了安全起见系在阿格力的骆驼后面,但这也造成一个问题:当贾斯珀需要停下来小解时,他叫“嗨!阿格力”,但这完全是徒劳。他又叫“停一停”,可是他的话经常被误解,而且阿格力的骆驼仍在缓缓前行。豪撒语里,“小解”被叫作“费特萨里”,所以阿格力的骆驼就得到了绰号“费特萨里”。每当贾斯珀大叫“费特萨里”时,阿格力就立刻明白了。 沙丘像是有自己的生命,在沙漠上流动着,这一刻平静安宁,但当风吹散了沙丘,就变成了可怕的漫天风沙。5天后,我们到达了“阿格代姆绿洲”,它坐落在一组绵亘的山脉西边。一股巨大的成就感和解脱感涌上我们心头。教授一刻不停地在类似于饼干碎片的残垣中进进出出,忙着用他喜爱的数码相机拍摄一个法国堡垒的遗迹。尽管,在威斯切尔的时代,沙漠中的绿洲无人居住,现如今,这里却住了一百口人。他们围着一口井搭起一圈简易的泥土房子,他们的孩子朝我们奔来,紧握着他们在沙漠里获得的矛头和箭头。他们在自己做的物品上增添了漂亮的锯齿。从阿格代姆北上比尔马途中,我们又经过了好几个绿洲,每个都被20来英里的流沙隔断。在一片空无一人的绿洲,在这些地区早已消失的长颈鹿、河马还有大象的足印,深深地嵌进古老的干涸的湖底。 夜晚,就在这些被无尽的沙海包围的水洼旁边,我们躺下来休息,头顶上群星闪耀。万物寂静无声,仿佛上帝创世纪前的宁静。全世界似乎只有我们和骆驼的存在。有时候,黎明前的浓雾覆盖了沙漠,天空和沙漠仿佛合而为一了。接着,破晓前漫射的光线拂开雾气和星光,约翰尼起来生火泡茶。 我们的伙食简简单单却有丰富的营养。每晚,阿格力会给每个成员准备饭菜。如果我们在绿洲买了一头羊,那羊身上的所有东西,从脑子到内脏都会配上通心粉、意大利面或米饭。如果有蔬菜的话,也加在里面佐餐。卷心菜和洋葱保存时间最长,而即使是切开最黑最小的卷心菜时,它的菜心仍然新鲜多汁。当肉和蔬菜准备好之后,就轮到用红辣椒和番茄沙司为通心粉调味了,这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剩下的晚饭就留到第二天早饭时加热了吃。午饭就是一袋枣干,一路上边走边吃。 越往北走,晚上越冷(经常在零度以下)。匆匆吃过早饭后,把行李装上骆驼得花一到两个小时。在寒冷的空气里,我们的手指变得僵硬,没法灵活地抓住并用力拖拉冰冷的绳子。我和贾斯珀都没有睡在帐篷里,这样铺床或装载货物比较方便。捆扎行李时,我们被骆驼的呻吟声所淹没。如果所载的重量不均衡,骆驼很快会拉长声音咆哮着,让装货人知道,他做的有多糟。 在我们到达距库卡瓦520英里的古老绿洲“比尔马”时,我对坐骑骆驼“帕夏”的喜爱,与它娴熟地审察沙丘的程度相当。我以威斯切尔在“基德瓦”获得的马的名字,命名了我的骆驼。威斯切尔在马背上能够很快地环绕整个远征队,这样就可以在流血冲突发生之前,阻止随从间的争吵。 骆驼“帕夏”最初野蛮又难以控制。但我充分意识到:赢得动物的心就得满足它的胃。在行进中,我和“帕夏”分享一袋枣子。“嗨,帕夏”,我大声叫唤,它的脑袋会绕着长脖子转动,接住我朝它投去的枣子,然后很灵活地吐出果核。不久,当我叫它的时候,这家伙就像小狗一样靠过来了。 但正如柏柏尔人说的,骆驼和一部分人一样,具有双重性格。某些时候,它顺从而且安静;其他时候,它乖戾和顽固。对付这种小把戏,首先要弄清它当日的心情和相应的反应。这种双重性牵涉到它和远征队其他骆驼的关系。“帕夏”认为它应当得到它的那份食物,甚至是更多。如果它感到自己的份额不够多,就会粗鲁地在对手肩上咬一口。当然,这样的举动同样得付出代价。在10天时间内,我都不能骑“帕夏”,因为鞍子会使它暴露在外的伤情恶化。 “比尔马”是一座由泥砖砌成的城镇。海枣和丛生的青草环绕着这座城镇。比尔马的中心是一眼珍贵的美泉,在荒漠中长途飞行的各种迁徙的鸟儿,会在诱人的草木间小憩。威斯切尔曾经会见过比尔马的柏柏尔酋长麦拿,他形容这位酋长是“半盲,耳聋,跛足,超过100岁”。我们被介绍给麦拿的孙子阿吉·马德·塔赫尔,他是主管比尔马的政府官员,非常有教养。他见到我们很高兴,并且在他家里———镇上惟一的水泥房子里,做了一顿有山羊肉、绵羊肉、米饭和土豆的大餐招待我们。对我们萎缩的胃来说,这桌酒席简直就是饕餮的盛宴。 “您可以带我回英国见见威斯切尔的孩子们吗?”当房间里的电灯泡随着发电机的波动忽大忽小闪烁时,他问道。我礼貌地婉拒,但也意识到假设威斯切尔本人听说这个会面一定欣喜万分。 骆驼断草 沿着比尔马到利比亚国界的通道,我们来到了一片寸草不生的古老荒漠。“没有飞鸟,”威斯切尔这样记载,“没有生物,甚至连极微小的昆虫和杂草,都没法在铺满路面的深色碎石中生长。”我把这些话放在了心上,我提前购买了骆驼吃的草料和我们自己的储备口粮。并不是每个柏柏尔人过去都走过这段路,所以估计要买多少草料比较困难。结果我严重低估了路程的长度(180英里)以及路况。道路两旁骆驼的尸体触目惊心,彻底证明了威斯切尔所描述的:这里是“凄凉的荒原”。 东北风卷起大片的飞沙,将我们的脸吹得像针刺般疼痛。贾斯珀在他的鞍上蜷起身子,用白头巾把自己裹起来。悬挂在他背后的,是一个用来给卫星电话充电的太阳能电池板,这算是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的一种不得已的让步。风妨碍我们对话,所以我坚持努力地看书。但我的努力是徒劳一场,骆驼的步伐引起反胃的感觉,所以我不得不放弃了。这没什么,教授说他计算出我们每小时前后摇摆4000次。“如果我们花100天,每天行进10个小时,那么我们就会摇摆四百万次,”他评论道,“我可是‘中国第一人’啊,应该写进吉尼斯世界纪录!” 经过五个乏味的白天和阴冷的夜晚之后,我们终于到达破旧的图穆边境哨所,在这里,利比亚士兵和警察用一个简明扼要但态度强硬的通知——“禁止外国人通过”,挡住我们的去路。无奈,我们等待了两天,许可证才从上面办下来。事前的准备产生了效果。 路况变得更差了。荒野中寒冷的风呼啸而过,发出刺耳的声音,尘土和飞沙径直扑向我们的脸。教授由于疲乏,蜷缩着身体骑在骆驼上。他的头巾像绷带一样捆扎在脑袋上,活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头部受伤的士兵。 我对骆驼口粮的误算现在暴露出来了,在我们到达利比亚境内第一个绿洲“塔加西”之前,骆驼得饿着肚子再走3天。骆驼滴水不进可以坚持超过7天,但如果它们在恶劣环境下消耗太多体力,就必须进食。我朝最坏处想,我们的骆驼也可能变成路边的尸骨。 骆驼断草第一晚的情形简直糟透了。我们睡在坚如岩石的墓石群旁,靠它们挡风,饥饿的骆驼可怜巴巴地站在周围凝视着我们,好像在说:“你们在做什么?我们整日为你们辛勤工作,可我们的食物在哪里?”我惭愧难当。第二天早晨,骆驼呼出的难闻口气证实了它们的胃空磨了一整夜。 狠了狠心,我们又往它们身上装了行李。后来,奇迹发生了。我们到达了另一个旅行队头天晚上扎营的地方。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有足够的草料——可能是太多了,他们甚至丢了一些在沙地上。我们欢呼雀跃,赶紧用手把草拢到一起,从里面挑出沙子。第二天,奇迹再次发生,我们在另一个营地找到了更多剩余的草料。 凄凉的荒原在我们几乎“弹尽粮绝”之时又抛出一个救命锦囊。一连几天,我们也缺少维持体力的必需品:酒。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我们发现沙里躺着一个袋子。阿格力跑过去查看。使我们惊异的是,袋子里装着几瓶一公升装的威士忌。某个可怜的旅行者一定是在快到图穆边检站时慌了神,把他携带的这些违禁品丢弃在这里了。我们拿了两瓶酒,并且向上天祷告,表达我们的谢意。 威士忌和草帮我们渡过了难关,我们终于到达了重要的绿洲城镇“卡特伦恩”。自从10月24日离开库拉瓦,整整两个月时间,我从没有从镜子里看过自己的脸。虽然我操纵剃刀穿过脸上的沟沟壑壑,沿着下巴那饱经风霜的轮廓,尽我所能地刮脸。但现在我面对真相时,那一幕并不雅观。 幽灵来访 第二天就是圣诞节。这一天也是贾斯珀和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光(他儿子在新年前夕要结婚了,他要搭公共汽车回肯尼亚。我们所有人,包括骆驼在内,都会很想念他的),我无法抗拒心中的愿望,要把自己装扮得整洁潇洒。我想摆脱顶着一头乱发的疯狂科学家形象,沉湎于对刮脸的奢望中,我去了理发店。当地可怜的理发师阿布杜勒,在看到他的这位怪异的客人时,微微有些紧张。 阿布杜勒的年纪大概在四十岁上下,长得圆圆胖胖,穿了一件肮脏的白衬衫和一条沾有污渍的长裤。他有种令人不安的肌肉抽搐现象。每隔几秒钟,他的头就会不知不觉地朝左边抽动几下,我无端地想知道:他的手是否能用这把微微闪光的“杀人剃刀”,平滑地剃掉我的胡须。他一只手举起一把剪刀,另一只手拿着一把手术剪刀,在我的面前挥动着。我用力地指向那把剪刀,片刻之后,他过度热情地把手插入我泛灰的头发。第一刀剪下去,我就知道毁了,而当他结束“手术”时,我已经被修剪成一只仲夏的老山羊了。 当我们进入“迈尔祖格”沙漠时,鹅卵石和页岩地面被广袤的沙漠取代。教授兴奋地叫我们看蝴蝶。它们正在迁徙吗?还有蜻蜓。离开了水,它们究竟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呢?然而,我们的骆驼看到的却是其他东西,在一片风光如画、无人居住的绿洲,它们不愿在那里过夜,它们成群结队四处乱窜。然后,它们会突然停下来,凝视着天空,接着又朝向另一个方向走动。 同往常一样,阿格力总是能作出解释。“这儿有邪恶的幽灵,”他向我吐露这个秘密,“这些幽灵在戏弄骆驼,还试图骑骆驼。我们快点离开这里,越快越好。”那个晚上是新年前夕,温度降到华氏23度。第二天清晨,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骆驼恢复了任劳任怨、坚定而不屈的步调,每小时行进两到三英里路。而那些不安宁的幽灵,则留在鬼魂出没的绿洲,继续无拘无束地嬉戏玩闹。 和许多其他的利比亚镇区一样,古老的“迈尔祖格”骆驼驿站,在上世纪70年代,由于当地的干打垒聚居地(威斯切尔所说的“瘟疫和热病区”),由政府下令彻底清理,居民搬迁到用混凝土修筑的新镇。我在“玛祖克”废墟和雄伟的古炮台闲荡,轰然倒塌的清真寺和坍陷房屋的地基,乱糟糟地堆满生锈的罐头和破裂的瓶子。我们没办法像威斯切尔一样在这里休养生息,一呆就是一个多月,我们只不过逗留了一天。 费赞是一个遍布绿色植物、气候温和的绿洲。在通过费赞后,我们遭遇了巨大的超过400英尺高的沙丘。这些引人注目的沙丘,环绕着神秘的沙漠之湖。我心存焦虑地看着这些沙丘。骆驼身体结实而且消瘦(到现在,我们也一样),但是穿越这些巨大沙丘所需的努力,令人望而却步。 在此前一些时候,我们有了一位新的导游,他是利比亚柏柏尔人,名叫西寇。他戴着巨大的头巾,身着宽大的长袍,就像从《指环王》或是《阿拉丁》里走出来的精灵。他有种无法抗拒的冲动,想与所能见到的任何人交谈,这点和他的装束很配。如果没人和他说话,他会自言自语。向前不远,就是我们最难克服的障碍哈马达哈穆纳——南北与东西延伸达300英里,遍布岩石贫瘠的一个高原。威斯切尔曾总结说是“撒哈拉所有沙漠里最艰难的一个,欢声笑语在这里终止,甚至人声都被淹没。”威斯切尔错了。没有东西可以淹没西寇的声音,他从不会停止说话。 走向胜利 与其说他是个向导,不如说是个“演说家”。不久他就迷失了方向。在情况最好的时候,穿越哈马达·哈穆纳高原,预期只要花6天时间。但当我们到达高原的时候,西寇完全失去了方向。由于搞错了方向,他把我们的计划又延长了两天。 登上高原时,我的内心充满忧虑。骆驼累了,有一些几乎是筋疲力尽,其中的一两匹已经开始跌倒,这是不好的征兆。走到半途,有那么一瞬间,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威斯切尔出现在我身后,并且对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头两天里,我们发现了一丛够骆驼填饱肚子的粗草。但之后,有两匹骆驼很明显完全没有力气了,我希望它们能挺住。只要它们坚持6天,就能到达高原北麓的塔巴尼耶,在那儿,茂盛的植物会把它们团团包围,它们可以尽情享用美餐,好好休息,这样就能恢复健康了。 阿格力和阿萨里为两只骆驼中的一只制作了靴子,这可以帮助它克服脚的开裂和肿胀带来的疼痛感。首先是用羊皮,结果在一天内就被锋利的石块磨成了碎片,然后又用卡车轮胎结实的内胎做靴子。这让那匹骆驼又坚持走了两天,但它实在太疲倦了,不能再走了。我的日志里写着:“酷寒的夜,洗手盆里半英寸深的水冻成冰了……下午四点,我不得不丢下这匹筋疲力尽的骆驼,它拖着绳子,缓慢而费力地走着。远远落在远征队其他骆驼的后面。我真的不愿放弃它,但是我也知道,现在已别无选择了。这匹可怜的骆驼,在这段艰难的旅程,全心全意为我们效力,但现在,我们解开它身上的绳子,离开它,留下它独自面对不可避免的结局。” 不久,我们又放弃了第二只骆驼。假如我们有枪,我一定会帮它更快地解脱。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割断它的喉咙,但我没办法这么做,柏柏尔人也不会,他们决不杀骆驼。 第二天,西寇也被放走了,上了一辆篷车,那是我们几天以来看到的第一辆车。车上的人在沙漠里急速穿行,追赶瞪羚。对于西寇的离开,我们所有人都如释重负。阿格力接替他做我们的导游,借助一点运气,带着我们沿着悬崖峭壁到了一个通向塔巴尼耶井的狭长山谷。那里到处是骆驼喜欢的怪柳和刺槐,你很容易想象到这样的情景,从罗马时代起,往南的旅行队在启程征服哈马达·哈穆纳高原之前,就在这里歇息。 现在,我们向旅程的最后一站——北边的米兹达镇出发。比米兹达更远的地方,是一片纵横交错延伸的城郊,这是威斯切尔不知道的地方了。这里通向利比亚熙熙攘攘的首都的黎波里,那里再也容不下骆驼。我们第一次走在了柏油马路上。司机看来是因为我们“可怜的外表”而心生怜悯,减慢车速并且从车里向我们扔来一团团面包。 我们在米兹达镇外5英里远的地方安营扎寨,寻找骆驼买主。利比亚人特别喜欢吃骆驼肉,我下定决心,绝对不把一路上为我们效力的骆驼卖给拿着长刀的小贩。最终,我把骆驼卖给了一个旅游承办商。我热切地希望自己能说服他,让他相信:一旦休息好,这些骆驼就为他从外国游客获得丰厚的回报。 奔涌的车流,和冷着脸的商人疯狂还价,任劳任怨的骆驼们的神秘表情,和柏柏尔人的深情道别,都迫使我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离开纷繁芜杂的尘世,在骆驼和威斯切尔的那片悠悠天地里漫游的100天,就这样终于结束了。我出神地仰望着米兹达四面荒凉而平顶的大山,不由得陷入了沉思:无论人类这一不速之客给沙漠带来多大的改变,它们将仍然存在着。沙漠的风在黑色岩石上留下的痕迹,见证了这里永恒不变的苍凉。沈路莎 石志宏 马嘉 编译自美国《国家地理》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际新闻 > 正文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