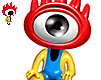| 沙龙的战争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24日14:27 扬子晚报 | |||||||||
|
从耶路撒冷蜿蜒而来的公路从小山上下来后,就开始笔直地在以色列濒海平原上延伸,在拉特伦交叉路口往右拐,就可驶抵以色列现任总理阿里尔·沙龙的大农场。在左面的一处坡地上,是拉特伦红顶的特拉派(天主教中强调缄口苦修的教派)修道院。 作为许多个世纪以来包裹着拉特伦小山的血腥暴力唯一见证的,就是修道院上方山顶上的一片大理石废墟。这是12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一处堡垒的遗存。在那一高地上,基督教战
“这家伙还喝了血” 沙龙几乎战死在那里。在这座小山的脚下,碧绿的葡萄园和金色的稻田正由丛生的灌木分隔开来,而在1948年的阿以战争也就是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中,作为一名20岁的排长,他参与了一次计划很糟糕的攻击,想要拿下这座小山,打开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结果在一连好多个小时内,他和手下被对方死死地困在那里,他腹部和大腿都中了弹。电台被打坏了,没有听到撤退的命令,直到看到身后小山上的阿拉伯士兵,他才意识到自己和手下已被独自留在阵地上。 上月一个周日的晚上,在沙龙的农场上,我问当他的车队现在驶过拉特伦时,他看到的是麦地还是战斗。他说想到的是战场。他说:“那天相当热。身体四周都在燃烧。”地里那天着了火。当他意识到困境并下令撤退也就是逃离时,35人中只有4人毫发无损。沙龙的伤口上流着血,他感觉自己太虚弱,快挺不过去了。 “我那时渴死了,”他说,“我感觉自己再也无力行动了,这可以说是我历来最艰辛的一次努力。” 他自己挪到了溪谷底,血水和粪肥上的绿色泡沫在那里交织在一起。“我犹豫了一分钟,”他说,“然后就将嘴伸到了泥浆里喝了起来,我得说,我喝下了大口大口的这种棕绿色泥浆。” 他开始笑了起来,神情温和而不带苦涩,还带着点真正的快乐,我们在交谈中说起一些特别可怕的事情时,他都表现出这样一种神情。他斜倚在一张黄色的软垫轮椅上,很随便地穿着凉鞋、休闲裤,蓝衬衫最上面的两颗纽扣敞开着,袖子也卷了起来。“我明白这确实很可怕。人们读到这个故事后会说:“看啊,这家伙还喝了血。”他开始大笑起来,晃动着凳子,“但我感觉到我如果不喝那‘水’,我就熬不过去。” 血腥记忆成时尚 当我通过层层安保拐进沙龙的客厅时,我脑海中留下了一道深刻的印象。在见识了这么多持枪警戒的卫兵后,我发现他静静地独自坐在那里:松软的椅子上,一位松弛的老人,一位带着太多记忆的老人。 现年76岁的沙龙,完全可以声称,从大卫·本·古里安以来,无论是好还是坏,他在塑造以色列的地域与道义面貌以及国际形象上发挥的作用,都比以色列任何其他领导人要大。 在1950年代,沙龙训练并领导着突击队,为以色列确立了无情报复的名声;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他赢得了最为漂亮的战斗之一;1973年,他富于想像力地率领部下跨过苏伊士运河,帮助结束了“赎罪日战争”。1973年,他创建了他现在领导着的右派利库德党,打破了工党对以色列政府的控制;他领导了1982年对黎巴嫩的入侵,这塑造也伤害了整整一代人;他策划了以色列的定居点建造计划,系统性地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当中,安插了一个个犹太人据点。 现在作为总理的他,正在建造一堵对付巴勒斯坦人的安全墙,这是自“六日战争”以来,对这片土地作出的最大的变化。他还试图拔掉他在加沙和西岸建造的一些定居点,而以色列以前的总理中谁也没这样做过。他这样做,并非因为他认为这是即刻通向和平的道路。利用白宫当局与他对世界抱有很相似的看法这一有利情势,他正竭力加强以色列应对冲突的力量,这些冲突并不只是与巴勒斯坦人,而且目前他也看不到这些冲突会有尽头。 “没看到有任何改变” 我问他是否认为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已经结束。我说,毕竟世界对于恐怖主义的态度在9·11以后已经转变,而且美国人现在正驻扎在约旦的邻国伊拉克。在拉特伦之战半个多世纪以后,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看来并没有被赶下大海的危险。 沙龙指出说,和1948年时不同,以色列现在与它的两个邻国埃及和约旦已缔结和约。“但这些和约仅仅是领导人之间的,”他说,“在国家或者人民之间并没有。而且主要的问题是阿拉伯人仍然没有作好缔结和平的努力,我也不知道他们将来能不能,他们还没准备好承认以色列在犹太人的故园建立独立犹太国家的天然权利。” “在这一问题上,”他提高嗓门说,“我仍然没看到有任何改变。” 他并不是宗教虔诚人士。出于其自身经历,他对宗教表示出的敬意都是中规中矩的,但这些敬意常被应用到疆土开拓和种族情感,而不是在精神信仰上。在我问作为犹太人对于他意味着什么时,他谈论的不是上帝,而是历史和地名:耶路撒冷、希伯伦、塔伯峰,这些出自《圣经》中的地名,今天仍然在称呼着同样一些地方。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说,“因为我想,那时存在的所有国家,后来都消失了,现在再也不存在了,但犹太人还存在着。” 然后他向我描述了他对征战的感想。提及以色列古代一部族时,他说:“当我走过以前属于本亚明部族的群山——比如说拉马拉或者其西部时,我常常微闭着眼睛,这时我看到的不再是电网和所有这些东西。”他吃吃笑了起来,这回明显是因为快乐,“在想象中,我经常觉得看到了本亚明部族的战士,他们正带着长矛,冲那些地方冲杀下来。” 他又说:“你知道,那些地方以前并不是由阿拉伯人开拓的。那都是犹太人旧时占有的地方。” 和平无路可走 在二月份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当时正在阿里尔镇上“家庭比萨快递”餐馆的一张塑料餐桌上吃午饭。餐馆的壁画上都是美国旧时名人:亨弗莱·鲍嘉、猫王等等。邻桌的那名女子有一个钱包,钱包上绣着玫瑰花和“爱滋养万物”字样。在我桌子下方的庭院里,一枚散失的子弹正在闪闪发亮。沙龙也许正筹划着解散加沙的定居点,但在这儿的小山上,起重机正在忙碌着修建新住宅。这处新的地产叫做阿里尔高地。 在阿里尔的围墙之外,只有几百码远但如同隔着一条银河那么远的地方,是巴勒斯坦人的萨尔菲特镇。我有过蜷伏在一块墓碑后的经历,悼念者正在举行葬礼,而阿里尔一处哨卡上的以色列士兵,同时在朝对面发起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开火。“想到以色列时你能不想到恐惧吗?”我吃午餐时的同伴德罗尔·埃克提斯问。“每当有一辆公共汽车遭炸”,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的士气就遭受一次重击,他对以色列如此强大又如此脆弱困惑不已。 沙龙承认说:“埃克提斯认识到了犹太民族最深切的心病。他理解恐惧。” 36岁的埃克提斯的一只耳朵上,戴着个小小的金环,对于沙龙来说,这种人也许是最可怕的噩梦。埃克提斯是以色列人,也是犹太人,曾经还是一名伞兵,他对西岸地区的小山和溪谷的了解,也许和沙龙差不多。但他从自己的军旅生活中得出结论说,占领正在毁灭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埃克提斯现在正为以色列激进组织“即刻和平”监视着定居点的扩张动作。 像希伯伦的微小的犹太定居点和崎岖山岭上的前哨村落,就是定居点扩张运动的灵魂所在。但运动的躯干和大脑,在阳光明媚的阿里尔小镇。媒体关注的大多是那些狂热分子,而且更多关注的是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也就是说,它们分散了世人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阿里尔带着它的大学和翡翠般的足球场,它的警察总部和前往特拉维夫的通勤车,正在稳步地扩张,而这种扩张几乎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而阿里尔这样庞大的定居点,正是沙龙极力永远保留的东西。这些巨大的综合建筑体保护着战略高地,而它们下面的无比珍贵的蓄水层,正是他最在意的,而且它们隔离着耶路撒冷。他们肢解了巴勒斯坦人渴望建立的任何形式的国家,因而能轻易对其进行监视,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由以色列予以控制。 从阿里尔高地上,你朝东面眺望,就可以看出以色列人的这种盘算。前哨村落正在每一座山头上扩张,以色列定居点形成的一条蜿蜒曲折的长链,横贯西岸地区,直抵约旦河谷。一位助手说,沙龙希望牢牢保住西岸一半的地方,但预计最终无法保住那么多。 埃克提斯坚持认为,以色列正在西岸地区制造种族隔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正生活在并行的社区里,使用着各自分离而不对等的道路系统、司法制度,有着不对等的机会和权利,而且几乎没多少往来。“阿里尔是以色列最为以色列化的城镇,”他相当刻薄地说。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斜躺进椅子里,伸出双手指着每个方向。“忽视民众的存在——完全不顾150或者200米开外的另一方人,生活在心理上和文化上的贫民窟里,不理会自己的邻居到底是谁。” 但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看来,埃克提斯是彻底地误解了巴以的情势。他们的看法是如此地根深蒂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来就不想要和平。频频出现的肉弹以及其他令人寒心的事件,削弱了以色列左翼力量,使得沙龙频频出招,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并牢牢控制住它。甚至连埃克提斯这样的鸽派人士,也怀疑以色列全面撤离西岸地区是否一定能带来和平。 最新一位挑战沙龙及其冲突观的工党政治家,是前将军、海法市卓有建树的市长阿姆兰·米兹纳。去年1月,沙龙曾在全国大选中给工党带来空前惨痛的打击,而在那时的一周前,我听到米兹纳面对成千上万的准备退役的军人,描述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一蓝图与沙龙现在追求的目标很接近,不过有两个关键的差异:米兹纳倾向于与巴勒斯坦当局——这意味着阿拉法特——立即举行会谈,同时立即撤出加沙。第二大差异就是,米兹纳不是沙龙。正如以色列政治理论家亚龙·伊兹纳希有一次告诉我的那样,以色列人选中沙龙,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相信:沙龙只有完全出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时,才会作出让步。“当沙龙也改变时,这意味着再没有谁能扛得住了,”他说。 那天晚上在海法,当米兹纳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并没给士兵留下多少印象。在沙龙的以色列,年轻人谴责老年人爱做梦。“他是有远见的,”那时22岁的战士阿萨夫·门泽尔对我说,“但这在中东是不现实的。以色列的政治史表明,任何人想要朝和平迈出一步——就像米兹纳这样,都是要失败的。” 不幸的家庭生活 在我们的小车获准进入沙龙“无花果农场”的第一道铁门前,我被彻底地搜身。入口看起来就是个密封的罐子,在第二道铁门升起前,第一道必须关上。“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将沙龙变成一个囚犯,”在我们前行时,陪同的沙龙发言人纳安南·吉辛咕哝着说。就在我们前头,一个大窝棚下呆着数以百计的绵羊,这也许是世界上最为安全的绵羊了。还有几只鹅在路上摇摇摆摆。 这农场据说是全以色列最大的,但住宅本身简朴而平常。一进入沙龙家中,就无意识地想起:这个世界名人中最为极端化的人物,这个体现了犹太人的力量与犹太人的残酷的卡通式人物,毕竟也是一个有着深度和复杂性,满载着满足和悲伤的人,这种丰富性也许还超出了他本来的份额。沙龙的首任妻子加莉1962年死于撞车。5年后,他们10岁的儿子古尔意外丧生。古尔当时正在玩弄朋友为沙龙从刚占领的西岸带回的一把古董手枪。没有人知道这枪是上了子弹的。沙龙听到了枪声,找到了孩子,孩子就在他怀里去世。 到这时,沙龙已经与妻妹莉莉结婚,又生了两个儿子。但在2000年3月沙龙当选总理前,莉莉又死于癌症。但她的影响仍萦绕在农场里。在客厅里,一座铜牛塑像竖立在一张桌子上,两个铜舞女正在手牵手旋转。这里留有的惟一一点军事生活痕迹,就是一面墙上炭粉画中的一队看起来很疲惫的巡逻兵。一名荷枪实弹的安全人员就站在沙龙视线之外的走廊里,在会谈中一直观察着我。“我整个一生都在保护犹太人,但你知道,我突然之间就成了防止遭到犹太人袭击的保护对象,”他说。 酝酿政治大变局 沙龙正准备第二天和他的老友、无可回避而又不折不挠的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会晤,商谈组建新的联合政府。在脱离计划带来的纷争面前,沙龙的右翼联盟正在解体。那些极右翼部长们开始意识到沙龙是不可抑止的,于是开始造反。 沙龙正打算至少要组建一个由利库德集团、工党和中间派“变革运动”掌舵的临时联合政府。但沙龙并不认为联盟能持续多久。在公开反对巴勒斯坦人建立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利库德集团中,有一大帮人正沸反盈天。沙龙的助手们说,他预计将不得不于明年举行大选,然后才能启动他的计划,着手拔除加沙的犹太人定居点。即使其计划失败或者自身下野,沙龙也彻底动摇了定居运动的基本信念。这位定居运动之父已经宣称:留在加沙将削弱以色列。 现在他思虑的恰恰就是以色列的政治大重整,它将同时惩戒左派和右派:承认某种有限形式的巴勒斯坦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同时承认与巴勒斯坦人缔结任何形式和平的不可能性。这可能意味着重新定义利库德党,或者创建一个新的中间路线政党。对于沙龙来说,这并不要紧。他从来不会将结果与手段混淆。军队、政党甚至定居点,都只是工具。 对于以色列负面形象的形成,沙龙要承担不少的责任。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曾经传唤他,要他解释他在1953年对当时约旦治下的西岸地区奇比亚村的袭击行为。沙龙当时对一名以色列妇女及其两个小不点孩子遇难进行报复。沙龙后来说,他和手下认为他们在数小时内炸掉的45栋住宅都是空的。但结果有69名阿拉伯人被杀,其中有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这些杀戮导致以色列首次遭到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沙龙对于武力的使用,都让那些向往以色列强悍的人激动不已,也让许多人确信以色列是他们在这个不可预知世界的庇护所,正如沙龙所言,这是惟一一个“犹太人能自行保护自己”的地方。但他也让许多人沮丧不已,他们曾经希望以色列可能成为一座道义的灯塔,或者说希望它能像其他国家一样,成为一个能被世人接纳的正常国家。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支持是以色列未来的希望。这就是它从加沙地带撤离和选择修造隔离墙的着眼点。脱离计划就是试图让以色列背离其所在的地区,向西瞩目欧盟和美国。在奥斯陆和平协议之前很久的时候起,以色列梦想过要与邻居们融入一个新的中东。他们现在愿意等等看。也许巴勒斯坦人能转过弯来,建立一个民主的和平主义的政府。也许它不会。这无关紧要。 沙龙的那名顾问说,隔离墙是“一堵实在的和心理上的墙”,而且心理上的作用更为重要。“我们真正想做的,就是背离阿拉伯人,再也不和他们交往,”在总结他所认为的以色列人的压倒性观点时,他这样说,“我们再也不想被接纳进中东了。”另一名顶级顾问这样谈论沙龙的计划:“这可能有助于巴勒斯坦人。也可能伤害他们。我们不在乎。” 我曾问沙龙是否还像他曾经写过的那样,仍相信能在阿拉伯人中灌输一种“挫败的心理”,他扭头盯着我。“不,”但沉默片刻后他又说,“我想,如果以色列表现出脆弱,那将导致无尽的战斗。” 沙龙曾经对我说,“如果环境有所不同”,他很可能会选择务农而不是军旅生涯。“我本来就不愿以色列以战士的形象而知名。”他说。 的确,对于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梦想中的以色列,更多的是特拉维夫的欢快气息,而不是耶路撒冷的血腥噩梦,他们更中意的是沙龙桌子上的铜制舞蹈少女,而不是沿着围墙巡逻的疲惫士兵。石志宏 编译 宋世锋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际新闻 > 正文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