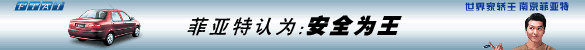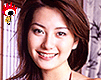德国的出路:1945年5月8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09日02:20 东方早报 | ||||||||
|
他们都是德国人,他们亲历了那段历史,他们听到德国战败的消息时,有的是在英国战俘营,有的是在美国战俘营,也有的在家中疗伤,还有的已经忙于战后的日常生活安排。 作为战败国,德国人究竟是如何看待1945年5月8日这个二战胜利日?2005年5月6日,《法兰克福汇报》记者斯特凡·奥斯特和弗兰克带着“1945年5月8日您在做什么?”的问题开始与一些时代见证者的对话。受访者有前总统魏茨泽克、前总理施密特,还有从事纳粹历
德国人不否认希特勒是自己民族历史中的污点,更坚持不断反省普通人的罪责;与此同时,他们还尝试去纪念参加抵抗运动的德国英雄们,尝试去挖掘因为不妥协而被纳粹迫害的德国受难者们。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人希望告诉世界,尽管有战争狂人希特勒,尽管有军国主义的大量拥护者,尽管每个德国人都要为600万犹太人之死担负起道德责任,但是,德国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德国人中也有良心未泯者,德国人中也有伸张正义的人。在今年的5月8日,勃兰登堡门前,又聚集着数万德国民众。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世界———德国已经走出希特勒阴影,1945年5月8日就是“德国的出路”。讲述者:德国前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关键语:见证第三帝国的覆灭从此再没见过父亲的笑容 记者:冯·魏茨泽克先生,1945年5月8日您在做什么? 魏茨泽克:我在博登湖我寡居的姐姐家里养伤。这一天对我个人而言可能并没有像它对于历史而言那么重要。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德国有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 魏茨泽克:我不记得有过哪一天真正相信过我们会赢! 记者:希特勒后来曾经说过,慕尼黑协议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您的父亲是参与协议签订的外交官…… 魏茨泽克:希特勒在生命的最后时日曾经这样说过,因为他错过了打击西方于猝不及防之时的机会。而我父亲和当时的意大利外长都在支持一场密谋,即如何促使墨索里尼在英法意德四方会谈时支持和平方案。 记者:您的父亲还与当时一些积极的反战组织,特别是军事反战组织有过接触?但后来他却被当作希特勒的帮凶在纽伦堡受审,您本人参与了为您父亲的辩护。您怎样解释这种矛盾? 魏茨泽克:有一天,我的父亲在和我谈话时,突然转到了一个他平时很少提及的话题:我们可以,我们能够,还是我们必须坚守岗位呢?父亲的一位军方朋友贝克,在接到备战的命令后,自认为无法承担责任,因此辞职。但我父亲不同,他要为避免战争尽一份力,因此他必须坚守岗位。 记者:也就是说,这里关系到的问题是,谁应该留守岗位,去阻止最坏情况的发生,谁应该辞去职务,不去推动最坏情况的发生? 魏茨泽克:对,还是那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可以,我们必须,我们能够坚守岗位吗?我父亲为避免武装冲突与其他国家外交人员所作的斡旋,用司法角度来看,几乎已经到了背叛国家的边缘。在国家安全总局里还找到一份文件,里面的内容就是要免去我父亲的职位并起诉他。以至于后来他在纽伦堡盟军的法庭受审之时,觉得自己站错了法庭。 记者:对于您父亲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您有多少了解呢? 魏茨泽克:我在战争中是个士兵,与家人的联系不多,但毫无疑问,战争一直在折磨着他。9月1日战争爆发,9月2日他的儿子,我的哥哥战死。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脸上的笑容。看得出,他心中一片茫然。讲述者: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关键语:讨论德国缺少的素质德意志民族一直声誉不佳 记者:施密特先生,1945年5月8日您在做什么? 施密特:我当时在比利时的英国战俘营,我没有体验这一天发生的历史事件,我几乎没有注意到有这样的一天。 记者:当时您听说希特勒死了的消息吗? 施密特:这可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我应该是不知道。另外这对我也无所谓。 记者:能谈谈您的家庭吗? 施密特:我出生在汉堡一个不问政治的普通家庭,我父亲是个教师。当时学校里的孩子都要参加希特勒少年团,我当然也要参加,但却遭到父亲的禁止,当我一味坚持时,站在父亲身后的母亲告诉我一个我还不知道的事实———我有一个犹太血统的外祖父。从此,我的经历就和我这个年龄的其他少年不大一样了。 记者:有点害怕吗? 施密特:我父亲十分害怕,并不是害怕被处死,他也不知道犹太人会被处死。他害怕的是如果有一天这个秘密被人知晓,他的职位就保不住了。仅仅这一恐惧就足以将人折磨得筋疲力尽了。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纳粹有一天会灭亡? 施密特:1941年,与苏联开战时。但早在1937年,在看到一个名为“败坏了的艺术”展览后,我就觉得这些人很疯狂。 记者:您从何时起开始觉得纳粹党人是罪犯的呢? 施密特:战后。我早就知道希特勒会将德国引向灾难,我所设想的战争结局甚至比现实中的还要惨烈。但我当时并没有把他当作罪犯,因为我对犹太人种族大屠杀的事一无所知。 记者:您从何时起有了从政的想法? 施密特:我并非刻意从政,但从战俘营出来之后,我就一直积极参与政治。1953年有一个人对我说,你的口才很好,还学过经济,我们联邦议会里可能需要你这样的人,你愿意参选吗?我当时就是觉得当4年的议员应该很有意思,但根本没有想过从此成为一名政治家。 记者:您不仅在前线亲历了战争,还看到了盟军对您家乡汉堡的轰炸,您怎么评价盟军的轰炸? 施密特:我认为任何针对平民的轰炸都应该被禁止。我并没有说盟军的轰炸是犯罪,但完全可以采取另外的进攻方式。 记者:您认为纽伦堡的审判对德国人有启蒙教育的作用吗? 施密特:很少。对绝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如何生存,尤其是如何度过1946年和1947年的冬天,这一问题远比反思希特勒更重要。当然少数人例外,一种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当然关注纳粹的下场,还有就是一些流亡归来的有识之士,他们的目标是要让德国重新恢复秩序,这一点上他们的精神远远地走在了前面。但他们无法改变德意志民族受损的声誉。 记者:为什么? 施密特:首先是因为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性大屠杀,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发展得很晚,我们重要的邻居:法国、波兰的民族意识形成都比我们早上200~250年。因此这个民族没有什么抵抗力。他们很容易激动和狂热,他们会为威廉二世时代的繁荣而陶醉,为海因里希·冯·特来切克的(种族优劣)理论激动。 记者:能展望一下德国的未来吗? 施密特:现在我们对未来还没有太大信心,但这种状况可以改变。但今天的人好像缺少我们祖辈和父辈那样的动力,缺少精神上的指引。教堂不会给我们什么指引,政党也不会,商业集团的老总更不会,就连记者们也不会给人们什么指引。 记者:这是您的经验之谈? 施密特:是的,都是我的经验之谈!讲述者:德国犹太人马塞尔·赖西·兰尼基关键语:回忆求生的技巧逃亡后多活一天比登天还难 记者:赖西·兰尼基先生,1945年5月8日您在做什么? 兰尼基:我在华沙。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庆祝是在5月9日进行的,即投降签字的日子。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我们必须要到大院里,朝天鸣放礼炮。大家都到了院子里,每个人都抽出了枪,大家应一起扣动扳机,可是我晚了一秒,这是我二战中开的第一枪,也是最后一枪。 记者: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战争结束了?逃亡结束了?未来不确定? 兰尼基:还是最后一种感觉更确切。未来的一切都是那么不确定。总有人问我解放后的那几个星期我都干了什么。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激情,我要找吃的,找穿的。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 记者:您是在哪里度过战时的那几年的? 兰尼基:最初在华沙,1940年起在华沙的犹太人居住点。从1942年秋天逃跑之后就一直过着地下生活。1944年解放时,我和太太还处在地下。 记者:解放的时候您很害怕? 兰尼基:是的,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记者:您知道1945年5月9日,您的全家几乎都被杀害了吗? 兰尼基:不知道,我知道我父母和我太太的父母被杀,我哥哥也被杀,但姑姑舅舅们和表亲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记者:您出生在波兰,父母是德国人,又信仰犹太教。您觉得自己的根在哪?兰尼基:我还是觉得在德国文化里。 记者:您在华沙的犹太人居住点生活过,那里什么样子? 兰尼基:居住点是一个封闭的小城,因为不断有人被运送到这里,所以很快就将近有45万人住在这里。尽管死亡率很高,这个居住点还是在不断扩大。我总在想,逃出去又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呢?说实话,1943年,居住区的生活还不算最糟糕的。在这里人们还可以串门,还有文学晚会、音乐会。在这里每天都有枪声,每天都有人被害。但人们还能生存下去,在死亡的恐惧中生存。 记者:为什么在居住区里,刮胡子那么重要? 兰尼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德国人在选择哪些人该被送往集中营的毒气室时,会先挑那些胡子拉碴的人,他们觉得这些人邋里邋遢,最该处死。 记者:您后来从居住点里逃出来。在第一个落脚点待了多久?后来又怎样?兰尼基:我们在一所公寓里住了一星期,然后又搬到了另一处条件好点的。但我们必须不断逃亡。因为会被发现。记者:当您重回德国,在街上看到的流亡返回者,要比以前纳粹时少得多,您有没有觉得很别扭呢? 兰尼基:当然。我是晚些时候,1958年才返回的。当时我在选择,是留在社会主义的波兰还是离开,我选择离开,但去哪里呢?以色列?不行,我一句希伯来语也不会。只能去德国,我们是从这里被运送出来的,这个国家有义务接纳我们。 记者:您回德国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 兰尼基: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记者:当您多年以后回首这段历史时,更像是在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还是别人的命运? 兰尼基:这个问题倒是很出乎我的意料。我所经历的一切,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太深了,我很难将其当作别人的故事。(高天忻对此文亦有贡献)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际新闻 > 正文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