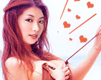死神远去 青春来了 艾滋孩子的成长故事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3日05:55 都市快报 | |||||||||
|
在医疗技术发达的美国,那些HIV阳性的孩子(患艾滋病或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已经几乎不再有夭折之虞。于是,他们的青春不期而至,问题也随之出现。6月26日的《纽约时报》对此作了报道与思索。 不再有死亡阴影
1991年,纽约哈莱姆医院的儿科医生伊莱恩·艾布拉姆创建了家庭护理中心(FCC,FamilyCareCenter),这是纽约最早几个专门治疗患艾滋病或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的医疗机构。当时,这种“治疗”主要是减轻那些孩子死亡前的痛苦。起初的5年里,每年有10至20个婴孩在FCC死亡。其中有个孩子一直活到6岁,当时,医生把这视作医学奇迹。 如今,由于蛋白酶抑制剂、联合疗法、鸡尾酒疗法等医疗手段的应用,在FCC接受治疗的约135个HIV阳性儿童,平均年龄达到了13岁,而且正在逐年增长。 艾布拉姆女士说,“这些年来,我们这个项目已经从治疗为主、心理健康辅导为辅,转到了心理健康辅导为主、治疗为辅。在旅途中,这是最后一段了。” 奇迹之后是挑战 然而,在这旅途的最后一段,出现了没人曾经预见到的复杂的心理问题。那些生来体内就有艾滋病病毒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在早年很少有孩子能幸存下来的时候,他们的心理问题似乎毋庸担忧。现在,HIV阳性儿童存活时间延长了,进入了青春期,病情的透露就成了棘手之事——他们对自己的情况究竟知道多少?该由谁来告诉他们真相?什么时候、怎么告诉? 挑战与奇迹接踵而至。 艾布拉姆女士举例说,有个14岁的病孩,对T细胞(一种有免疫反应的淋巴细胞)指标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并且每天服药,却一直不知道自己是HIV阳性的。 成功阻击母婴传播 截至1990年,美国大约有2000个孩子是在母体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1994年,临床试验表明,抗艾滋病药物AZT(中文名齐多夫定)能有效阻止艾滋病病毒的母婴传播。这种药物得到推广后,美国的艾滋病母婴传播率马上从大约25%降到了8%。 此后,加上其他措施(例如建议HIV阳性产妇不要进行母乳喂养),美国基本上消灭了艾滋病的母婴传播。目前,美国的艾滋病母婴传播率已只有1%至2%。也就是说,每年美国出生的HIV阳性婴儿只有约200个。2003年,纽约市的这类数字是5个。像哈莱姆医院这样有经验的医院,过去4年中只有两个HIV阳性婴儿出生。 1999年时,通过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孩子,寿命为8.6岁至13岁。如今,那些遵医嘱服药的孩子,其寿命已不再有一个明确的上限,他们已经从绝症病人变成了慢性病人。而在以前,别人从没想过他们会步入成年。有个收养HIV阳性儿童的母亲说:“我把她宠坏了,因为我一直觉得她快要死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宠爱表现为对孩子隐瞒真相。 A的故事:“他的日子会很难过” A的客厅墙上挂了很多像框,里面都是她的6个子女和养子女的照片。光看这些照片,很难判断其中哪个孩子是HIV阳性。再看看A,她是个蛮吸引人的年轻女子,说话柔和清晰。你也很难想像她和她的次子一样,感染艾滋病病毒已有十多年。A和丈夫(也是HIV阳性)一直对几乎所有人——她的朋友和邻居,她的其他几个孩子,甚至她次子本人——隐瞒次子的病情。 A的次子是在子宫里感染病毒的。出生以后,他几乎每天都要服药,却没人告诉过他吃药的真正原因。现在,他11岁了,定期去FCC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有时候,孩子会产生疑惑,A就告诉他:你得的是一种血液疾病。 A说:“他很可爱。但他还有点不成熟。我觉得他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事。我准备下半年试试向他透露。” A觉得,她的其他子女现在也还不能理解这事,“我经常去看医生,丈夫也经常去看医生。儿子吃药的时候,我们就叫其他孩子离开房间,因为他们老是要问:‘他为什么要吃药?’‘他为什么老是生病’‘他为什么要去找医生,而我不用去?’” A很害怕别人知道儿子的病情。她哥哥是亲戚中惟一知情的,而她的父亲、继母和姐妹都不知道孩子的病情。 A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她说:“人们要么给你同情,要么把你一把推开。有些孩子、有些父母很残忍。到时候,没人愿意碰你。他们会说:‘别过来,别靠近我。’他在学校里很有人缘。要是老师和同学知道真相,他的日子会很难过的。” 在A的次子身上,有两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1)随着他逐渐长大,不可避免会发觉,父母一直对他隐瞒着一个巨大的秘密;2)这个快乐、英俊而有魅力的男孩正在接近性成熟期,但他携带艾滋病病毒,自己却不知道。 A自己也很踌躇。她说:“要是他知道之后埋怨我,我认了。的确是我的错,谁让我有过不安全的性行为呢。我担心的是,他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同了。他还是个孩子,喜欢音乐、电视、摔跤,喜欢女孩。我不想让他改变。说真的,我的困难比他更大。” E的故事:“她的老师简直要疯了” E曾经参加过“行动起来”(ActUp)组织。该组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以激进手段来提高全世界对艾滋病危机的认识,其中一些成员后来成立了“只为孩子”基金会(JustKidsFoundation),用和平手段来帮助HIV阳性儿童。E就是其中一员。当时,她决定收养一个这样的孩子。 医生给她送来的女婴不光是HIV阳性,还在母体内就对高纯度可卡因上瘾。当时看来,她只能再活两三年。当然,后来她活了下来。 大约在8岁时,E的养女开始对自己的病情有了疑惑。借助一本专门为HIV阳性儿童写的书,E告诉了养女真相。那本书说的都是实话,但语气很乐观,意在培养这些孩子的自尊和自信。 E的方法效果很好—可能是太好了,以至于养女去了学校后,竟然想把自己的情况告诉要好的同学。E说:“她的老师简直要发疯了。家长们会怎么办?校方开了无数次会,最后决定把这事瞒起来。他们告诉我女儿,她自己知道这事就行了。” P的故事:长子鼓励幼子服药 P曾经由于工作患了肺病,落下终身残疾。不再上班后,她决定收养孩子。当时,她只是想:我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过去15年里,在与姐姐同住的一套公寓里,P养育过大约60个孩子,他们的居住时间或长或短,其中有两个被她收养。头一个是个男孩,现在已经12岁,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1994年时,他的监护人——姨母得知他母亲患艾滋病后,把16个月的他拒之门外,扔给了慈善机构。 姨母从未送男孩去做过HIV检测。P收养他后,检测结果表明:是阳性。哈莱姆医院的医生告诉P,男孩也许活不到4岁。P回忆说:“当时我常问他:‘今天过得好吗?’他的每一天都非常宝贵,我真的怕他活不久。”孩子满4岁时,P和医生们给他搞了一个派对以示庆祝。 孩子到五六岁时,开始抱怨每隔12小时必须服用的AZT的副作用。有一天,他提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要求:想要个弟弟,跟他一块儿玩。P反复考虑后,去了收养机构,提出再收养一个孩子,并且有3项条件:必须是个男孩;要比头一个养子年幼;也得是HIV阳性的。 P说:“他们真的以为我疯了。不过要是大儿子出了什么不幸——但愿不要这样,我不想他看着我说:‘其实你始终知情的。所以你让我有了一个弟弟。这样你就有一个健康的小孩了,可以用他来取代我了。’” P刻意在大儿子房间里放了一些关于HIV和艾滋病的儿童书籍。于是,他渐渐生疑。4年前,在医生的劝说下,P对他说了病情真相。 那天,P带他去看医生,之前先去餐馆吃午饭。P让他自己随便点菜,然后说:“我要跟你说点事情。” 孩子说:“等会儿吧。”开胃菜上来了,然后是主菜。P又说:“我真的要跟你谈谈。”儿子说:“我知道你有事。不过别影响吃饭嘛。” 吃完饭结了账,在去医院的路上,P说:“过来。”“不。”P狠狠心,还是说了真相。说完后,她流泪了。孩子看上去却很平静。他说:“就这些事吗?我还以为你要告诉我:我像你一样有哮喘呢。” 大儿子有时候会问起生母的情况。P不光知道他的生母是谁,还偶遇过她。不过根据法律,在他18岁之前,P不得向他透露任何有助于他找到生母的信息。他的生母现在看上去还比较健康,又生了孩子。 P的第二个养子现在已经6岁,尚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哥哥在鼓励他坚持服药。 父母的三种态度 在说出真相的问题上,HIV阳性儿童的父母们往往持不同的想法。 父母们常有的担忧是:孩子还不明白艾滋病意味着什么,现在说会不会太早、太突然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HIV儿科心理支持与研究项目负责人劳丽·维尔纳博士说:“家长们会说:‘看看她,她在那儿玩,她很快乐。我干吗要把这种会改变她一生的沉重消息压在她身上呢?’” 一个12岁女孩的母亲也说:“在她这个年纪,她还不想显得太扎眼,不想与朋友们不同。她不会愿意说任何跟艾滋病有关的事情,不会愿意谈艾滋病患者。不然,朋友们会围过来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有的父母觉得,这种秘密让人不堪重负,最好的方法是告诉所有人,从整个社区甚至整个社会那儿得到帮助。他们还希望这种诚实能让孩子在心理上好受一点。然而调查表明,这种广而告之的“泄密”,反倒对孩子的自尊心不利,此外还会危及这些家庭在社区里的处境。 另一种态度则是,孩子应该知道任何事情,没啥好羞耻的。但其他任何外人都无权知情,因为这与他们无关。不过,孩子们往往很难理解这种态度中包含的戒心。他们一旦得知秘密,将很难适应对外人保密的任务。一项调查显示,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孩子中,有45%被告知不准跟任何人说起此事。在这个年龄承担这样的责任,实在太艰难了。 父母的问题和压力 那些HIV阳性儿童的家庭,常有其他问题:吸毒,药物滥用,精神疾病,家庭暴力,家庭不稳定,种族歧视等。而且,这些家庭往往很穷。 因此,医生也担心,让家长在“泄密”方面承担太多压力,也许会导致他们逃避压力,甚至使孩子彻底停止正常的治疗。 有一位HIV阳性儿童的母亲就说过:“不是我不愿跟孩子说这事,事实上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情况——她会为我感到羞耻,会对我感到愤怒。我不愿意听她说:‘妈,你怎么会做过那种事情呢?你当时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 医生该做的和不该做的 在“泄密”问题上,医生也受到严格约束。根据法律,如果没有得到家长的明确同意,医生不得向HIV阳性儿童透露他们的病情真相。而且心理学家认为,由家人而不是医生向患儿透露真相,可能更有利于患儿以后的精神状况。 目前,一些医学专家(他们大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致力于HIV阳性儿童的治疗)开始在“泄密”问题上对家长施加影响——什么时候由谁来告诉孩子?怎么说?怎么才能既说出真话,又不危及孩子的家庭关系?目前看来,这些专家的努力,成功率颇高。 FCC负责人艾布拉姆女士说:“家长们最常见的反应是:‘他没问起过,所以我没告诉他。’不过,最终所有的家庭都做了对孩子最有利的事情——说出真相——只不过未必是在我们认为应该的时间。” 纽约长老会-哥伦比亚医院特殊需求医疗中心负责人克劳德·梅林斯也说,他的HIV阳性患儿中,有70%是在10岁或11岁时知道自己病情的。 “泄密”是一个过程 不过,有些父母觉得,只要把真相告诉孩子,这事就算完成了,不需要再次谈论。 事实上,孩子处理信息的方式与成人是不同的。医生和社会工作者认为,对孩子“泄密”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谈话必须进行数次,才能真正开始起作用。 纽约长老会-哥伦比亚医院特殊需求医疗中心的负责人克劳德·梅林斯说过这么一件事:在一项关于艾滋病的心理影响的调查中,一个女研究生问一个孩子:你得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时是什么反应? 那孩子盯着她:“我有艾滋病?”事实上,这孩子已经不止一次被告知自己的病情。于是,医生将他的养父母叫来,再次就怎么“泄密”指导了一番。不谈生论死问生儿育女HIV阳性孩子知道真相后,往往不会马上谈生论死。梅林斯说:“他们总是问及很快将要发生的事情,比如结婚、生孩子。他们害怕自己不会有正常的寿命,十四五岁的人就想这些事了。” 梅林斯的一位同事也说:“他们反复追问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病毒的永久存在,他们知道,体内的病毒永远没法消灭;二是他们生儿育女的能力会受到什么影响。” 此外,有些孩子已经在心理上对真相形成了抵触。一次,纽约长老会-哥伦比亚医院特殊需求医疗中心的医生得到家长授权后,对在那儿治疗的一个女孩最终说出了“艾滋病”一词。女孩却说:“我没有艾滋病。只有那些皮包骨头、住在非洲的人才会有艾滋病。所以我没有的。” 换一个医生真难 当年那些HIV阳性儿童中,年龄较大的已经步入成年。他们也有自己的心事。 20岁的V现在在曼哈顿的一家面包房工作。他7岁时,母亲因艾滋病去世。那7年中,两人都是医院的常客,“医院就是我的第二个家,甚至比真正的家还要牢靠。护士们都认识我,她们就像照顾儿子一样对待我。这种情况现在很少有了。” 母亲去世后,V一度被收养,但与养父母的关系很糟。那几年中,他并没有家的感觉。后来,他搬到了一个专门为HIV阳性少年设立的集体家庭中。18岁时,他搬入了独自租住的公寓。他说:“我成长得很快。每个人看见我都说:‘你只有20岁?不可能。’” V的梦想是开一家自己的面包店。眼前,他最大的烦恼是:他必须挥别为他治疗了多年的儿科医生,另寻一位为成人治病的医生。他说:“我从18个月起就认识他。很多人没法让我信任。也就是说,我可以信任你,但我不信任你。明白吧?” 这种心理上的困扰,在V这一代HIV阳性青年中很普遍。在他们的生命里,那些儿科医生往往是陪伴他们时间最长、最负责可靠的成年人。纽约圣卢克氏-罗斯福医院的医生斯蒂芬·阿帕迪有个女病人,现在已是青年。她10岁时,父母就已双双去世,她的哥哥也不懂怎么照顾她。当时,这个女孩在服药方面缺人指导,一度病情不轻,几乎无法行走。在阿帕迪医生治疗下,现在她显得朝气蓬勃。但只要她和阿帕迪医生在一起,无论遇到谁,她都要说:“这是阿帕迪医生。他认识我母亲。他认识我父亲。” 成年后为同病的儿童代言 有些HIV阳性孩子成年后,表现出了早熟、独立,和敢于直面偏见的无畏。 本·班克斯今年26岁,住在弗吉尼亚州。他在襁褓里得过一种罕见的癌症。12岁时,也就是癌症治愈10年后,他做了一次体检,发现自己是HIV阳性。医生认为,这是因输血而感染的。 从此之后,班克斯开始小心翼翼,生怕对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学校特别允许他在午饭前跑到洗手间里偷偷服药,而不必去校医那儿,以免其他学生认出他服用的药名来。有一次,班克斯和同学们一起在教室里看电视剧《莱恩·怀特的故事》(莱恩·怀特是一个血友病患者。1985年,13岁的怀特被诊断出因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学校立即决定禁止他到校上课。1992年,怀特去世)。当时,班克斯静静地坐着,四周的同学都在取笑电视里的怀特。 班克斯人缘很好。他渐渐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然后是其他几位朋友,进入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后,又告诉了一些同学。现在,他是一家儿童艾滋病基金会的一位发言人。2003年,他结了婚。 班克斯说,他对于自己病情的态度有个转折点(从绝症转变成一种可以控制的疾病),那是在17岁时。当时,他向许愿基金会(Make-a-WishFoundation,美国的一个慈善组织,专门帮临终的孩子实现梦想)提出了自己的申请,却遭到拒绝。他惊呆了,打电话给自己的医生。医生说:“本,干吗不把机会留给真正需要的孩子呢?你会活得好好的。” 去夏令营哄孩子吃药 21岁的希尔玛拉·克鲁兹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第4。她和弟弟妹妹都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弟弟和妹妹都在5岁时夭折,当时克鲁兹才8岁,最年长的哥哥在精神上难以承受,离家出走。3年后,母亲也去世了。从16岁起,克鲁兹就独自生活。现在,她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办公用品商店工作。 克鲁兹的同事中,有些知道她的病情,有些不知道。她说:“有些人,你光听他们说的话、开的玩笑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我觉得,他们并不能面对这事。” 每到夏天,克鲁兹就去一个艾滋病基金会的夏令营当辅导员。参加夏令营的HIV阳性儿童很难对付。他们难得轻松一下,不必成日担心自己的病情,因此往往不愿按时吃药。有时,克鲁兹只能说:“你们把药都吃下去,我就也吃一颗。来,一起吃。”事实上,孩子们吃的药未必适用于克鲁兹这样的成人。到了晚上,她往往会难受得整夜辗转呻吟。 梦想和现实的落差 生活在这些年青人面前豁然开朗后,是否珍惜就成了关键。有个20岁的姑娘,做一份全职工作,同时在大学读书。她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她说:“我的很多健康的朋友整天无所事事。我有工作,我读书。我想,这种差别是因为我想在死之前确信自己能做这些事情。我的目标是把它们都完成。” 然而,现实仍然严峻。纽约长老会-哥伦比亚医院特殊需求医疗中心的一位医生说,他有两个病人,一个17岁,想当兵,一个18岁,想当飞行员。后来,他们知道了相关的法规,知道自己并不能遂愿。这位医生说:“事实上,艾滋病病毒仍然绕不过去。” (编译应民吾 都市快报)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际新闻 > 正文 |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