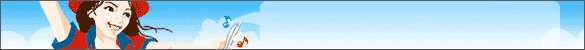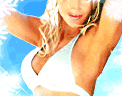[人物]四个印度人故事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4日00:03 新京报 | |||||||||||||||
|
开篇,我们选择了4个印度人的故事。 个人的讲述或许偏颇,却因其触手可及,而更接近印度社会某个方面的真实。V.K.索尼,一个信心十足的企业家,而在社会的另一端,农民工库马尔正艰难地进行着讨新行动。
米拉·奈尔,一个从印度边缘走到世界中心的电影人的经历,折射了一些印度人对国际化的体验与应对姿态。 阿伦德哈蒂·罗易,一个蜚声世界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生存样态,讲述了一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面对全球化浪潮的两难生存悖论。
印度一公司办公大厅。这样的场景是索尼的工作常态,对库马尔及其子女来说却有些遥不可及。 企业家 V.K.索尼 V.K.索尼,1950年出生于印度旁遮普邦城市贾朗达尔。 在这个从事商业的中产阶级家庭里,重视教育和培养家庭观念是索尼成长过程的重要内容。1973年,年轻的索尼从旁遮普工程学院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以后,很自然地走上了商业的道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印度著名的医疗连锁企业阿波罗集团担任市场开发职责。在这里,索尼迅速展示出了他的商业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提拔成了副经理。 之后的十余年里,索尼与所有大公司的年轻职员一样,开始了漫长的跳槽过程。他先后为西姆科-比尔拉集团、肖-瓦莱斯公司和M&M等印度著名企业工作,后来被印度领先汽车生产企业M&M公司提拔为总经理及副总裁。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变成了传说中的“空中飞人”———必须不停地进行环球旅行,飞到世界各地去会见国外的商业伙伴。 索尼认为,不断变换工作极大丰富了他的商业技能和管理技巧,也给了他深入不同文化的机会。不过,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感到了家庭和事业无法两全的痛苦。1998年,索尼的两个孩子都进入了非常关键的高中时期,家庭观念浓厚的索尼认为,在孩子一生中的重要阶段,身为父亲应该优先考虑的是与孩子尽量多地呆在一起,给他们适当的支持和指导,常常出差的工作无法使他做到这一点。这一年,索尼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离开M&M高层,开始自己做生意。 他的生意开始不是很容易,坐在自己250平方英尺的家里,索尼思前想后,决定从门槛较低的国际贸易开始。1998年10月,刚刚开始创业的索尼成为第一批访问中国的印度商人之一。在中国,他看到了基础建设的兴起和机遇。回国后,他开始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短短几年时间里,索尼的企业已经从最初的国际贸易领域发展到了人力资源咨询、外部采购、商业咨询等不同业务领域,最近他还开始投资动画和远程教育系统。 现在,索尼的孩子们都长大了,他的一子一女也追随父亲的脚步走入了商业领域。他们的经历和父亲当年有一些类似,不过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开始更为国际化。大学毕业以后,他们先后进入的都是世界知名的顶尖商业咨询公司。索尼自己的企业也运作十分顺利。不管是对印度经济,还是自己的事业,他都感到信心十足:“关于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我都有很多的长期和短期目标。我现在集中力量要做的,就是不断向前,实现这些目标。”□本报记者马晶 农民工 库马尔 库马尔是一名建筑工人,来自中央邦,属于印度最低种姓———首陀罗,也就是贱民。与其他进城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民一样,他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 2004年年底,德里大学一个主要宿舍改建工程完工后,包工头拿走了工钱。民工四处求援无果,家中老小还等着他们拿回工钱维持生计。最后,他们找到德里大学一个学生会负责人。学生会本来希望德里大学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先垫付民工工钱,再追究携款潜逃的包工头的责任,但遭到校方的拒绝。最后,学生会决定前往改建好的宿舍前,加入民工绝食的队伍,以壮大声势,吸引媒体前来报道。 库马尔的家乡收成不好,城市化步伐又快,因此很多农民都进城去了。可是,他们种姓低,家境贫寒,无法得到任何好的教育,缺乏任何其他谋生技能,甚至连主流社会通行的英语也听不懂。库马尔的儿子出生在德里,在一家公立学校上过几个月的学,后来终究还是辍学了。库马尔说,公立学校比较远,又不像私立学校天天有校巴接送,父母因工作的原因没时间接送他们,久而久之就干脆不去了。 民工的绝食行动引起了德里电视台等媒体的注意,三四天后,情绪逐渐缓和下来。学生会一些成员买了一些食物,去库马尔家看望他的妻子和儿子。库马尔的住处其实就是不远处临时搭建的贫民窟,高不过1.5米,面积不过5平方米,阴暗破烂,酸臭扑鼻,陈设除了简陋的灶具、瓢盆,就是一家三口共用的木板床。床上没有蚊帐,又不可能用得起蚊香。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跟我们家乡里的差不多的。”通过印度学生的翻译,他告诉笔者。 “当初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我看你们的生活也没有改善啊。” “没办法,土地收成不好,租税又重,生活很难啊。”他叹着气说,“时不时会有人饿死或者还不了债自杀哩。” “政府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政府一直在发放福利和资金,可是都很难到农民手里,都被中间的官员拿掉了。”一位印度学生听了库马尔的解释后,跟笔者说。 “那他们的出路何在?” “唉!他们从祖上到现在都很穷,所以孩子没法得到好的教育;因为他们得不到好的教育,所以他们也会很穷;因为他们穷,他们的后代也还是不能得到教育……你能看得出出路在哪儿吗?政府已经有够多的事情忙了,民间助学又不成气候。我自己是很悲观的。”这位婆罗门出生的印度学生这样说着,但未显惆怅,或者愤慨。 □印度德里大学毕业生 岑斯 电影人米拉·奈尔 2001年威尼斯电影节上,一部用手提摄影机拍摄的低成本影片《季风婚礼》以压倒性优势夺得了金狮大奖,随后在美国获得超过1300万美元的票房,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卖座的外语片之一。这部影片巩固了导演米拉·奈尔作为印度最有声望的国际级导演的地位。在此之前,她导演的《爱经》已经使她以“反叛性的印度导演”蜚声世界。
米拉·奈尔,一个已经蜚声世界的印度导演。她的经历或许代表了部分印度人对国际化的体验。 以印度的边缘打动世界 米拉·奈尔出生于印度东北海岸奥里萨邦的一个小镇上,她把这里描绘成“即使在印度也是偏远的地方”。和很多中国导演一样,米拉·奈尔也是以表现边缘人的纪录片起步的。 1985年,奈尔导演了纪录片《印度脱衣舞娘》(IndiaCabaret)。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她深入印度的脱衣舞俱乐部,和脱衣舞娘一起住了两个月,甚至被错认为脱衣舞娘。 更有趣的是,一开始,对纪录片一无所知的父亲强烈反对奈尔拍这部电影。他说:“你不能拍她们,因为这几个女人我都认识。”奈尔问父亲:“你怎么认识她们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带我去看这些恶心的东西,跳舞什么的。”话一出口,父亲立即意识到无法再理直气壮地阻止女儿拍片了。 《印度脱衣舞娘》使奈尔引起了西方的注意。1988年,奈尔推出了第一部故事片《孟买你好》(SalaamBombay!),资金来源是英国第四电视台。奈尔套钱的方式也和中国很多导演类似,英国第四频道答应提供投资的50%,她手中本来只有15万美元,但她说有40万美元,这样四频道就给了她40万美元。 她和孟买的浪流孩子打成一片,然后找到20个孩子,以每天25卢比的价值雇了他们做演员。这部表现孟买流浪儿童的影片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还得到了奥斯卡和恺撒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孟买你好》在印度被看做“有争议性的”,观众也不买账,最初没有一个发行商愿意碰这部表现街头少年的电影。但是当它在国际上获奖之后,终于有人愿意发行这部电影,在印度的主要城市放了27周。 有记者问奈尔,为什么她对边缘人那么感兴趣。奈尔说:“我想要质疑谁是‘外围的’,谁在定义它。我经常发现那些被认为是‘外围’的人非常引人入胜。”她坦言,吸引她的是印度的边缘人那种幽默感和对生活的调皮态度,就像《孟买你好》中的那些小孩对自己的身份没有一点痛苦和不好意思。 到世界中心展示故国 1996年,奈尔拍摄的《爱经》(KamaSutra:ATaleof Love)使她走进了世界各大媒体的焦点。 《爱经》是一部印度产英文电影,讲述古代男女的性爱故事,片中有大量裸露和性爱镜头,这在保守的印度自然会引起争议。奈尔回忆说:“我4个月里一直黑着脸。他们要剪掉任何一段有着‘色情’内容的影像,我说这部电影就是关于‘色情’的,如果把它们剪掉,就不是我拍的电影了。我把他们带到法庭上并且胜诉了。” 2001年的《季风婚礼》使奈尔摆脱了“争议导演”的称号。 这部电影在印度也获得了票房成功。影片以印度旁遮普省的一个大户家庭为切入点,通过5个独立成章但又互有关联的小故事,为观众展示最具印度民族风情的婚礼习俗。按照旁遮普习俗,所有新人必须在季风雨到来之前了结人生大事,才能迎来下一年的风调雨顺及家庭生活的和谐美满。奈尔用她清丽的镜头语言,通过5对新人的奇特遭遇,生动再现了现代印度人的人生百态。影片既放弃了一般印度电影“歌舞片”的架构,也放弃了边缘性和争议性的主题,表现了印度平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这部影片国际化的语言也使它在国际电影市场中大放异彩。 但是,《季风婚礼》这样的片子没有成为印度电影的主流。2005年,奈尔在泰姬陵拍摄美国影片《名正言顺》(TheNamesake)时,一个印度记者明言奈尔的电影会“损害泰姬陵的名誉”,因为这个建筑正在“被很多白人拍摄”。另一个游客不解地问:“为什么那个男演员不跳舞?” “我不想代表整个印度” 米拉·奈尔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英语教育,年轻时赴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她拍的多数电影都是英文对白。虽然关于印度的电影给奈尔带来了莫大荣誉,但她不认为自己是个“印度导演”,她不喜欢给人以狭隘的感觉。她承认印度给了她很多东西。她说:“我喜欢满不在乎、泰然自若的感觉。这是印度人的特征。无论是情感上,还是视觉上,有像马戏团那样的杂耍精神是很重要的。” 印度这种“马戏团”式的热闹有时是辛酸的。奈尔说:“我想以下的情形是‘印度的’:我们曾经没有隐私,我们曾经很多人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在《季风婚礼》中,奈尔把这种困境变成了喜剧,一家人睡一张床的习惯让他们不知道如何定旅馆的房间。 奈尔反对盲目地追求“国际化”。她说:“我开始时被认为是一个局外人,后来成为大家妒忌的对象。所有的印度导演都想成为国际导演。他们会过来问我:“如果我找到了迈克尔·凯恩或者肖恩·康纳利做影片的男主角,你觉得我会变成国际人物吗?‘这种对’国际化‘的热衷是完全错误的。” 她也不愿意被看做“印度的代言人”。 记者问奈尔:“你是否觉得自己被迫成为某种‘文化大使’之类的人?” 奈尔回答说:“是的。你作为一个在美国的印度人,而且在这个国家关于印度的图像如此之少,你会觉得非常艰难。我总是被要求提供关于印度的所有东西,我说:“我不能做这个。‘我不会成为一个驻美的文化大使,因为我主要是一个脏兮兮的个体。我更感兴趣的是人的生存处境。惟一能够做到这件事的是所有印度人做自己的事情,把自己凸现出来,以营造出我们多层次的存在影像。 现在这么做的人太少了,我是少数几个之一,因此我发现自己要做那么多人要做的事。这不公平,也不可能。” □本报记者 刘铮 作家阿·罗易 1999年,一支由来自不同国度的400人组成的队伍,向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纳玛达流域进发了,声援那里的“纳玛达反水坝组织”(NarmadaBachaoAndolan,简称NBA)反对政府修建水坝的斗争,队伍中有个瘦弱的女子,她就是印度当代著名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ArundhatiRoy)。
阿伦德哈蒂·罗易,印度著名作家。从容的思考几乎成了她的标志。 放下笔踏上远行的队伍 纳玛达水坝计划是印度政府在世界银行资助下拟定的,预计建设30个大型﹑135中型和3千个小型水库,估计会淹没245个村庄,4000万人需要搬迁。独立后的印度已建成水坝近4000座,高居世界第三。然而,在这个拥有这么多水坝的国家,尚有2亿多人用不上自来水。而水坝建设付出的代价是1亿多人被赶出家园。 罗易根据实地考察,写出了长文《更大的公益》。文章的叙述焦急而富于耐心,她相信大量确凿的数字和分析足以说服那些被蒙蔽的人。有时她说“这仅仅是个故事”,目的是提醒人们看似只能在故事中出现的情况就要发生在眼前。 她悲痛地使用了“unroot”(根除)一词,这是水坝建设后人们的真实处境。他们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被政府草草安置在聚居区里。政府的承诺一向是高调,新聚集地甚至有为孩子准备的滑梯和跷跷板。 但罗易发现,事实上那里的居住条件却非常糟糕。然而,这还不是每个迁居者都能享受到的待遇。有的人则要迁居三四次,因为他们的新家又要为另一个水坝之类的工程让路。 他们极度贫穷,只能在城市郊区的贫民窟中挣扎,成为廉价劳动力,比如建筑工人,去修建新的工程项目,而这些工程又会使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这些人要不在城市郊区苟延残喘,要不干脆愤自杀。 令罗易深感吃惊的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口吻出奇地强硬:“如果你正准备为国家牺牲,那你就应该为国家牺牲。”(尼赫鲁语)罗易发现,在暴力和强权面前,人民一旦陷进贫困的泥潭,就很难有希望。 历史的书写同样不会留下这些卑微的名字,他们的眼泪被“国家利益”的宏大字眼所掩盖。于是,她放下了笔,“把乔伊斯和纳博科夫搁在一边”,踏上了远行的队伍。 放弃巨神呼唤微物之神 罗易是位行动主义者,最初她却是在书斋里扬名立万的。1997年,年方36岁的罗易凭借《微物之神》(TheGodof SmallThings,另译《卑微的神灵》)一举夺得全美图书奖和英国布克奖。这是印度人第一次获此殊荣。《微物之神》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49周,译为40种语言出版,获利千万。小说成功后,各路讨伐纷至沓来。罗易看得很清楚,小说遭受攻击的不是所谓的色情内容,而是关于贱民维路沙的描写,他和上层妇女的恋爱情节触怒了一些人士。这些人的憎恨只能说明在甘地发明“上帝的子民”用以称呼贱民阶层的50年后,印度种姓制度的问题依然存在。 罗易没有被不同的声音所吓倒,更让人钦佩的地方是她也没有为赚取更多钞票去复制更多类似的小说;相反,她由一个单纯的小说家转变成了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她把巨额稿费捐给了NBA,甚至加入这个队伍。 罗易的眼光是宽广深远的。70多年前,卡夫卡把大祸临头的人类比喻成瑟瑟发抖的地鼠。一语成谶,波赫伦沙漠地底的一声巨响让印度人民被梦魇所笼罩。她不认为核试验是富国强兵的手段,是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标志。在著名的《想像的终结》一文中,罗易一针见血地指出,核武器只是为了满足极少数人的野心,是极端分子拉选票的手段。相信政府的诡辩就如同相信一个人会被坟头绊倒。她说:“可以确信的是印度在前进,但绝大多数印度人没有。我们的领导人说我们必须拥有核弹头以保护我们免受巴基斯坦的威胁,但是谁能保护我们免受自己的威胁?” 受困知识分子生存悖论 罗易表述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当提到印度政府时,总爱在后面强调“历届印度政府”。她要表达的意思是,对个体的冷漠与践踏是印度政府长久以来的问题;她反对的不是具体哪届政府,而是一切暴力和强权。她认为,在后殖民时代和商业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的幽灵不是消失了,而是改头换面渗透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过时的武器、违禁杀虫剂,这些垃圾统统披上华丽包装,摇身一变,像礼物一样被发达国家送往印度,印度人民却要感恩戴德。 尽管罗易言辞激烈,她金刚怒目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丝忧虑,隐藏着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生存悖论。纳玛达运动不能说失败,因为世界银行取消了投资;也不能说成功,因为印度最高法院判决计划继续实施,罗易本人被判处象征性的监禁一天。面对更加强大和手段高明的新帝国主义和新种族政策,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又该采取何样对策呢?她把尼赫鲁和甘地称作父亲和母亲。一方面坚持对暴力统治的批判,一方面又要冒着“文化原教旨主义”的风险参与国家的振兴。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甘地精神的坚定隐忍,也分明体会到了父亲的失音,就像《微物之神》中贱民维路沙的荒野之爱———他没有自身视角表述的可能,只能从他人的偷窥中向读者传递信息。 □特约撰稿人 王鸿博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际新闻 > 正文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
![[人物]四个印度人故事](http://image2.sina.com.cn/dy/w/2005-12-04/8620d79f76c9a57c6f9747653d5af3d3.jpg)
![[人物]四个印度人故事](http://image2.sina.com.cn/dy/w/2005-12-04/d51692d87e57c14b9f906e74701d6f6c.jpg)
![[人物]四个印度人故事](http://image2.sina.com.cn/dy/w/2005-12-04/efebe06506fd3494714d32d18981ec3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