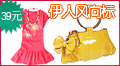|
|
|
|
|
西方神学:回应挑战的入世之路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27日11:20 南风窗
李 欧 从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基督教节节退却,先是失去了世俗的权力,真的成了“恺撒的归恺撒”,行政权只能施行在梵蒂冈这弹丸之地;接着在汹涌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夹击下,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力也江河日下。于是,19世纪的尼采庄严宣称:“上帝死了。” 而时至20世纪,尤其20世纪后半期,基督教似乎重新恢复了生气。据《2001年度世界宣教工作统计表》记载,全世界总人口中约有33%是基督徒,其中积极分子——所谓能认真承担“基督之伟大使命”者约有6.5亿多;当年为基督教事业的捐款达2800亿美元,用于基督教的计算机约有4.24亿台,当年出版的基督教期刊约3.6万多种,关于福音、神学的书籍1.71万多种……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有待考察,但在这科学高度昌明、“以人为本”是世界性的主流意识的时代,基督教居然仍能保持发展到这种规模,令人叹为观止。 其原因,首先,无论怎样,当今居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英国诗人艾略特曾经断言:“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在一定意义上,西方文化就是宗教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其次,在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形下,基督教的思想家以及神职人员积极地调整宗教策略、改革宗教观念,来适应新的文化境域。一方面,他们在与各种有重大影响的非基督教的思想流派的对抗中,吸收对方的思想,并以此作为资源来发展自身。另一方面,积极“入世”,关注地球上发生的各种类型、各种性质的重大事件,主动进行干预,甚至某些杰出成员以殉道者的身份为之牺牲也在所不惜,如马丁·路德·金、朋霍费尔、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牧师们,从而,扩大和深化了基督教的影响。 人本主义的“傲慢” 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浪潮构成了对基督教的直接威胁。20世纪的很多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却试图整合人文主义思想,并以此来发展神学思想。马里旦在《整体的人文主义》一书中,旗帜大张地宣扬“基督教人文主义”。布洛克则认为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思想并行不悖,而且还有大量的可融合点。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更进一步指出,在市场经济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下,人文精神已经大大衰落,而宗教则有助于人文精神的重建。 当然,他们对人文主义并非全盘照收,而是深刻地揭示出人文主义内在的悖谬和外在的困境,从而彰显宗教思想的神圣性。被称为“战后最富有影响力的宗教思想家”的尼布尔对“终极信靠”的思考就是典范例子。他认为人文主义把“终极信靠”放在人身上,如“有充分教养的聪明人”,“发扬理性的知识分子”,“纯洁又有热情的青年人”,或“朴素而不会剥削他人的无产阶级”等等,但是,历史显示,这些形形色色的“终极信靠”都令人失望。“人性中没有任何生机是不会枯竭的,没有任何美德是不会腐败的”,尤其在拥有权力后,道德英雄纷纷落马。他甚至提出:“不要信靠任何的人……这世界没有任何形式的善是既无腐败也不可能腐败的。” 在尼布尔看来,人本主义以人为万物的尺度,以此来权衡世界,如《圣经·罗马书》中指出的,“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这是一条傲慢的道路,是对人性过于乐观而造成的;人文主义想用人自身来替代上帝,其结果必然给人类带来大灾难——“对人的崇拜”会演变为“对己的崇拜”,必然导致狂热以及同伴的相互斗争,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却落实为兄弟间相残的现实,正彰示了人“傲慢的罪”。尼布尔宣称:“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人的人是应受到诅咒的。”对于这些偏激结论,笔者并不苟同。不过,基督教思想家对人文主义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切中要害。 上帝也环保 对宗教构成另一重大威胁的是科学思想。在当代生活中,科学的影响无所不在,无法抵挡,甚至被某些神职人员讥讽为“新宗教”,但这也迫使基督教改变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教庭对伽利略的平反就是一种象征。进一步,一些神学家还试图用科学思想来支撑宗教。 如玛奇(Diarmuid’ O Murch)著有《量子神学》一书,力图用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量子力学”来阐释神学。这还是林林总总的所谓“科学神学”中的一种。当然,神学家们更强调的是神学与科学各有领域:科学求真,在物质世界中探索;宗教求善,在精神世界里追索价值与意义。两者既可对话,又可相互支撑。他们常引用爱因斯坦的话:“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更有一些杰出的基督教思想家,甚至试图去解决一些当代的重大的科学问题,一些令科学家们都备感棘手的问题,如生态问题。例如,被爱因斯坦赞为“集善和美的渴望于一身”,“我们这一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的阿尔伯特·史怀泽(Albet Sehweitzer)牧师,在1919年就提出了“敬畏生命”的理念,尔后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他的理论,并且身体力行深入黑非洲内陆长达50年之久,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且,他的思想已经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基础与核心。 1960年代以来,以莫尔特曼为首的一批神学家,如美国的寇柏,德国的李德科以及汉斯·约纳斯更是大张旗鼓地鼓吹“生态神学”。他们认为,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宗教危机、信仰危机,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当代科学家们所提倡的“保护生态”,仍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追求,而按照《圣经》,上帝在与人类“立约”的同时,也与一切非人类的生命立约,“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一切活物立约”(《创世纪》),在这里,人并没有被授予统治地球的权力,而只是作为上帝的代表,对地球进行保养和管理。因此他们鼓吹,必须迎接人类的第三次“复活”:耶稣降临是第一次复活,是人与上帝和解;宗教改革是第二次,是人与人和解;当前则是人与自然和解,它将导致人类的第三次复活。 存在主义的挑战 在面对非神学的并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流派的挑战时,一些杰出的神学思想家也试图吸纳它们,结合它们,发展和完善宗教哲学和神学。例如,存在主义是20世纪影响极为深远的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如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尔斯、加缪等都是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其中大多数是无神论者。而神学家保罗·蒂利希、马丁·布伯等则将基督教与存在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被无神论者萨特称之为“最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蒂利希(Paul Tillich),在其《系统神学》、《存在的勇气》、《新的存在》等著作中,深入地探讨人的存在,人的超越性以及与上帝的关系。他认为存在主义和基督教神学在对人的本性的体认把握上是一致的,人的本性既表现在自由性,也表现在有限性上,这是人的悲剧性的生命结构。 他通过对“勇气”的发掘,将“存在—本身”(being—itself)的结构敞开,使伦理学范畴进入本体论的领域。他还探讨了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核心范畴,如“焦虑”、“关怀”、以及“意向”等。他认为,必须先确立“终极关怀”,人的生存意义才得以敞开和澄明,而这种“终极关怀”指向绝对超越者——上帝;进一步,他还推论,人的基本意向就是使人与上帝相关联。 神甫会晤马克思主义者 1965年,一批拉美神甫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会晤。这是神学家们主动邀请的,试图探讨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性。会晤没有直接结果,但是以“解放神学”命名的一种激进神学在拉美各国成长壮大起来。 在这种神学理论中,出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如阶级斗争、剥削、革命、压迫、人类解放、人性异化等等,并且如同马克思主义一样,这种神学理论被用于指导改造社会的实践。从196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各种反抗阶级压迫,反抗社会不平等,反抗种族歧视的社会运动中,都能发现大批神甫的身影,最著名的是被称为“游击队神父”的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神父。“解放神学”的主要代表还有古巴神父博夫、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尼加拉瓜神父卡德纳尔、阿根廷的塞根多,其中,思想最系统的是秘鲁的古斯塔沃·古铁雷斯。 1968年,“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召开,并在会后发表声明,谴责建立在不公正基础上的现行社会结构以及“制度化的暴力”,宣称“上帝差遣他儿子耶稣就是要解放所有被罪、饥饿、悲惨命运和压迫所捆绑的人们”。麦德林会议之后,许多神职人员深入社会最底层,实际有效地去帮助穷人。在这些“革命教士”的影响下,拉美各国城乡自发组织起探讨教义和社会问题的大批的“基层社团”,对拉美的社会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过,70年代中期后,罗马教廷试图压制解放神学的“过激行为”。教廷的信理部部长拉辛格在世界主教会议上宣称“解放神学”具有“异端”思想的危险,并且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如撤换一些主教等,使解放神学运动一度走向低潮。但是,该运动不久就恢复了生机。1984年,教廷发布了《关于解放神学若干问题的指示》的文件,指责解放神学“以不适当的方式搬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不能容忍的”。不过,在抗议声中,到了1985年,教廷又发布了《基督教的自由和解放》的文件,做出了明显的退让,甚至在文件中还引用了解放神学的理论观点;而解放神学的核心人物也做了一些妥协。从此,解放神学在教会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发表评论】
不支持Flash
不支持F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