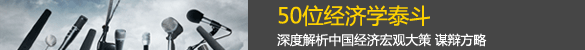一体两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体两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呈现的公共资源与企业边际两大课题, 恰好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最大软肋
特约撰稿 苏小和
这个夜晚的19点是如此美妙,从斯德哥尔摩传来消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颁给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与奥利姆·E·威廉森(Oliver E.Williamson)两个人。如果是奥斯特罗姆一个人获奖,或者是我更加熟悉的威廉森一个人获奖,我是不会使用美妙这样的辞藻的。一个人不好,两个人可以互相取暖。当威廉森和奥斯特罗姆站在一起,我似乎看到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美妙经济学世界:一个平衡的公共资源经济治理结构,一个边际效应最大化的企业发展框架。两者相互结合,带给人类社会最大的福祉,也带给每一个有尊严的个体最大的福祉。
我的朋友李华芳对两位获奖学者的总结非常简练且准确。他说奥斯特罗姆一直在研究不同制度如何影响公共选择过程形成集体行动;而威廉森则在交易费用如何影响合约结构界定企业边界的向度上发掘出了伟大的成果。而北京的梁小民教授在场域的划分上有他自己的界定,他认为奥斯特罗姆是公共的,而威廉森则是企业的。
国内大多数人对奥斯特罗姆比较陌生,事实上,她一直与中国有关,并有几个学术品质相当不错的中国学生,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毛寿龙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建勋教授。这几年,在圈子之内,一直传言奥斯特罗姆将要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个月前,毛寿龙邀请奥斯特罗姆来北京讲学,王建勋还问过此事,她哈哈一笑,把传言当成了一个笑话。如今传言变成了现实,最激动不已的,当然是王建勋。消息一出来,他就努力给奥斯特罗姆打电话,可惜都未接通,只好电话留言,向老师表示祝贺。在王建勋看来,奥斯特罗姆获得诺奖,其意义不同凡响,这至少意味着,诺奖评审委员会终于认识到,关于人类自治能力的研究将为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开创一条新路。
至于威廉森,相信经济学圈子里的人都对他熟悉有加。这位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人,沿着哈耶克、科斯和布坎南的学术世界一路走来,将新制度经济学带入了一个更加细致、更加幽深,同时也更加有针对性的伟大境界。对于所有热爱制度经济学的读书人而言,威廉森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响亮名字。因此,当秋风听到威廉森获奖的消息,一点都不意外,只是简单说了4个字:实至名归。
但我想继续说下去:当奥斯特罗姆的公共资源研究成为诺贝尔奖醒目的桂冠之时,我们对公共这样的课题究竟理解多少?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个国家,公共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敏感词,或者是政府的一个代名词。我们只有政府主导,我们没有公共参与。不仅政府以为这样的局面是理所当然,我们的人民——我是说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团体,而不是抽象的总称,也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切的公共资源都必须交托在政府手上,他人无权置喙。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由此出现。在我们的国家,铁路是政府的,银行是政府的,石油、通信、能源当然也是政府的。教育是政府的,医院是政府的,科技也是政府的。政府像个无所不能的大善人,计划着,或者说主导着这个国家的一切,一切的思考,一切的吃穿住行,一切的愤怒,一切的欢乐,等等。
但问题就在这里。当政府将一切的行为集于一身,这将牵涉到多少计数的交易成本。扪心自问,我们的政府是不是浪费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是不是成本最高的企业?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层面诞生。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到今天威廉森的“企业边际”研究,今天的制度经济学已经将国家制度、法治、文化传统等诸多变量纳入到经济学的场域。任何一个试图发展的国家,当它仅仅用一种计划和垄断的方式来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如果它不是出于狂妄、愚昧和无知,“交易费用”的拷问就必然陈列在它的面前。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一直沿着“新制度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的路径考察、分析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他曾经直指中国大部分企业缺乏规范的企业行为方式,缺乏对商业文明的基本认同。当一个市场体系的“交易费用”大到人们无法接受的程度,企业家的行为选择必然是放弃,是逃离。没有人天生就愿意为了一笔生意去酗酒,没有人天生就喜欢行贿、喜欢拉关系走后门,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在一种暧昧的、模糊的状态下做生意,更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名目繁多、操作无序的工商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也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偷窃和模仿别人的技术。而这正是中国企业的本相。企业家都不愿意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在30年的发展中,渐渐有意识地丢掉了不确定性因素尤其是“交易费用”高企的国内市场,转而大面积依赖相对确定的国际市场。在这样的意义上,周其仁先生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拓展。
如此看来,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呈现的公共资源与企业边际两大课题,恰好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最大软肋。我们的公共资源需要走向一种多元均衡的状态,我们的企业必须要解决交易费用持续增高的局面。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体两面。感谢奥斯特罗姆,感谢威廉森,感谢两位大师同时站在了诺贝尔的领奖台上,是他们的同时出现,让我们如此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