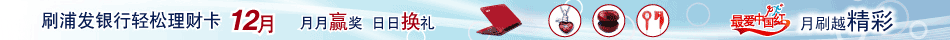德国90后:不关心柏林墙只反思国家前途
柏林墙倒塌20周年:今天,他们如何纪念
纪念的最好方式是思考,是伤痛教会了德国人思考
本刊记者/王维博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11月9日,西德长大的阿克曼特意从北京飞回德国。“整个柏林都在庆祝。”阿克曼在电话那头很兴奋,“街头放着老电影,酒吧里全是人,大家用酒精和歌声来庆祝。”
米夏埃尔·卡恩-阿克曼,德国汉学家,现任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上世纪60年代曾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汉学,70年代中期在北京留学,8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向德国人介绍了从老舍到张洁等一大批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
“墙已经没了这么多年了,还起什么哄?把日子过好是最重要的。”66岁的柏林人考夫曼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47年前,他生活在东德,是守卫柏林墙的普通一兵。
在柏林著名的波茨坦广场旁边,鲁夫经营着一家古董店,“这几天,柏林墙砖卖得挺好。”做墙砖买卖的生意人还有很多。这些被称为柏林墙碎片的砖头,被包装好,根据大小以从1欧元到数十欧元不等的价格,一卖就是20年。
18岁的雅克和他的朋友则将一场行为艺术献给了这个纪念日。他们把用塑料、纸板做成的“微缩柏林墙”摆到了柏林墙一段地基遗址上。
“说实话,我并不真正了解那段历史,我出生的时候,墙已经不存在了。”雅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所关心的,是我们对国家前途的反思。你以为现在东德和西德就不分裂了吗?”
筑墙者与逃跑的人
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德国驻华使馆新闻官龙安德只有13岁。
在龙安德的记忆里,父辈的往事多与“逃跑”有关。龙安德的父亲1938年出生于东柏林。母亲于1949年,在西德一个北方的城市出生。苏联的红军打到柏林的时候,父亲及家人连夜逃往了丹麦。
1945年到1947年,龙安德的父亲在丹麦一个专门供德国人住的难民营生活两年。两年之后重返柏林,“柏林8层以上的楼几乎都被推倒了”。虽然考虑到以后法、英和苏联还会有矛盾,但是他们还是决定安定下来。那时候,柏林市民能在城市自由活动,但随着冷战铁幕开启,1952年东西柏林的边界关闭。
1953年,因为一场柏林的起义,龙安德的父亲再次出逃到匈牙利,直到1961年才又回到柏林。资料显示,从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逃入西柏林,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包括技术人员、熟练工人。
1961年8月12日,与西柏林接壤的东柏林街道上所有灯光突然熄灭,军车连绵不断地开上来。2万多名东德士兵只用了6个小时,就在东西柏林间43公里的边界上,筑成一道由铁网和水泥板构成的屏障,这就是柏林墙的雏形。
“那道墙正式的名字叫‘反法西斯防卫墙’,接到任务的时候,我只知道要去修筑工事。”考夫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考夫曼回忆道,柏林墙并非只是一堵水泥灰墙,它外围有道3.5米高的通电铁丝网,铁丝网与柏林墙之间有50米宽的空地,埋有地雷。“包括壕沟在内总共有15道防线吧。有些墙体很厚,防止车辆冲撞;有些路段,翻过墙去还有河水挡着。”
重重封锁,也挡不住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想要过另一种生活的人还是不少——可耻的资本主义,那时候就是这样说。”考夫曼的语气不容置疑。
彼时龙安德的父亲已快大学毕业。东德政府要求他入党,龙安德的父亲不愿意,所以1964年又一次逃跑。柏林墙建成第三年,他先逃往丹麦,最后去了西德。
与大多数逃往西德的人一样,龙安德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半夜翻墙逃走,一同逃跑的朋友则被抓回去蹲了一年监狱。
“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多名士兵把守,24小时不断人,常年倒替。发现叛国越境的,我们就鸣枪,逮住他或者击毙他。这是政府允许的,也是士兵的责任。”考夫曼已经记不得抓获了多少偷越国境者,“我没有打死过人,所以后来也没有接受审查。”他至今不后悔那段“为国守边”的经历。
龙安德的父亲逃跑后的第二天,东德警察找上了门:“你儿子怎么敢离开我们伟大的东德呢?”龙安德的奶奶气愤地骂:“这个傻瓜,这个笨蛋,怎么就离开我们自己的国家?”
那时的逃亡常常被解读为对自由的向往。1963年6月25日,柏林墙建成两年后,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德发表了《柏林墙下的演说》,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我现在觉得这是一种误读,过度渲染了柏林墙的政治符号作用。有些人拼命要到那边去,因为那边也是德国的土地,有骨肉朋友,想过去是自然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翻墙与‘自由’无关。但当时听美国人、英国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也很激动,觉得寻找自由是自己的责任。”柏林市政厅退休办事员施莱因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施莱因上世纪70年代正在东柏林居住,“最终我没有冒险。因为我在东德生活得也并不糟糕。”
“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1976年,龙安德出生在西德的科隆市。8岁时,他到东德去看望祖母和其他亲人。从西德到东德虽然要经历严格检查,但并没有很多限制。
东德人很安静,平常习惯在家里呆着。西德常见的大众、宝马、奔驰在东德几乎看不到,街上跑的都是冒着黑烟的老式汽车,买一块面包要排很长的队。这对年幼的龙安德来说,简直无法忍受。
汉学家阿克曼那时还是个少年,他在东德没有亲戚。唯一一次去东柏林,是因为学校安排去东柏林旅游一天,除了要等很长时间接受检查外,对东德没有特别的印象。
“我去了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但是东德对我来讲,就如同让我去芬兰一样,让我去那里干吗?没有这种意识,没有这个必要,我和他们没有关系。”阿克曼说。
那一次之后,阿克曼再没有去过东德。实际上,很多西德人也都有类似于阿克曼的体验。在他们的意识里,两个德国已经成为一种思维习惯,他们并不认为德国的统一是迫切解决的问题。
在当时的阿克曼看来,西德进入欧洲,变成欧共体的一部分要比统一两个德国重要得多、必要得多。“我承认,这些都是当时大部分西德人的想法。”
对阿克曼和龙安德来说,柏林墙的倒塌非常突然。前不久,德国的一个媒体把20年前东德和西德的新闻报道拿出来对比着播,龙安德才弄明白那段历史。
一直在东边的考夫曼记得起那一天的所有细节。“那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1989年的11月9日,本来不是我执勤,但柏林墙这边地动山摇,我也从宿舍跑出来,我看到人们喊口号,舞动旗帜,我没有听到枪响。”考夫曼说。
“推倒柏林墙!”“打倒墙!”有人站出来高呼着,结果一呼百应,数十万人一眨眼工夫居然把延绵数十里的柏林墙推倒了。
“德国的统一,是东德人创造的,不是我们西德人创造的。这是一次没有流血的伟大革命。”阿克曼这样评价。
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墙
柏林墙倒下的第二天,在东德做研究员的默克尔就带着妹妹到西柏林百货公司“朝圣”,首次品尝了来自意大利的奶酪。 如今,作为德国统一后首位来自东部的总理,默克尔成为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真正的主角。
柏林当地时间11月9日下午,默克尔和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起重新越过柏林墙一处检查点“伯恩霍莫大桥”——20年前最早开放的东西柏林边界关卡。“即使上世纪80年代,我都不敢相信柏林墙能在我有生之年倒塌。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想到,德国和欧洲能统一,这种幸运让人难以置信。”默克尔说。
来到柏林墙的脚下,看到欢呼的人群,阿克曼再一次落泪了,但心境却与20年前大不一样。
1989年11月9日,阿克曼正在北京为刚成立的歌德学院奔波。当天晚上,通过电视他看到柏林墙倒的消息。东德人爬上柏林墙挥舞双手的画面击中了阿克曼的内心,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他流泪了。
“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墙。”柏林墙已超越了政治意义,而是对生活的一种象征。这是时隔20年后,阿克曼再次流泪的原因。
柏林墙推倒后,每天都有几万人从东德涌入西德。当年,西德政府给每个访客100马克,作为欢迎的礼物。然而今天,这种不平衡似乎并未改变, “统一代价之大”也越发引起东西部同样的不满。
柏林自由大学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2%的前东德居民和11%的前西德居民表示,如果柏林墙没有被推倒,柏林形象会更好些。柏林墙拆除20年后,许多前东德居民认为,前西德接管了他们的文化和政治,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而前西德民众说,他们不情愿再支付高昂的“统一税”。
从1991年开始,联邦政府累计向东部地区输血总额已经达到了1.3万亿欧元,如此庞大的天文数字,居然还是未能拉平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差距。而前东德人对共产主义时代的怀念也令西边的人厌烦。
德国东部的失业率几乎是西部地区的一倍左右,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和西部有着明显差距,有四分之一的东部地区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都令联邦政府头疼。最乐观的估计是,等到2019年,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可以达到西部的平均值。
“纪念的最好方式是思考。伤痛的记忆固然重要,最需要的是未来的思考。是伤痛教会了德国人思考。”阿克曼说。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